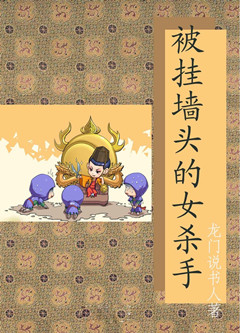面包树上的女人-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躺在我身边,捉着我的手,我转脸问他:「我是不是最幸福的一个?」
他轻轻扫我的脸颊,我在他身边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清早,迪之的传呼机响起,把我们吵醒。
「卫安传呼我。」她说。
「你再找他,我便不理你。」我跟她说。
「我要见他一次。」
她叫卫安到酒店接她,真是死心不息。
我们把光蕙送上计程车,她和孙维栋之间的事,谁也帮不上忙。
当天晚上,我接到迪之的电话。
「我把车冲上人行道,撞倒一棵大树。」
「你有没有受伤?」我吓了一跳。
「没有。卫安的车车头全毁掉,他给我吓得魂飞魄散,我故意的。」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可能会死的?」我斥责她。
「那一刻,我倒想跟他一起死。但,从警察局回来,我不断想起他的脸,他算什么?我会蠢到为他死。」
「你总算想得通。」
「昨天我醉了,光蕙到底发生什么事?」
「孙维栋是性无能的。」
迪之在电话那边大笑:「我猜中了!稍为好一点的男人,却是性无能,真好笑。」
迪之失恋,我好不到那里,她整天缠着我和林方文。
那天晚上,我和林方文陪她吃过晚饭,她又缠着要我们陪她上的士高,结果我们去了荷东。我和林方文都不爱跳舞,她自己在舞池上跳了一会,有几个男人向她搭讪,她回来跟我说:
「借你的男朋友给我好吗?」
「你拿去吧。」我说。
她拉着林方文的手,把他带到舞池上,双手放在他的脖子后面,脸贴着他的肩膊,身体贴着他的身体,她把他当做她的男人,我开始妒忌。
三首慢歌之后,转了一首快歌,迪之拉着林方文的手,把他带回来,「这个男人还给你。」
「你可以为我写一首歌吗?」她问林方文,「你不是每年除夕都为程韵写一首歌的吗?」
我觉得她有点儿过分。
林方文笑着没有回答。
「你的福气比我好。」她苦涩地笑,独个儿回到舞池上。
我和林方文相对无言,那一夜开始,我知道迪之对林方文有不寻常的感情。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我跟同学在大会堂看话剧,散场后,碰到卖番薯的小贩,我买了三个,放在大衣里保温,拿去给林方文,我想给他一点温暖。
到了宿舍,我发现迪之竟然在他房间里,她坐在他的床上吃蛋糕。迪之看见我,连忙站起来跟我说:
「我经过饼店,看见还有一个芝士蛋糕,立即买来跟你们一起吃,我以为你也在这里呢。」
「我去看话剧。」我绷着脸说,「我买了煨番薯。」我从大衣里拿出三个热烘烘的番薯放在桌上。
「真好!一直想吃煨番薯。」迪之把那个芝士蛋糕推到一旁,「还暖呢,我拿一个回家吃,可以吗?」
「随便你。」我冷冷地说。
「谢谢,我走了,再见。」她在我身边走过,没有望我。
「芝士蛋糕好吃吗?」我问林方文。
他望着我,说:「她是你的好朋友。」
「正因为迪之是我的好朋友,我才了解她,她想找一个男人报复。」
「你以为我会吗?」林方文问我。
我跑去追迪之。
「迪之!」我在后面叫住她。
她回头看我的时候,正流着泪。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啜泣。
「对不起。」我说。
「我很孤独。」她流着泪说。
「我明白。」
「我跟林方文之间没有事情发生。」她说。
「别傻,我相信你。到目前为止,他还是一个好男人,不要找他做报复对象,好不好?」我也忍不住流泪。
「我不想的。」她说,「我恨男人。」
「我知道。」
「我没事了,你回去吧。」迪之说。
「不,我跟你一起走,我们住得很近的,你忘了吗?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回家了,你在这里等我,我进去拿书包。」
「迪之怎么样?」林方文问我。
「如果不是先遇上我,你会喜欢她吗?」我问他。
他失笑。
「答我。」我说。
「不会。」
「真的。」
「早知道你不会相信。」
「我陪迪之回去。」我跟他吻别。
那一夜很冷,迪之没有穿上大衣,我让她躲在我的大衣里。
「我暂时借温暖给你。」我说。
「比不上男人的体温。」她说。
「死性不改。」我骂她。
迪之拿了一个星期假,去南丫岛住。每次被男人伤害之后,她便跑去找邓初发,邓初发是她的庇护所。
光蕙约我吃饭,没想到她把孙维栋也带来。她对孙维栋的态度和以前有很大分别,她对他呼呼喝喝,他跟她说话,她摆出一副烦厌的样子,孙维栋却逆来顺受。
在洗手间,我问她:
「你不是说要跟他分手的吗?」
「说过了,他在我面前哭,求我不要离开他。」
「如果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还要拖泥带水呢?」
「我寂寞。」
寂寞最霸道,可以成为伤害任何人的藉口。一个男人,泥足深陷地爱上一个不爱他的女人,注定要放弃自尊。
「如果我找到另一个男人,我便会跟他分手。」光蕙说。
「你这样是精神虐待他。」
「没办法,是他自愿的。」
我跟他们分手的时候,孙维栋找到一个机会紧紧握着光蕙的手,可以握到了,便好象很快乐。光蕙的脸,却没有任何表情。他越着紧她,她越厌弃他。
迪之从南丫岛打电话给我,她说天天在岛上晒冬天太阳。
「邓初发好吗?」
「好!他看见我便开心。」
邓初发和孙维栋真是一对难兄难弟!邓初发已经康复过来,但迪之是他心里的一条刺,时常刺痛他,他却舍不得拔掉。孙维栋还在苦海浮沉,拿着一根钉不断刺向自己胸口。谁叫他们爱上害怕寂寞的女人?
林正平唱红了林方文的歌,林方文的歌也令林正平更红。林正平很喜欢他,想把他据为己有,于是提出成立一间制作室。他是大股东,小股东除了林方文之外,还包括林正平的唱片监制--一个有严重黑眼圈同性恋者,还有林正平的经理人邱正立,他以前是弹钢琴的,据说他也是男同性恋者。
这间由四个股东组成的制作室,有两个同性恋者。据迪之说林正平偶然也玩玩男人,那么,林方文是唯一一个绝对的异性恋者了。我真怕她受不住那份阴阳怪气。
「放心,我不会变成同性恋的,我只喜欢女人。」林方文跟我说。
「我怕你一个敌不过他们三个!」我笑着说。
「他们都是很有才华的人,我喜欢跟有才华的人合作。」
制作室的工作很忙,许多时他都无法上课,我只好替他做功课。我见他的时间也越来越少,那个有严重黑眼圈的唱片监制晨昏颠倒,爱拉着林方文在晚上工作。好不容易他坐下来跟我吃饭,他们却不断传呼他去喝酒,他们好象想跟我争男朋友。
「你已经很久没有上课了。」我跟林方文说,「再这样下去,他们会逼你退学。」
「必要时便退学。」他说。
还有一个月便是学期终结的考试,这一个学期,林方文差不多完全没有上课,我只好替他做一份笔记。那天傍晚,我到林方文的宿舍放下笔记,他的母亲坐在房间里,她看见我,立即起来,亲切地对着我微笑,她的端庄,完全不象一个经营小舞厅的女子。
「伯母,你等林方文?」
「是呀,我刚从台湾回来,买了一盒凤梨酥给他。这种凤梨酥他最喜欢吃的,他爸爸以前行船到台湾也买过给他。」
「他可能很晚才回来。」我说。
「他很忙吗?要工作又要读书。」
「他跟朋友成立了一间制作室。」
「我还没有请教你的姓名呢?」
「伯母,我叫程韵。」
「程小姐。」
「伯母,叫我程韵可以了。」
她拿起一块凤梨酥:「来,你试一块。」
「不。我等林方文回来一起吃。」
「好的。」她拿起林方文放在床上那支乐风牌口琴:「这支口琴是他爸爸的,他还舍不得丢掉。」
「他很喜欢这支口琴。」
「他爸爸是行船的,我曾经跟着他上船生活了四十五天。那时,我们新婚不久,他在甲板上为我吹奏口琴,还自己作了一首歌呢!」她笑着,「他哪里会作歌!」
她哼了一段不知名的音乐给我听,大抵那就是林方文爸爸在甲板上作的一首歌。
她拉着我的手,哼着那段歌,跳起舞来。
「我们在甲板上跳舞。」她怀念着。
她的舞跳得很好,我很笨拙,她把我当做她的丈夫,回忆他留给她最浪漫的时光,她眼里并没有泪,往事的伤痛,只留在心上。
「林方文的音乐细胞也许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她说。
「可能是的。」我说。
「他写的每一首词,我都常常听,他是个很有才气的男孩子。」她流露着母亲的自豪。
「是的。」我同意。
「他小时最爱摺纸飞机,我以为他长大后会做飞机师,没想到他当上填词人。这么晚了,我不等他了。」她站起来。
「伯母,你再等一会,他会回来的,我传呼他。」
「不,不要打扰他工作。你叫他要用心读书,不要忙坏身体。」
我送她上了一辆计程车,临行她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再会。如果她愿意离开那个中年男子,林方文也许会原谅她,可是,谁伴她度余生呢?她太寂寞了。
我在宿舍睡着了,林方文回来,把我唤醒,已是深夜。
「你回来了,你妈妈来过。」
「嗯!」他一张温熙的脸突然变得冷淡。
「她刚从台湾回来,买了一盒你最喜欢的凤梨酥给你。她等你等了很久。」
他并没有热情地捧起那盒凤梨酥,他是故意跟他母亲作对。
「她叫你用心读书。我替你做了一份笔记。答应我,你会来考试。」
他点头。
可是,那一天,他没有出现。
考完试后,我冲上录音室找他。
「你为什么不去考试?」
「我走不开。」他说。
「你答应过我的。」
「你先让我写完这段歌词好不好?」
黑眼圈老妖露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在这里等你,直到你回去考试为止。」我坐到录音室外面,我要和他比耐性。
他没有理会我。到了午夜,歌还没有录完,我在那里坚持着,连一个呵欠都不敢打。黑眼圈老妖叫人买了宵夜,林方文递上一碗热腾腾的粥给我。
「我不回去考试了,你走吧!」他说。
「还有一年便毕业,你现在才放弃?」我很失望。
「是否大学毕业并不重要。」他说。
「因为你妈妈特别叮嘱你要用心读书,所以你偏偏要放弃,对不对?」我质问他。
「别乱猜,只是突然不想念书。」
教务处要林方文决定退学还是留级,他没有答复,便搬离宿舍。黑眼圈老妖替他在尖沙咀一栋旧楼内找到一个八百多尺的单位,租金三千多元,屋内家具齐备,有一个仅容两个人站着的小阳台,可以俯瞰尖沙咀最繁盛的十字路口。
新屋入伙的第一天,我们都累得要命,只吃饭盒庆祝。
「我一直憧憬着我们一起行毕业礼。」我跟他说。
「我会出席你的毕业礼。」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会送你一束百合。」
还有一年才毕业,林方文离开校园,离开我的视线更远,一切会安好吗?
第四章 空中的思念
………………………
学校开始放暑假,我在杂志社已不需做校对,他们让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