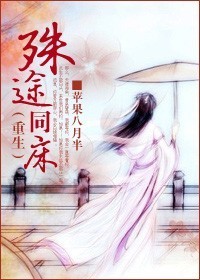殊途-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全校都知道,市委秘书长的儿子,为了她和人打了一架,黄昏时分,她和晴川拎着书包刚走到楼下,二楼走廊上有人吹了声又尖又细的口哨,怪腔怪调的大叫:“祸水!”!
晴川回过头去,提高了声音叫道:“哪个?有胆子滚出来!”
没有人作声,教学楼前种着一整排高大的广玉兰,枝叶繁茂,有片叶子打着旋飞坠下来,咔嚓一声轻响,落在任意意的脚踝边。校园里到处都是这种树,大片的硬挺叶面,一面光洁如革,一面有着细密的淡黄色绒毛,有点像枇杷树的叶子。机关大院里种了不少枇杷树,晴川小时候,总是爱和一群男孩子爬树去摘枇杷,从来都不好吃,其实。
任意意的长发垂在晴川的手腕上,滑腻轻泻,滑不留手,一下子滑下去,发线在晚风里轻轻荡漾,晴川有点恍惚,任意意的眼波像水一样,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声音也温温柔柔,像水一样。晴川懊恼的揪了揪自己刺猬样的短发,说:“我怎么就淑女不起来?”任意意璨然微笑,她笑起来很好看,一口细白的糯米牙,真正的齿若编贝。
过了几天,晴川看到任意意在捡来的广玉兰叶子上写字,秀气的钢笔字:“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晴川摇头晃脑捉狭的背诵:“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以翰墨为香。”
任意意没有听得完,就作势在她手上拍了一记,说:“只有你会拽文。”晴川语文课不大听讲,忙着看闲书或是做化学作业,化学老师总是布置很多的作业,晴川抱怨说:“一辈子都做不完似的。”少年,以为多做三五道题就是人生最大的烦恼。虽然课堂开小差,但她的语文成绩甚至比语文课代表任意意更出色,因为底子好。任意意很羡慕她家里的藏书,这星期她才从晴川那里借到《随园诗话》。
晴川有回向她无意提到:“小时侯背《论语》背不上来,就装肚子疼。”任意意想像不出来晴川刻苦背书的样子,因为语文课上要求背诵的篇目,从来没有见她下过功夫,但她见过晴川背单词,记不住就抱怨:“真是比先秦古文还难。”
是另一国语言,当然比先秦古文还难。晴川还是孩子气,稍稍遇上事就怨天尤人,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苦。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但抱怨完后不过一分钟就后会忘记,有一种没心没肺的快乐。
早自习后她们两个总是一块儿去吃早餐,食堂里人太多,低年级的学生总是回教室吃,晴川拿勺子敲着不锈钢饭盒,拉长了声调唱:“远看水光光,近看像米汤,虽只三四粒,总比没有强。”害得全班同学都差点喷饭,更有人捶桌大笑,连班主任也忍俊不禁。后来被学校后勤处知道,此后的稀饭总算是像模像样了。
任意意跟她开玩笑说:“全校学生都要感谢你呢。”晴川的眼角微向上翘,不笑也是一种甜滋滋的模样,此时却有一种淡然的冷漠,说:“假若我是李晴川、赵晴川,谁理会我的打油诗?”
任意意有点隐约的觉察,这个骄傲的女孩子心底里的寂寞。
其实晴川有大帮的朋友,男生女生,高谈阔论,呼啸成群。任意意才是寂寞的,班上的女生都不大跟她说话,还有人冷不丁冷嘲热讽。晴川说:“她们妒忌你啊。”晴川就是这样,心直口快,因为一贯是周围的人哄着她。
黄昏时分她们两个爬到天台上去说话,俯瞰着整个校园。粗砺的水泥栏杆晒了一天,趴在上面微温的感觉,微微呛人的灰尘气味。晴川喜欢坐在天台栏杆上,她的身后是满天的晚霞,有一颗极大极亮的星星升起,明亮的像眼睛。晴川说:“假若有一天想死,最后一瞬间,我也要知道飞的感觉。”任意意跺了一下脚,说:“好端端的说什么怪话。”晴川从栏杆上跳下来,隔热层的空心砖,在她脚下“咚咚”响。她忽然问任意意:“你是不是很喜欢郭海林?”
任意意不知道她从哪里看出来,她的脸在晚风里发着烫,她并没有回答。晴川又坐回栏杆上,她的身子微微向后倾,一头蓬蓬的短发在风里,像绒绒的一朵蒲公英。任意意说:“别往后仰了,当心。”
晴川指着天幕给她看,说:“孔雀蓝、蟹壳青、烟紫、橙红……”听着就是琳琅满目眼花缭乱的颜色,她说:“张爱玲喜欢珠灰,我喜欢银红。”
这是任意意第一次听说张爱玲,晴川借了本《传奇》给她看。港版的,繁体竖排,看着相当的吃力。可是那样炫目的文字,仿佛訇然打开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有绮艳的乔琪纱,有黯然的沉香屑,有一个城市的陷落,只为成全一个流苏。景泰蓝方樽里插着大篷的淡巴菰花,小白骨嘟,像是晚香玉。后来任意意与晴川,满世界找晚香玉这种花。
晴川说:“张爱玲的文字,好像一匹织锦缎,看着花团锦簇的繁华热闹,触手却是冰凉。”
任意意将这句话讲给郭海林听,郭海林有几分诧异,就去向晴川借张爱玲的书,那是他第一次主动找晴川说话,他站在走廊里问她:“晴川,你能不能将《传奇》借给我看看?”1994年的春天,走廊里能看到楼前高大的广玉兰树,开了一盏一盏洁白的花,仿佛是莲。这种花有清新淡雅的香气,凋谢时,是一瓣一瓣的落。晴川从操场回来,拾了一瓣,在上头写:“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曰,此时此夜难为情。”淡蓝色的钢笔痕迹,写上去落絮无声,再搁一会儿,字迹就变成黑色。
她第四遍读《神雕侠侣》,郭二小姐有那样声名赫赫的爹爹与妈妈,闻名天下的神雕大侠又给了她三枚金针,天下间诸事无可不为,可是,三枚金针一一用出,最后只是在华山之巅,眼泪夺眶而出。
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只是心下一片苍凉罢了,郭襄,与她同样十六岁的郭襄。
---------
长安拿了一本卷了角的《神雕侠侣》,楼下租书店吴老板说,这个书好看。
她也觉得好看,从第一本看到这第四本,看得连饭都不想吃。长安从电子厂里辞职出来,在“梦巴黎”娱乐城当前台,每个月工资也有八百块,但是公司不包吃住,光这间小小的阁楼,也得三百五十块一个月。长安跟人合租,每个月也花一百多块。
天气闷热,阁楼里像蒸笼一样,太阳从天窗里晒进来,人躺在席子上就像一张烙饼,翻来覆去的被烤着。长安起身拿凉水拧了个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躺下来接着看书。
有些字并不认识,她连蒙带猜,其实当年她的语文成绩不错,上课时老师总叫她起来带头念课文。
她和一个在工厂认识的老乡合租,老乡现在面包店打工,每天清早就去上班。长安是下午四点才上班,凌晨两点下班,上午她都在睡觉,下午一个人关在阁楼里,无聊的只好发呆。书店也是租的这家房东的门面,就开在楼下,一来二去跟吴老板熟了,吴老板看她无聊,就顺手给她几本书看。
书里讲到杨过送给郭襄三件礼物,每一件礼物都看得人心里怦怦直跳。她在心里想,这个男人必然是爱着郭襄的,不然为什么肯这样给一个女孩子费心思。哪知看到最后,结局却无声无息。她在心里感叹,人生在世,果然福气总是有限的,郭二小姐要什么有什么,从小在蜜罐里长大,总有一样不如意。她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命里八升,求不得一斗。
看完书已经是三点多钟,太阳正毒,她又用凉水洗个脸,就着桌子上的小镜子开始化妆。
刚上班时就被领班教训:“要化妆啊。”她从来没有化过妆,最后壮着胆子去买了一支十块钱的口红,涂在唇上厚厚的一层,像是猪油腻腻的,叫她总想去抿嘴,可是在梦巴黎淡蓝色的灯光下,嫣红如醉。
现在她已经熟练的打粉底,画眉,描眼线,领班说,这样才精神,确实精神,梦巴黎四面无数的镜子,大大小小,方的圆的,镜里的自己,眉目如画,有一种剔透的娟秀。
总有客人爱跟她开几句玩笑,她也知道自己的优点,但笑得恰到好处。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这份工来之不易,她已经攒了有一千块钱了。
经理走过来跟她说话:“小徐,酒水单上没有我签字,不许打折。”经理最近和领班不太对头,但领班是老板的远房亲戚,长安接到酒水单时,听领班说:“打九折。”她迟疑了一下,才笑着说:“经理忘了签字吧?麻烦王姐你拿去给他签下。”
领班瞧了她一眼,高跟鞋蹬蹬蹬就走开了。
长安拿到第二个月工资的时候去买了一双高跟鞋,那是她穿的第一双皮鞋。一天下来脚站得生疼生疼,同事教她在脚后跟贴创可贴,但一张创可贴要三毛钱,她舍不得,将鞋后跟处用砖头敲了敲,第二天又穿着上班。她已经有一米六四,穿上高跟鞋站在前台后,前台上一溜小射灯打下来,照着就像亭亭一枝白荷,气质恬静,人人都想跟她搭讪两句。
下班时才发现收到一张百元的假钞,收到假钱要自己赔的。长安心里一阵抽痛,那是多少箱方便面。王领班扬着脸说:“说过多少次了,你们总听不进去。工作没一点责任心,非要花钱买教训才知道。”
她赌气低着头,收银机里一摞一摞的钞票,灰蓝色的一百元,软塌塌的潮乎乎,有一种可疑而难闻的气味,她觉得像是汗馊气,无数的手捏过,想着就肮脏,但这肮脏她都没有。王领班和她一样没读完初中,长得也一般,方方的一张脸,扑上粉也像个揉坏了的汤圆,但她是老板的亲戚,所以一来就当领班,趾高气扬的训斥人。
这天下班特别晚,包厢里有一桌客人凌晨三点多才结帐,她下班走回家去,这个城市的霓虹灯依旧闪烁,花花绿绿滟影映在人眉目间。人行道上的夜市摊子还没有收,烧烤的木炭散开呛人的青烟,油腻的羊肉串或是旁的肉类,在烧烤架上滋滋的冒着油。吃宵夜的几个人向她吹了声口哨,说:“小姐,来喝一杯。”
她并不理睬,继续向前走。身后摩托车突突的引擎声,她没有在意,突然只觉得肩上一紧,一股极大的力道向前扯去,她猝不防及,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挣扎着爬起来,摩托车后座的人正抡着她的背包,她本能的追上两步,摩托车油门加大,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她呆子一样站在街头,这才觉得膝头刀割一样的疼,低头一看,左膝上蹭破了一大块皮,手肘上也在流血,她的身后正是一家美食城,霓虹“生猛海鲜”在夜色里明灭,每一次亮起,就突兀的将这个世界照成一片黯然的红色。
她穿过狭陡的楼梯,回到那笼子似的阁楼上。洗完伤口她才愣愣的坐在床上,毫无预戒的,她的身子开始剧烈的颤抖然后就抽泣起来,室友掀开蚊帐,睡意朦胧的问:“怎么了?”
她一边哽咽一边讲给她听,室友嗐了一声,躺回去睡觉,说:“你算是运气好的了,没听人说,前两天开发区发现无名女尸,被人先奸后杀。”
她抱膝坐在床上,全身像在井水里冰着,牙关轻轻的打着寒战,她怕死,她从来没有这样怕过。她见过养母死后的样子,可怕极了,养母死后是她给穿的寿衣,胳膊硬硬的,怎么都笼不进袖子里去。尸体泛着青灰的颜色。她不要死,她还这样年轻,她不要死。
天窗外是瓦灰色的天,有极大的月亮,模糊、晕黄,像是包厢里烛台的影子,月光映在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