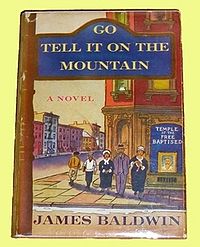在细雨中呼喊-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具僵尸,把整个当铺搅得天翻地覆。勇敢的孙有元得到父亲遗体的有力支持,将那几个伙计打得惊慌失措。他们谁也不敢碰上那具死尸,以免遭受一年的厄运,那个时代的迷信使孙有元的勇敢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挡。当我祖父挥起他的父亲,向那个面如土色的掌柜击去时,轮到孙有元惊慌了,他把父亲的脑袋打在了一把椅子上。一声可怕的声响使我祖父蓦然发现自己作孽了,他那时才知道自己大逆不道地将父亲的遗体作为武器。父亲的脑袋已被打歪过去,我祖父经历了片刻的目瞪口呆之后,立刻扛起父亲的遗体窜出门去,在凛冽的寒风里奔跑起来。然后孙有元就像一个孝子一样痛哭流涕了,那时候他坐在冬天的一棵榆树下面,怀抱我损坏了的曾祖父。我的祖父使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父亲打歪的脑袋扳回来。
孙有元埋葬了父亲以后,并没有埋葬贫困,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能挖些青草煮熟了给母亲吃。那是一些长在墙角下有着粉绿颜色的小草,孙有元不知道那是益母草。于是他惊喜无比地看到卧床不起的母亲,吃了这种草后居然能够下地走路了。这使我那粗心大意的祖父茅塞顿开,他极其天真地以为明白了一个真理,他感到那些妙手回春的郎中,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无非是割一堆青草像喂羊一样去喂病人。因此他放弃了去城里打短工的念头,我祖父作为石匠之后,决定像一个郎中那样医治百病了。
兴致勃勃的孙有元知道刚开始必须上门问诊,日后名声大了就可以坐在家中为人治病。他背起了一篓子杂草,开始了走家串户的生涯,他嘹亮的嗓音像个捡破烂似的到处吼叫:
“草药换病啦。”他风格独特的叫唤格外引人注目,可那一付贫穷的样子让人将信将疑。到头来还真有一户人家请他上门就诊,我祖父行医生涯第一个病人,也是最后一个,是个腹泻不止的男孩。面对这个气息奄奄的孩子,孙有元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也不号脉问诊,就从篓子里抓出了一把青草给患者的家人,让他们煮熟了给孩子吃。当他们满腹狐疑看着那把青草时,孙有元已经走到了屋外,继续他的喊叫:
“草药换病啦。”当孩子的家人从屋里追出来,用虔诚的疑惑向我祖父发出询问时,我实在惊讶孙有元竟然还能胸有成竹地告诉他们:
“他吃了我的药,我就带走他的病啦。”
这个可怜的孩子吃下那一把青草后,立刻上吐下泻绿水,没两天就一命呜呼了。从而让我曾祖母在一个下午,胆战心惊地看到了十多个男人气势汹汹走来的情景。
我祖父那时候一点也不惊慌,他让脸色苍白的母亲回到屋里去,又将屋门关上,自己则微笑着极其友好地迎候他们。死者的家人和亲属是来向孙有元讨命的,我祖父面对这班脸色铁青一意孤行的人,竟然想用花言巧语哄骗他们回去。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聆听孙有元冗长的废话,而是一拥而上,将我祖父团团围住,几把铮亮的锄头对准了他闪闪发亮的脑门。经历过国军枪林弹雨的孙有元,那时候显得不慌不忙,他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们,别说才十多个人,就是翻一倍,他也照样打得他们伤痕累累。死到临头的孙有元如此口出狂言,反而把他们给弄糊涂了。这时候我祖父解开了上衣的纽扣,对他们说:“让我把衣服脱了,再和你们打。”
说着孙有元拨开一把锄头,走到屋前推开了房门,他进去后还十分潇洒地用脚踢上了门。我祖父一进屋就如石沉大海一样销声匿迹了,那班复仇者在外面摩拳擦掌,他们不知道我祖父已经越窗而逃,一个个如临大敌似的严阵以待。他们左等右等不见孙有元出来,才感到情况不妙,踢开房门以后,屋内空空荡荡。随后他们看到了我祖父背着他母亲,在那条小路上已经逃远了。我祖父不是一憨乎乎的乡巴佬,越窗而逃证明了他是有勇有谋的。
孙有元背上我曾祖母撒腿就逃以后,他便很难终止自己的奔跑了。他就像我祖母一样,挤身于逃亡的人流之中,有那么几次他都清晰地听到了身后日本人的枪炮声。我祖父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孝子,他不忍心看着我曾祖母扭着小脚在路上艰难行走,于是他始终背着母亲,满头大汗气咻咻地在那些尘土飞扬的路上,跟随着逃亡的人流胡乱奔走。直到后来的一个夜晚,精疲力竭的孙有元脱离了人流,将我曾祖母放在一棵枯萎的树下,自己走远去找水后,他才不用再背着母亲奔走了。连日的奔波让我虚弱不堪的曾祖母,在那棵树下一躺倒就昏昏睡去了。我曾祖母在那个月光冷清的夜晚,睡着后被一条野狗吃了。童年时我的思维老是难以摆脱这恶梦般的情景,一个人睡着后被野狗一口一口吃了,这是多么令人惊慌的事。当我祖父重新回到那棵树下,我的曾祖母已经破烂不堪了,那条野狗伸出很长的舌头一直舔到自己的鼻子,凶狠地望着我的祖父。母亲凄惨的形象,使孙有元像个疯子一样哇哇大叫,我祖父那时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人,他像那条野狗一样张开嘴巴扑了上去。野狗更多的是被我祖父的嗷叫吓坏了,它立刻调转方向逃跑。气疯了的孙有元竟然去追赶逃跑的狗,他追赶时的破口大骂无疑影响了他的速度。到头来狗跑得无影无踪后,我祖父只能气急败坏同时又眼泪汪汪地回到母亲身旁。孙有元跪在我曾祖母的身旁使劲捶打自己的脑袋,他响亮的哭声使那个夜晚显得阴森可怖。
孙有元埋葬了母亲以后,他脸上由来已久的自信便一扫而光,他极其伤感地在逃亡的路上随波逐流,母亲的死使他的逃亡顷刻之间失去了意义。因此当我祖父在一庭残垣前最初见到我祖母时,他的心里出现了一片水流的哗哗声。我祖母那时身上富贵的踪影已经丝毫不见,她衣衫褴褛地坐在杂草之上,恍惚的眼神从披散的头发中望到了我祖父凄凉的脸。被饥饿弄得奄奄一息的祖母,不久之后就伏在我祖父的背脊上睡着了。年轻的孙有元就这样得到了一个可以作为妻子的女人,他不再毫无目标地漂荡。经历了饥饿和贫困长时间掠夺的孙有元,背着我祖母往前走去时,他年轻的脸上红光闪闪。风烛残年
祖父摔坏腰以后,我的印象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叔叔。这个我完全陌生的人,似乎在一个小集镇上干着让人张开嘴巴,然后往里拔牙的事。据说他和一个屠夫,还有一个鞋匠占据了一条街道拐角的地方。我的叔叔继承了我祖父曾经有过的荒唐的行医生涯,但他能够长久地持续下来,证明了他的医术不同我祖父那种纯粹的胡闹。他撑开宽大的油布伞,面对嘈杂的街道,就像钓鱼那样坐在伞下。他一旦穿上那件污迹斑驳的白大褂,便能以医生自居了。他面前的小方桌上推着几把生锈的钳子,和几十颗血迹尚在的残牙。这些拔下的牙齿是他有力的自我标榜,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招睐着那些牙齿摇晃了的顾客。
一天上午,当祖父背上一个蓝布包袱,怀抱一把破旧的雨伞,悄无声息地从我们前面走过时,我和哥哥十分惊奇。他临走时都没和我父母说一句话,而我的父母也没有任何异样的神态,我和哥哥趴在后窗的窗台上,看着祖父缓慢地走去。是母亲告诉我们:“他去你们叔叔那里。”
祖父晚年的形象就像一把被遗弃的破旧椅子,以无声的状态期待着火的光临。厄运来到他身上的那一天,我哥哥孙光平以他年龄的优势,先于我得到了一个书包。那一刻在我童年记忆里闪闪发亮,在我哥哥即将获得上学机会的那个傍晚,我的父亲,兴致勃勃的孙广才,以莫名其妙的骄傲坐在门槛上,声音洪亮地教育我的哥哥,如果和城里的孩子吵架——“一个你就打他,两个你赶紧逃回家。”
孙光平傻乎乎地望着孙广才,那是他对父亲最为崇拜的时候。我哥哥虔诚的神色,使我父亲不厌其烦地讲述同样的道理,并不觉得那已经是废话了。
我父亲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乡巴佬,任何时髦的东西他都一学就会。当我哥哥背上书包第一次走向城里的学校时,孙广才站在村口给予他最后的提醒。他一个成年人学电影里坏人的腔调实在是滑稽可笑,他扯开嗓子大喊:
“口令。”我哥哥天生就具有非凡的概括能力,这个八岁的孩子转身来回答时,并没有转述父亲昨晚纷繁复杂的教导,而是简单明了地喊道:“一个就打,两个逃回家。”
在这表达欢欣场面的另一侧,我晚年的祖父拿着一根绳子无声地从我身旁走过,去山坡上捡柴了。孙有元那时的背影在我眼中高大健壮,我坐在泥土上,他有力摆动的脚走去时,溅了我一脸的尘土,使我当时对哥哥的嫉妒和盲目的兴奋变得灰蒙蒙一片。我祖父的厄运和我哥哥的兴奋紧密相连,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当我和弟弟还依然满足于在池塘边摸螺蛳时,第一次从城里学校回来的孙光平,已经懂得用知识来炫耀自己了。我无法忘记孙光平最初背着书包回来的耀武扬威,我八岁的哥哥将书包挂在胸前,双手背在身后,显然后一个动作是对学校老师的摹仿。然后他在池塘旁边坐下来拿出课本,先是对着太阳照一照,接着十分矜持地阅读了。我和弟弟那时候目瞪口呆,就像两条饥肠辘辘的狗,看到一根骨头在空中飞去。就是在这个时候,孙广才背着满脸死灰的孙有元奔跑过来。我的父亲那时显得十分恼怒,他把孙有元放到床上以后,便在屋门外嘟嘟哝哝起来。
“我就怕家里有人生病,完了,这下损失大啦。多一个吃饭的,少一个干活的,一进一出可是两个人哪。”
我祖父在床上一躺就是一个月,后来虽然能够下地走路,可他从山坡上滚下来后,腰部永久地僵硬了。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孙有元,在看到村里人时的笑容,比我祖母突然死去时更为胆怯,我清晰地记得他脸上战战兢兢的神色,他总是这样告诉别人:“腰弯不下去。”他的嗓音里充满了急切的表白和自我责备。突然而至的疾病改变了孙有元的命运,他开始了不劳而食的生活。在我离开南门前的不到一年时间里,这个健壮的老人如同化妆一样迅速变得面黄肌瘦了。他作为一个累赘的存在已经十分明显,于是他开始了两个儿子轮流供养的生活。我就是在那时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叔叔。祖父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就独自出门沿着那条通往城里的小路走去。他进城以后似乎还要坐上一段轮船,才能到达我叔叔那里。一个月以后,总是在傍晚的时刻,他蹒跚的影子又会在那条路上出现。
祖父回来的时候,我和哥哥会激动地奔跑过去,我们的弟弟却只能干巴巴地站在村口,傻笑地看着我们奔跑。那时我所看到的孙有元,是一个眼泪汪汪的祖父,他的手在抚摸我们头发时颤抖不已。事实上我们充满热情的奔跑,并不是出于对祖父回来的喜悦,而是我和哥哥之间的一次角逐。祖父回来时手中的雨伞和肩上的包袱,是我们激动的缘由。谁先抢到那把雨伞,谁就是毫无疑问的胜者。记得有一次哥哥将雨伞和包袱一人独占,他走在祖父右侧趾高气扬,我因为一无所获而伤心欲绝。在短短的路程上,我一次次向祖父指出哥哥的霸道,我哭泣着说:
“他把包袱也拿走了,拿起了雨伞还要拿包袱。”
祖父没有像我指望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