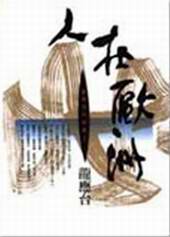人在欧洲-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是一个Stasi,在一个农机场里掌管几百个人的思想“忠诚”资料,
“他?”铁匠酒喝得陶陶然,脸红红的却突然生起气来,“他?你知道他让多
少人坐过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诉你,革命了,这种人不坐牢简直老天没
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头发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园角落里坐下。或许因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东德
人,他觉得轻松,话渐渐多起来。
“社会主义不可能全是错的,它照顾了穷人也庇护了弱者。我们只是经济搞坏
了,应该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胡搞。市场经济哪里是一夜之间可以变过
来的?你看嘛,现在东德的工厂一家一家倒闭,农产品一车一车倒掉,失业的人,
这个月比上个月就多了一倍——整个东德一团乱,所有的规则都不算数了,新的规
则谁也不会,谁也不知道……”
“何内克?我觉得何内克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周围的人,误导他——他是个七
十几岁的老人了,人老了总是头脑不太清楚……”
铁匠咕噜喝一大口,说:“该枪毙!何内克该拉到墙头枪毙!他把一千七百万
人的幸福给毁了,这罪不算重吗?柏林围墙上的守卫?该枪毙!他们明明知道越墙
逃跑的人只是追寻自由,是无罪的,他们却举枪射杀,这是谋杀罪,那些守卫是谋
杀凶手,应该一个个找出来,公开审判……”
铁匠在遥远的那一头坐着,他听着音乐,打着节拍,很愉快的样子。他是伊贡
的亲家。
彼得弯下身来帮一个小孩系鞋带,系好鞋带,孩子像风一样地飞走,彼得沉郁
地说:“那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怎么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样的痛苦的问题,四十年前曾经椎心泣血地问过:
“服从国家命令还是固执个人良知?”为什么悲剧的历史总是不可避免地重复。
“到今天,”彼得扬起头来,面对阳光,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都不否认我
是个共产党员。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见风转舵的人。昨天还在喊社会主义万岁,
今天却变成民主斗士,在街头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里的血可以一转
眼换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岁了,你知道吗?”彼得的眼光追随着一只黑色乌鸦,停栖在
苹果树上,他突然转过来直直看着我,好一阵子不说话。然后哑声说,“到了六十
四岁,人家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全走错了路——
“哈!干杯吧!”
他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
乌鸦拍拍翅膀,飞走了。
毒 药
我想沿着花园筑一道墙,木板篱笆就好,给爬藤穿梭的空隙,也给松鼠和野兔
钻进钻出的余地,过路的行人却望不进来,我们可以袒胸露肘地晒太阳。
“不行啊!”德国邻居警告着,“您得先给乡公所营建组打个电话问问,可不
可以建墙,好像有不少规定哪!可别建了之后又得拆掉!”
营建组说,花园围墙如果不高于一公尺半,只有一般的限刺,譬如围墙不能占
据人行道.墙上不能张贴商业广告等等,如果超过一公尺半,就得到乡公所特别个
案申请,那个时候,营建组就必须实地视察,决定你所申请的墙高度、材料、格调,
是否会破坏社区的整体和谐和美感。如果一整条街都是花木扶疏的树篱,他们就不
会容忍你建起一道监狱似的水泥墙,譬如说。墙上有绿色的爬藤,人人欢迎,但若
是你要把墙漆成救火车一样刺眼惊心的颜色,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好吧!我要筑一道一公尺半高的木篱。
木板运来了,沙子也卸下了。园丁开始打洞、钉桩子。星期五的黄昏,木篱已
经筑了一半。
“很快了!”他说,边跳上小卡车,“我星期一上午九点就来继续。周末愉快
啊:”
人行道上留着小小一堆沙。
星期一,上午九点。门铃响着,很准时的。
站在门口,不是园丁,是个警察。
“请问那堆沙子是你们的吗?”
他指指人行道。
“阻碍行人交通,请马上把它移走。”
“等一会儿园丁就来上工,马上要用到那堆沙,用完就没有了。可以等一等吗?”
“不行。”警察说,他知道那堆沙从星期五晚上就在那儿,过了一个周末。他
不曾早来,是因为不想打扰我们周末的安宁。现在可已是星期一上午九点了!
没话说,我马上开始搬沙。
邻居海蒂看到了这一幕,笑眯眯地说:
“你可领教到咱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了?!去年夏天,我们院子里苹果树枝长得
太盛,枝叶隔墙伸到人行道上去了,没注意剪它,路人就打电话到派出所去告状了!”
对门的考夫曼太太兴致高昂地说:
“瑞士人比咱德国人更要命。我们不是在早晨起床之后,都会把被褥披在窗台
上晒晒太阳、透透空气吗?哈,在瑞士呀,过了早上十一点,如果你的被子还挂在
窗口,就免不了有人打电话给警察了哩!打电话的老女人,不但认为你懒,而且觉
得你的被子乱了社会条理,严重得很哩。”
夏天,我们到亚洲去了两个月,回来时,发觉院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结实累累,
池塘里的莲花早已谢了又开,开了又谢。草坪长满了野花野草,蜜蜂闹烘烘的,好
像载不动躯体里沉甸甸的蜜,不断坠进人的酒杯里去。
木墙外的人行道上,野草一簇一簇地从砖缝中愤然昂起,迎着阳光,显得特别
油绿,有的还开着黄色的小花。
那条小道,因此很有一种颓弃阑珊的情趣。
门铃响了,打开门,是个制服整齐的警察。
“您是这儿的房主吗?”
“是的。”
“有件事情想拜托拜托您。”他合掌,作出恳求的姿态。
奇怪了,我想,是乡里要借用我们的家做什么事吗?有什么恳求如此慎重?
“麻烦您到这儿来看看好吗?”他挥挥手。
我们站在那条我认为颓废又美丽的人行道上,石隙里的小黄花在风里摇曳。
“拜托拜托,”他说,“您能在下星期之前将这条路清铲干净吗?铺在地上的
松针也得清走。还有,不只这段人行道是你们的责任,从人行道缘往马路伸进的一
点五公尺路面,住户也都有义务清扫。拜托拜托。”
上车前,他再加重语气:
“下星期我可得来检查哦!可别等着罚款啦!”
周末,邻居看见我们一家三口在人行道上拔草、扫地、剪树枝。扫把、畚箕、
剪刀,散置一地。四岁的孩子拔了草之后,正目不转睛地研究石隙里的蚂蚁。
施密特太太走过来,手里拿着个小瓶子,“用拔的您们要拔到哪一天?您看,
有这种除草药水,很有效呢!”她举着小瓶子,“混在水里,浇在路面上,就不会
再生野草,一年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毒药的妙用,可是毒药流进土地,渗进地下水,对自然环境没什么好处,
而且,我喜欢拔草,晒晒太阳,未尝不是种享受。
蒲公英的根生得很深,拔不出来。
施密特太太看看四周,压低声音说:
“一定是五号那家老夫妇去告状的,老人家最吹毛求疵了。”
一会儿,考夫曼太太提着菜篮子晃过来:“好辛苦啊!”
她看看四周,悄声说:
“一定是施密特太太打电话给警察的,他们看起来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海蒂搁下脚踏车,漫步过来,笑着说:“德国人就是这样,讨厌天下太平静了,
所以鸡毛蒜皮都看成天大的事。你可别太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我纵声笑了,邻居的善意安慰令我忍俊不住,他们何从知道,在我来到这“讨
厌的”、“一板一眼”的德国之前,我住在一个多么不一样的社会呢?!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来到。红砖人行道上,突然摆起了面摊。老板娘手脚利
落地撑起布篷、架起桌椅板凳,老板开始洗锅洗碗洗菜。客人欣然入座,先吃面、
继之喝酒,继之划拳唱歌,继之口角打群架,老板把唱机开到最大音响,培养气氛,
我们在屋里挣扎睡着,等待天亮。
油腻和烟火终于使人行道上的红砖变成黑酱色,鞋子踩过往往就黏在地面,不
能拔脚。有一天,大概有人和面摊老板取得了协议。那个傍晚,面摊没有搭起来。
倒是来了许多工人,七手八脚地搭起了一个大帐篷,占据了整个人行道,还有半边
行车的大马路。
有人要办丧事了。
供着死者照片的道场布置起来了,摇着铃的道士、唱着佛的和尚、吹着唢呐的
中乐队、打着大鼓的西乐队、对着麦克风嘶喊的“白衣孝女何秀子”,还有那受雇
而来五人一组的“五子哭母”公司哭成一团,还有那脸上涂了白粉不知是男是女的
人。边唱边扭腰……
日日夜夜,在我们的人行道上。
我曾经多么盼望警察的到来。那个时候,我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板一
眼”的女人,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告状,耳边还有忘了取出的耳塞。偶尔,警察因为
不堪其烦而来,总带着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摊贩都是可怜人,为了生存,没办法
啦!你也要同情同情嘛!”或者:“作丧事,中国人情嘛,反正丧事也不会天天有,
忍一忍就好了。”
当然,我实在也不太有抱怨的权利,只是一个房子外边的人行道罢了;我知道,
有人在买了新公寓之后,发觉楼下人家突然变成一家铁工厂,电焊器和打铁机每天
激炸着金属摩擦相撞敲打的巨声,也有人突然注意到隔壁紧邻每晚发出缠绵而不可
道人的呻吟声,门上已经挂出“按摩”的招牌,大人忧愁着不知怎么告诉年幼的孩
子“不要到隔壁去玩——”
而同时,在我们大楼的顶楼空地,我发现有人运来了沙石水泥.正在建不知属
于谁的小屋,一栋又一栋……奇怪,当初买卖契约中不是写明了:“顶楼空地由住
户共同使用”吗?
拔掉最后一株固执的蒲公英,我们这段人行道就像整条街其他路段——样既整
齐又清洁了,只是失去了一点阑珊浪漫之意。往后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是拔草的
日子。草,尤其是石隙里的野草,长得比日子的更迭还快。于是有一天,我也去买
了一个小瓶子。
面对着六十公尺长的人行道,看见黄色的野花星星似地点缀着路面,我领悟到,
我从一个以任何理由都可以牺牲整洁和秩序的社会,来到一个为了整洁和秩序可以
牺牲许多东西的社会。“为了整齐,”我想,一边把小瓶子里的液体倒进水壶里搅
和:“下毒也在所不惜吧!”
我开始浇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
我的手里有一块钱
1
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
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
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
“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
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
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时光里的欧洲 (完结)作者:郝景芳 txt下载[出书版]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