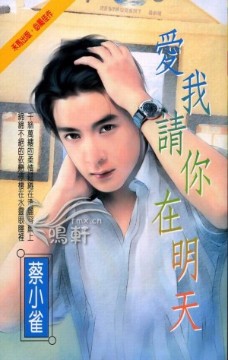你在高原 张炜-第1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妈妈说:“你心里明白就行,不过你还是要走。你如果在这个小茅屋里,不等你长大长壮——也许就是明年吧,又会像你父亲一样被送到南山,再不……那时你就什么指望都没有了。趁着你还小,蹄子还轻快,能跑就快跑吧,跑吧,自己逃出去吧……到那边你可不要忘记接上读书,不要忘记……”
这天晚上妈妈最后一遍叮嘱,我含泪点头。不过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可以走,我可以踏着父亲的足迹一直走到那座山里,但我不会去找什么“老孟”,更不会去给一个陌生的人做儿子。
出逃
1
第二天早晨,天还不亮,大约只有三四点钟的样子,我就被喊起来了。我一夜没睡,妈妈也没有睡,只有那个可恶的父亲在隔壁里打着呼噜。妈妈走过来,她也许早就走过来了,因为我一睁眼就发现她坐在床边。她抚摸我的脸,抚摸了一遍又一遍。她把我从枕头上扶起来,这会儿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小孩子。可是我自己知道从今以后我就是一个大男人了——床边是一个挺大的包裹,我将背着它进山……妈妈告诉我:要趁着天不亮摸出园子,在园角上的那棵桃树下边有人接你。我知道那人就是小泥屋里的邻居,他会把我送走,然后交到一个尖下巴的人手里……我吃了一点儿东西,把我们的小茅屋看了又看,背起了那个包裹。
走了两步我又听到了呼噜声。
我想起了什么,想最后看一看那个打呼噜的老头,想看清他的样子,以后好好恨他。
就这样我走到了西间屋——父亲,就是那个又丑又老的人,这会儿仰躺着,在那儿发出了一阵阵急促的呼噜声。他睡得好香啊,这个该死的,他睡得好香。他毁了母亲,毁了外祖母,毁了我们全家,最后又毁了我。
我走到了床边。他毕竟是我的父亲哪,我要最后记住他的模样。
妈妈大概完全理解我的心思,那时她点了一根蜡烛,凑前一步把那个男人的脸照亮了。
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奇怪的事情,后来一辈子也没有忘记:我发现父亲打着呼噜,一声又一声打着,越来越响,可是他紧紧闭着的眼睛里竟然溢出了泪水……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62)
我正疑惑,母亲就扯了扯我的手。我想我不能耽搁,转过身大步走了出去……
我很小心地沿着树底、猫着腰往前走。母亲就跟在我后面几步远的地方。走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什么尾随着我,是比母亲的脚步声更为柔和细腻的一种响动。我感到了什么,驻足不前——这时那个声音也没有了——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不得不继续往前——我终于发觉了一个细小的影子,它沿着树下的地垄往前跳蹿……我的心头热了一下,把手挡在嘴巴上轻轻地打了个口哨。
那个小小的身影跳到了树上。
我就这样走走停停,最后走到了园子一角的那棵大桃树下。那个叫老骆的邻居扯了扯我的手,我们就上路了。走出园子,走到丛林尽头时,老骆把我交到了一个早就等候在那儿的人手里,这个人就是尖下巴。
我和尖下巴整整走了好几天,走到了重重叠叠的大山里。一路上他常用闪烁的眼神看我,只不说话。我也不说,我讨厌他。许多年之后我还记得他不断牵拉我的那只手:冰凉而瘦削,汗漉漉的……
进山之后,最令我吃惊的是这山的颜色——从我们的小茅屋往南望去,这大山一片蔚蓝,好看极了,而且总是那么神秘;可这会儿我看到的却是干黄干黄的土山,石头也不是蓝色的,裸露的石头甚至也是土黄色的,或者是长着斑点的青黑色。总之这是让人失望到极点的一片大山。我从来没有到过山区,这会儿感到透心的沮丧,尽管还有一丝丝好奇。山路难行,时而靠近深不见底的山涧。我想在这细细的小路上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当然了,半空里的树丫会把我接住,可那时候我的身子一定会被扯得稀烂……
走了一天,前边出现了一个村落。在这个村子里,尖下巴的中年人把我交给了一户人家。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就是“老孟”的家。我错了,“老孟”住得更远更远。这一户人家据说只是尖下巴的亲戚。他们在这里招待我吃了一顿午饭——一种用淡水鱼做成的包子,好吃极了。
包子是用菜叶和鱼肉掺和一块儿做成的。我记得自己一口气吃了五个包子。吃过之后那户人家告诉,从今以后我的父亲就是“老孟”了——他没有儿子,我要负责给他养老送终、要对得起他,他自然也不会亏待我。为了找我这么一个儿子,他一辈子的积蓄全搭上了!那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烧了一辈子砖窑和烤烟炉,那真是一个好人……
“积蓄”两个字像石块一样砸了我一下,我吓得全身发紧——有谁把我卖掉了吗?是谁?尖下巴?我的爸爸和妈妈?最后一个问号让我差点跳起来大喊……我咬得牙关乱响,忍住了。最后我一口气把什么都答应了:我一定听话,一定会做那个老人的好儿子。
就这样我们起身了。我要去见自己的义父了。
2
一路上我都咬紧了牙关,我只在心中诅咒。
走啊走啊,一口气走了几个钟头,我们终于深入到了大山的最深处。这座山变得真正险要高大起来,那时候我不知道最高的山就叫砧山。看到这些高山,我觉得像来到了一个奇怪的世界。那个小茅屋,那片荒滩,那里的大李子树、海棠树,我度过了童年的一切景物,好像一下子都变得陌生而遥远了。它们渐渐变得与我毫不相干……一路上只有那个跳动的黑影一直在伴着我,伴着我。我觉得它从果园里开始就一直在暗暗跟踪我、护佑我。它的四只爪子在这高山之巅跳跃不止,它在走一条与我完全平行的路线。有了它在身边,我想我不再那么害怕,而且以后也会生活得幸福安逸……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63)
翻过大山就来到了一个村庄,我想我就要归于这当中的一户人家了,我从现在起就要属于一个孤老头子了。这样想着,尖下巴却并不停步,还在往前急奔。后来我们穿过了村庄,又走上了另一座大山。在山的半坡上,月色下可以朦朦胧胧看到一个孤房子。那个孤房子的旁边就是筑起的一座高高的烤烟炉——原来那个孤房子里就住着我未来的父亲!
在我打量那个小屋的时候,尖下巴伸手指点起来,可他说了些什么我差不多一句也没有听清。一颗心咚咚跳,那个小屋也在我的眼前闪动跳跃。我不知怎么脚步迟缓起来,后来借故解溲,就到路边的一个大石头下边蹲了。这样蹲了一会儿,我才突然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再也没有比从这儿逃开更好的了。
我小心地摸索着往后退去。我退呀退呀,直退了十几米远,然后一猫腰就向另一块大石头奔去了。在那块石头后面我探头望了望,见尖下巴还在那儿着急地观望。这时候我悄悄说了声“对不起了”,就撒开腿猛跑起来。
我的脚踢到了石子上,石头沿着山坡哗哗往下滚动,发出了咕咚咕咚的声音。又跑了一会儿,我听见后面的尖下巴被狼咬了一样,嚎着骂着。我顾不得这一切了,一直向前、向前。
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跑到了哪里,反正直到太阳冒红的时候我才停歇。我记得当坐下喘息的时候,这才发现衣服大部被撕烂了,脚上胳膊上全是血口;眼前是一条清清的河水:河水清极了,借着黎明之光我差不多看到了水下的小石子、沙子、沙子上的几条游鱼。我跪在河边捧了水喝,这才发觉自己渴得真厉害,这河水真甜啊。我喝啊喝啊,一口气喝得肚子鼓胀。我从包裹里翻出了几块红薯吃起来,后悔包裹里没有火柴,不然我就可以在这儿生一堆火了。我身上有些冷,摸摸身上,到处都湿漉漉的。山里的夜气真重啊,它把我全身都打湿了。
这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离我不远处的山溪里,正有一对机灵的眼睛盯住我。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只小兽,是它的眼睛在注视我啊——从现在起,它将伴我流浪……
第六章
寻找小屋
1
大概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即如果时间能够倒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一遍就好了。是的,这种梦想之中就包括了无尽的追悔和思念,以及其他。时间像水一样流过了,一切都无以弥补,无从捕捉,也没法寻觅新的开端……我常常想到的是,我在当年如果能够用另一种方式对待柏慧,如果能从稍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她,不那么恐惧和慌乱无措,那么整个事情就将是另外一种结局了。比如,我干脆对她讲出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家族的全部——或者相反,做到真正的守口如瓶、一丝不漏……总之那种恐惧不安和小心翼翼、遮遮掩掩和欲言又止,反倒容易造成更大的误解。事发之后我却没有了一点儿理性和最起码的镇定,几乎从来没有试着去理解和修复,没有往这个方向探索过一点点可行性。我仿佛是一个应声毙命的丛林动物,从此彻底失去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关于父亲母亲,关于童年和整个家族的悲惨命运,关于这一切的禁忌和隐秘,还有深不可测的痛苦和仇视,让我变得那么勇敢决绝而又超常脆弱。你不能碰,不能染指,不能侵犯,甚至不能有一点点这样的企图和一点点的尝试。所以,我和你之间就注定了是那样的一种结局。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64)
我今天至为惋惜的不仅仅是因为失去了这个皮肤微黑、风韵迷人的姑娘,也不仅是因为一场热恋的失败,而是与之连在一起的那些深刻的误解和伤害。这伤害如果仅仅存在于我一个人的心中就好了,不,它是彼此的;它尤其关乎到我们整个的家族——那个光荣而又不幸、雄心勃勃却又一筹莫展、最后是任人宰割的家族。正是这种来自爱人的深深的伤害,才造成了我长久的、铭心刻骨的痛苦。这种痛苦他人无法理解。
作为那个家族的后来者和幸存者,为了生存和尊严,还有自身的禁忌,守卫隐秘正是我的权利,更是我不可推脱的义务和命运。
不过我现在常常设问的是,那个皮肤微黑的姑娘当时真的就没有权利知道那一切吗?是谁剥夺了她的这种权利?是一种血缘,一种时代的惶恐,还是因为她是柏老的女儿?今天看是再清楚也没有了:她还不是我眼中的“自己人”——显而易见,对于我来说她直到那时候还是另一种人,这正像柏老他们一直将我视为“异类”的道理一样。这就是血缘的残酷……
这个浑身散发着栀子花味的姑娘当时只有二十岁。那会儿她对于我、对于一个来自山野的青年一无所知,可以说什么也不懂。她不过是怀着合情合理的好奇心和刚刚萌发的一丝钦羡,与我越走越近罢了。在后来的时刻,在彼此难分难离的日子里,她自然而然地就要问到我的父亲。这一声平淡无奇的询问在我心中激起的波澜,她倒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当然,我必须向她掩藏真实的父亲,而只说出义父——那还是一个相当寒冷和无情的岁月,我的这种提防毫不多余,后来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当她后来执意要与我一起去看那个山里老人时,我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拒绝。
我当时吐出“父亲”这个要命的字眼时,心里咯噔响了一下……我马上想到的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