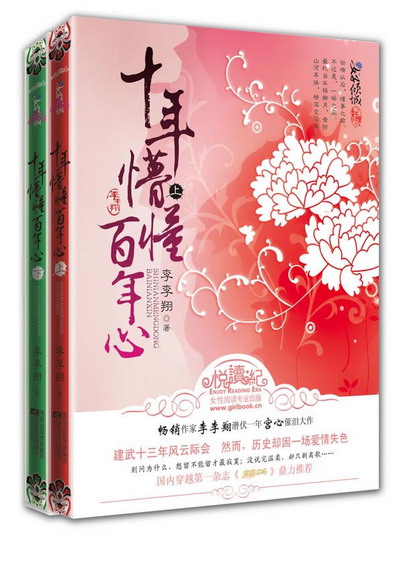饥饿百年-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我晓得是你去捡,”建申说,“我不会跑那么快。”
何大有些感动。
“何大,我们俩一起过好吗?讨来的东西,分着吃。”
何大觉得这是一个不坏的主意,但他对建申说:“我不能回何家坡……你要是回去,也不能对何家坡的人说我在哪里。”
“你是怕坤章么?他死了,比我爸爸还先死几天。”
“死了?”
“死了!他婆娘现在是李篾匠的婆娘了,就是从李家沟过来的那个李篾匠。”
“李篾匠还没走?”
“他反正就在何家坡周围转。听陈四娘说,他早就跟坤章家的搞上了。”
两人一起乞讨,胆子壮了不少,可在本质上并不能改变什么,该挨饿还是挨饿。他们在清溪场乞讨了几天,何大觉得集市上看起来吃的东西多,可没一样属于自己,要从拥有者手中讨得一份,比从乡下人那里讨困难十倍。于是他们相约到了附近的乡下。
晚上,他们趁主人睡下之后,就躲到人家牛槽里栖身。牛槽里蚊子虽多,可安全,牛粪一发酵,暖烘烘的,连冬天也不冷。何大后悔以前独自一人时为什么没想到这一招。
没过多久,就明白了这一招是很危险的。
那天,何大和建申挤在一个牛槽里,睡至半夜,牛伸头到槽里寻余草,草没找到,却碰到两张人脸,那头慈祥的老牛,用头轻轻地拱这两个小孩,还用舌头舔他们的脸。建申首先醒过来,想起自己的处境,“嘤嘤”地哭泣。何大也醒了,见牛栏猪圈里照进来的冷月,听着同伴的哭声,禁不住悲从中来,也轻声啜泣。何大一哭,建申越发伤感,竟大发悲声。建申的哭声惊醒了主人,主人先以为是鬼哭,吓得不敢动弹,继之听到牛槽里的说话声,就蹑手蹑脚地提着马灯走过来察看,竟是他娘的两个讨口子!这简直是晦气!主人举起淘粪瓢朝他俩的头上砸来。何大溜掉了,建申缺乏经验,缓了一步,头上被扣下一瓢,屎星子罩住了眼睛。主人还要追打,何大带着建申,逃到了黑暗的田野里。
“两个人一起就是好,”建申说,“今天要是没有你,我不就挨打了么?”说罢嘿嘿地笑。
但这之后不久,他俩就分开了。
隔阂起因于一次特殊的乞讨。
那天,他们到了王家坝,也就是王维舟的家乡。王家坝是一块很大的平坝,形如鲤鱼。其对河是侯家坝,长河穿过,使两块坝子像蝴蝶的翅膀。何大和建申沿着河滩一段沙地上了王家坝,见许多穿红着绿的人结队而行,走向大坝中心。紧接着,十余童男童女打着彩旗走来,后面跟着七八条大汉,背着立柜箱子等物。无疑,这里的一个大户人家结媳妇了。那不,一顶大花轿在几个壮汉的颠簸下晃过来,轿里发出一声接一声压抑着的尖叫。大汉们来了兴致,颠得越发没了体统。新娘受不住,要求下轿。壮汉们求之不得呢,就把轿歇了。那搭着盖头系着花绸穿着花衣花鞋的新娘从轿里出来,脚一点地就将盖头扯去,露出泪光烁烁的双眸,在十几个妇人的簇拥下缓步而去。那些背着重物走在前面的大汉便歇了打杵,吆喝道:“妹儿,把烟发起讪!”新媳妇索性止了步,任随汉子怎样吆喝,任随身边的妇人怎样劝解,就是不挪动一步。汉子知道无望,便扯开嗓子,扮成男女两角唱起野调:
一枝花花出墙外,
蜂儿见了笑开怀。
蜂儿蜂儿你莫笑,
我花原不为你开。
闻到花香我飞来,
你花怎不为我开?
我花已被情哥采,
情哥把我叫乖乖。
你若亲亲赛情哥,
明年我为你来开!
汉子唱着野调,已走出老远。这时候,新娘才肯举足。
建申说:“何大,我们今天可要吃一顿好的了!”
何大说:“快走!”
一枝花花出墙外,
蜂儿见了笑开怀。
蜂儿蜂儿你莫笑,
我花原不为你开。
闻到花香我飞来,
你花怎不为我开?
我花已被情哥采,
情哥把我叫乖乖。
你若亲亲赛情哥,
明年我为你来开!
汉子唱着野调,已走出老远。这时候,新娘才肯举足。
建申说:“何大,我们今天可要吃一顿好的了!”
何大说:“快走!”
坝子正中是一个大四合院。进院门前,何大和建申约好,不能一同前去,否则就可能被识破。只要他们分开走,挂情的人就以为他们是某家的小孩,不予过问。何大先去,挂情者见他那一头乱而脏的长发,立即起了疑心,喝道:“哪里来的!”做贼心虚,何大支吾起来。“打讨口子!”挂情者暴起一声,惊动大坝,惊动长河。
“打讨口子!打讨口子!……”院门口混作一团,何大的头上、脸上、背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和石头砖块。他放步跑去,一口气跑出老远,待吼声渺茫了,才停步喘气。
平坝上不管跑出多远,回过头都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不过,人的脸孔已不大看得清晰。人群中没有建申的影子,何大知道他趁乱溜了进去。他出来的时间短,头发不至于那么长,那么脏,溜进去也不会被揪出来。
何大坐在河滩上,抚了抚痛处,就专心致志地等建申。建申出来,一定会给他包几片肉和几个面筋团的。这里的风俗是,坐大席的时候,主人家都要为客人发草纸,方便客人把好吃的分出一点,给家里人包回去。客人上席的时候,草纸也就发到手上。如果主人吝啬,舍不得草纸,或者主人穷,买不起那么多草纸,也无关紧要,家家户户的地坝边都种着芭蕉,揪下一片芭蕉叶,照样行事,且经芭蕉叶包过的食物,会发出一股醉人的清香。何大一想起肉和面筋团,清口水直冒,恨不得建申马上向他飞跑过来。
可急是急不来的,看今天这家主人的阵仗,至少要安三十席,农村找不到那么多八仙桌,一般是五六席一轮,三十席就得安五六轮,建申个小,多半挤不上前几席。
清溪河淙淙而去。清溪河的美,在王家坝一段显出了它的极致。这里的河道比上游宽阔许多,碧蓝的河水,柔和地漫过去,使整个大坝成一片水乡,浅绿的金鱼藻,在河岸边摇曳,露出黯黑脊背的小鱼,在水草的根部穿来绕去。河床都呈缓坡状,缓坡上纤草萋萋,闪动着粼粼碧光。河水发出音乐般的声响,那东一丛西一丛散淡的人家,就在这音乐声中过着光阴。
建申比何大想象的回来得还晚,他来到何大身后,何大还兀自沉浸在遐思里,他大叫一声,吓了何大一跳。
建申并没给他包肉或别的东西!
“老子吃了两席!”建申从沙堤上跳下来,坐在何大身边,一边抹着闪着油光的嘴,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老子吃了两席!我挤上头席,吃了个饱,接着又吃二席。根本没人发现我!那家人蒸了扣肉,还煎了滑肉,油粑粑是不消说的。一片扣肉挑起来,筷子都要闪断!一席可以吃四片肉,我一共吃了八片,坐头席的时候,还把旁边一个老汉拈到草纸上的偷吃了一片,加起来就是九片!嘻嘻……”说着,建申响亮地打了个饱嗝,豪豪一股热气流,从缺了三颗门牙的嘴里直冲而出,浓浓的油星子味,使何大满口生津。
何大流下了眼泪。他觉得朋友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因为他遭打的时候,建申肯定是看到了的,建申分明知道他没能挤进院子坐上席,可是,建申却不给他包肉回来!
见何大流泪,建申说:“你怪不着我,哪个让你那么笨?他们把你打出来,你不晓得再溜进去?那个院子又不止一道门。”说毕,建申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又说开了:“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些,还有绿豆芽、炒豆皮、干洋芋片汤、干豇豆汤,都是用肉汤烧的……”
何大没有听完,站起来走了。两人就这样分道扬镳。
乡下的黑夜让人害怕,如果晚上不能睡牛棚,还不如到场口上去。
于是何大又回到了清溪场。
说东巴场跟清溪场“差不多”,应该说只是东巴人的自大,事实上,它们唯一相似的,就是河沿的吊脚楼,街有多长,吊脚楼就绵延多远,每座吊脚楼都用两根表皮发黑的木棒斜斜地撑起来,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却是人踏不翻,水冲不垮,也是奇迹。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上,总守着一个供水手享用的多情妓女,这里倒不,这里的水手向来比湘西水手更辛劳,更穷,这两样东西足以打垮一个男人肉体上的欲望。既然水手们缺了那份激情,清溪河上的浪漫女子也懒得守在吊脚楼上眼巴巴地等“我的人儿”了。这里的吊脚楼主要不是用来望人,而是做了堆放杂货或晾晒衣物的处所,有的还用来做了厕所,雾气蒙蒙的清早,歇在河上的水手如果定了睛看,常常可以望见白白的女屁股蹲在那里撒尿。
东巴和清溪相似的就是这点儿了,要说热闹,清溪远远超过东巴,虽同样没什么显示威严的城墙,但街道比东巴场多出好几条,东巴场的街道人们说是狗肠子,独独的一根,清溪场的街道分出了好几支,稍不熟悉的,就知头不知尾。东巴场的街面,全是土路,而清溪场的,则是清一色的石板街,石板厚重,光滑,本是从对河马伏山上开下的白石,年深日久,全都青幽幽放光,热天再多的人挤在街上,既无灰尘,又觉凉爽。这也难怪,东巴场只管东巴乡,只是偶有老君乡的人下来,清溪场却与三乡毗邻,人们自然就把这里当成了物资集散地。
商业活泛起来,当时清溪场一个老秀才在一篇文章里,借用战国时苏秦盛赞齐国富有的话夸张道:“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这里的居民普遍比东巴场上的富有,王维舟故里王家坝和对河的侯家坝,也比东巴的黄、钟二坝丰茂润泽。
要说何大真正见了一点世景,也是在清溪场上。
清早,街道静得出奇,青石板街在熹微的天光底下,暗黑暗黑的,像一条大鱼的脊背。当它渐渐显出本色的时候,正街的中心便响起特有的叫卖声:“碗儿糕哟——碗儿糕哟——”叫卖的是一个老妇人,总是把“碗”吐得很重,很长,“儿糕”一滑而过,“哟”字被她吞掉,就像一声无奈的叹息。到中街与上街连接处的警署门口,必有一个瘦长身材的灰衣兵士,喝一声:“等倒!”老妇人便停止吆喝,站住不动,灰衣兵士端着长身窄面筲箕,走到老妇身边,认真挑拣五个碗儿糕,也不付钱,转身走了。这是他孝敬警备连长的。灰衣兵士进去之后,老妇人立即收回挂在脸上的笑,把几滴凄苦的清泪洒在无言的大街上,推着“鸡公车”,走上几步,才想起她的职责,“碗儿糕哟——碗儿糕哟——”地叫卖。如果是冷场,老妇人的叫卖声要响到中午时分,逢赶场天,上午十点左右,她的声音就会被嘈杂的嗡嗡声淹没。
整个白天,街上几乎都有吵架的。打架的却极少,如果你看着他们马上就要打起来了,证明这场架快吵完了。这里浩荡的水,培育了人们的水性。黄、钟二坝也被水包围,坝上人的性情,却暴桀粗粝,要不是远古祖先性格的遗传,真是没法解释的。
清溪场居民的水性,体现在男人疏阔流动的品格和不尚孔武的性情上(王维舟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女人身上。这里的女人都漂亮,长眉秀目,腰段子又好。她们说话,总带着一种涩涩的嗲气,有事无事打着眼风,即使周围没一个人,也爱东瞧西望。在石拱桥头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妇人,一到赶场天就打扮得妖妖娆娆,搭张竹凳坐在门边补衣服或打线袜,一坐就是一整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