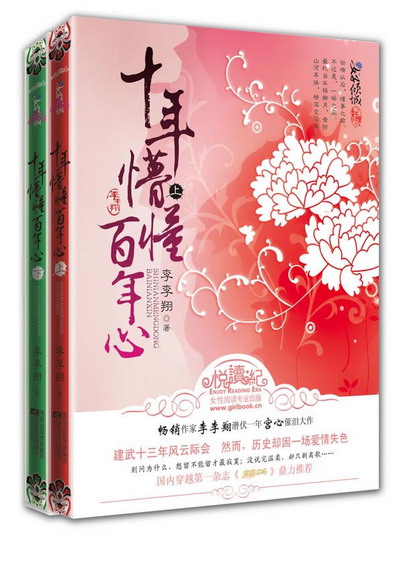饥饿百年-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河坝与山上不同,河坝的夏天已经是正正经经的夏天了,河水响铴铴地流着,小草翠汪汪地亮着,庄稼繁茂地生长着。河坝的天空也与山上不同,河坝的天空更低,更沉——为什么爬到越高的山上,望到的天空越是高远清寒?难道河坝与山上望到的不是同一个天空?这事情,何大一辈子也没想明白。
这天清早,何大沿河走去。在他的印象中,沿河走很远很远,再过河上山,爬一阵,就到了李家沟。具体有多远的路程?把脚走肿就是它的长度。这是他跟杨光武和刘氏逃到何家坡时留下的经验。他跟母亲许莲、弟弟何二去李家沟时,大半路程是许莲搂一个背一个,行路的艰难,他并没体验到,跟杨光武和刘氏到何家坡,毫无疑问就全靠他自己走了,他的脚肿得不行,因此,他认为只要自己脚走肿了,也就肯定该过河了。可这一次,从早上走到晚上,他的脚也没走肿,也就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过河上山。何大已经习惯了在野外度过黑夜,并不害怕,可是他饿了,肚子空得发慌,后来就痛,再后来,就不光是肚子痛,整个身上都痛,可又指不出痛在何处。是一种窝窝囊囊的闷痛。他蹲下身,从河里撩起水,咕嘟咕嘟地往肚子里灌,起初很管用,塌下去的精神一下子提升上来,过了一阵,再灌水不仅解不了饥饿,仿佛全身的皮肉都被水发胀了一样,走起路来一荡一荡的,沉重而飘忽。周围不是找不到可食的庄稼,河岸十余丈高处,就是梯田,坝下庄稼成熟早,胡豆大多被收去,可还有豌豆,豌豆已经干浆,连续好些天,彩色的阳光赋予了它石质般的硬度,对何大嫩弱的牙齿是一种考验,但于他而言,只要是可以果腹的,就是他的至亲至爱。此外,小麦也已成穗,麦粒儿已具雏形,巴掌大的田边地角,还种着涩涩的、表面如青蛙背脊般的牛皮菜……然而,何大惊惶未定,加上人地生疏,不敢轻举妄动,何况那些梯田不像何家坡的藏在密林之中,而是亮在明处,只要举着灯火,老远望过来,一眼就看个透。这让他既不敢偷豌豆,也不敢偷麦子。
何大怕走岔了道,不敢继续向前,站在河沿,彷徨四顾。在离他数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处灯光,灯光之下,晃动着几个人头,他们弓腰驼背,都在忙碌着,一种非常陌生的闷响,从那里发出来。何大没加思考就向那边走去。他的整个身体都只传递给他一个信息:要饭。
刚走到门边,就见几个浑身油污的人,每人碗里盛了红苕饭,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热烘烘的米香,混合着热烘烘的烂红苕气味,构成无法抗拒的诱惑。何大说:“我想吃饭。”
话音落下去的时候,人已仆地。
几个油污汉子放了碗,把何大扶起来,来不及问话,就给他舀了一大碗饭。
筷子还没送来,何大早已抓了一大把塞进嘴里。
这是一个榨油作坊,用木杠和石扇等简陋工具榨桐油和菜油。那几个工人,都是当地农民,作坊是他们集资建起来的。
工人们让何大吃饱了饭,问起何大的身世,问几声不见答应,一看,他已经坐着睡了过去。
他们把何大放在地铺上,跟他们睡在一起。作坊里是堆积如山的桐子,所谓地铺,就是在桐子上铺一张篾席。
第二天,何大吃了早饭,问往李家沟咋走,工人们给他指了路,就搬桶,上杠子,压石扇,忙碌得赤裸的上身筋骨累累。何大道了谢,沿河向下游走去。原来,他已经走过了十余里。
因为吃了两顿饱饭,何大显得格外精神,很容易就找到过河的地方,过了河,似乎没爬多久,就上了李家沟。
杨光武的住房一点也没变。何大忐忑地走到门边,见木板门被一把大铁锁锁着。这把大铁锁,是他母亲许莲从何家坡带来的。何大从门缝往里瞧,见里面一片狼藉。红、黑、白相间的鸡屎,随意撒在草凳上。傍灶台边,放着猪草板,横放在猪草板上的刀,分明是切菜用的。灶台的边缘黑不溜秋,有时拖下白白的一杠,是滗饭时流下的汤汁。这情形,使何大再次想起他的妈妈。许莲在的时候,虽一样的穷,但屋子里总是干干净净,哪怕她受了杨光武的毒打,自己爬不起来,也要吩咐何大把屋子扫一扫。许莲死后,整洁的杨家变成了狗窝,刘氏进屋,凭借女人的天性,使之有所改观,至少,草凳上是不会有那么多鸡屎的。
现在的情形只能表明:他们的生活是一日不济一日了。
想到这层意思,何大心里很凉,如果他们过不下去,就更不可能收留他。可是,他不留在这里,又能往哪里去?何大在门轴缝里找到钥匙——清溪河流域的农民,上坡干活或去集市赶场,都喜欢把钥匙藏在门轴缝里——开门进屋,拿起扫帚将屋子打扫干净了,又把草凳上的鸡屎擦去,那些已经干浆的鸡屎,用扫帚擦不掉,他就用指甲抠。做完这一切,杨光武和刘氏还没回来,他到里屋去看,杨才没有绑在床上,一定是带到坡上去了。何大一阵心酸,眼泪涌了出来。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他跟弟弟何二也常常被他们带到坡上……
这不是他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也不是他该哭的时候,他用袖子将泪抹去,就进了牛棚。
他曾听杨光武在何家坡说过,将来回了李家沟,就买一头牛。
牛棚里空荡荡的,连地皮都刮起来肥庄稼用了,证明他们并没养牛。没有牛,何大就更加觉得自己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他慢慢地走到屋外去,锁了门,将钥匙放回原处。
不知不觉,就到了母亲的坟边。
母亲的坟几乎只剩下一片平地。
何大蹲下去,“妈……妈……妈……”他这么单调地哭喊着。
在外面游荡了许久,走过了他熟悉的角落,在母亲被黄牯子戳倒的地方,他站了很长时间。太阳偏西时分,何大又转回到杨光武的屋后。屋脊上有了一团一团的黑烟,证明他们已经在做饭。何大没有多想,从一条长着小草洒满粪便的土路走到屋前,喊一声:“爸爸。”
把头塞进灶孔吹火的杨光武听到喊声,缩回脖颈,又揉了揉被柴烟熏得泪水巴沙的眼睛,看到了街檐下的何大,不相信似的张大嘴巴,好一阵才说:“你来了?”
看来,他根本就没注意屋子被清扫干净了。
何大一句话不敢说。
“你咋个来了?”
“我在何家坡惹了祸。爸爸收下我。”
杨光武走出来,问道:“你还没得老子的鸡巴大,惹了啥祸?”
何大就把不小心点燃了别人家房子的事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不过,他作了小小的又是极为关键的改动,他知道陈氏跟杨光武吵过架,就说自己点燃的是陈氏的房子。
杨光武哈哈大笑,“有出息,”他说,“老子收下你!”
何大除了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杨光武低了头看他的脸,怒道:“哭个球啊?”何大又喊了一声:“爸爸……”
不多久,刘氏回来了,她用背条把杨才跟自己连在一起,肩上扛着锄头,见了何大,竟也出乎意料地没说什么。
秋天来临的时候,何大终于被杨光武赶出了家门。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杨家。
沿着清溪河,何大一路流浪,他的头发已经好些时候没有理过,长至脖颈,脏得结成一块饼。当他从官道或村路上走过的时候,一些人就向他打趣:“喂,那娃儿,来给我当儿好吗?”他知道这些人只不过是说着玩的,就懒得答应。要是饿急了,就应一声:“给我一碗饭吃我就给你当儿。”那打趣的人立即噤了声,心肠硬的,不但不给饭,还一边骂,一边捡起石头瓦块向他掷来,他便蒙了头,飞跑而去。
朔风自北而南,翻过秦巴山地,像一支硬弩,直贯清溪河。这是流浪者最为恐怖的季节。何大到了毛坝,这里恶山野水,比李家沟荒凉十分。毛坝住着十来户人家,最富有的是罗光全,他有几十挑谷田,可土地薄,收成并不好。他家有三口人:罗光全的母亲加上罗光全夫妇。罗光全的母亲是瞎子,干不了活,几十挑谷田加上一些旱地,全靠两个年轻人做,惹得罗光全的老婆耿氏常生怨言。因此,当何大在村口出现的时候,罗光全的婶娘就把他带到了罗光全家。罗光全答应收下他。
何大在那里只住了两个月。他放牛,是一对子母牛。除了放牛,还割草,挖地,侍弄冬水田。大山上仿佛永远笼罩着冬天的暗影,早晨出去的时候,黑霜打得石头皴裂,土块发硬,何大穿着烂草鞋、短裤(他的裤子只剩膝盖以上的部分,看上去像短裤)、密布着网眼的薄衫,拉着牛上坡了。当太阳升起,冰雪融化,何大踩着烂泥回来的时候,罐子里只剩下几个荞麦粑。
这几个荞麦粑是他一整天的食物。
首先看不下去的是罗光全的婶娘。她对罗光全说:“光全,你还是给那娃娃沾一颗米嘛。他一天只吃三五个汤粑,哪养得活?”
罗光全轮一轮眼珠回道:“你心肠好,把你家的米拿给他吃吧。”
他婶娘穷,自知说不起硬话,就不敢言声了。
有天清早,何大赤脚站在冬水田里挞田埂,两条细腿像两根红萝卜,罗光全的婶娘背着猪草花篮从岩畔上溜下来,悄声对何大说:“娃娃,你自己另找个地方算了。”何大听从了她,没再挞田埂,从田里出来,用老人递过的一把猪草擦尽了腿上的泥水,离开了毛坝。
何大到了永乐的黄岭滩。这里一户姓钱的人家收留了他。钱家的主人名叫钱元,脾气就跟这里的地质一样,稍不留心,就山崩地裂。何大身上留下了无数伤痕。大半年后的某一天,何大从坡上回来,再也找不到主人的家了。主人的家被突发的泥石流埋没了:天边泛出鱼肚白的时候,泥石流带着低沉的吼声逼向了钱家,何大早已上坡去了,可钱家人全都还在梦中。何大跪在那一堆黄汤面前,为主人痛哭一回,就沿河而下,到了清溪场口。
清溪场口离何家坡近,由于在何家坡犯过事,使他怕于见到那里的任何人。他躲在一个拉着四五只羊正跟买主讨价还价的中年男人背后,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在他的印象中,何家坡人一般不赶清溪场,论物品,清溪场有的东巴场都有,只是清溪场的双月猪比东巴场便宜,尽管赶清溪比赶东巴多出一大半的路程,何家坡人买猪,还是要到清溪场来的。
羊的主人跟买主成交之后,兴致勃勃地抖着麻钱,向桥的北面走去。那是清溪集镇的中心,万家赌场就在那边。不仅有赌场,还有妓馆、相馆、茶坊。底层社会对生活的奢求,这里应有尽有。那人一走,何大再想找个遮挡之物就难了,卧着石狮的桥栏是遮不住的,桥上的人,不是匆匆过客,就是蹲在地上或放张小凳坐在地上抽签算命,无法挡住他。他垂了头,朝桥北走去。
正在这时,一个穿戴洋气的女人拿着一块馒头吃,馒头很干,许多粉屑就掉了下来,何大正要去捡,一个黑影突然蹿过来,捡起粉屑塞进了嘴里。
何大抬头一看,一脸漆黑的何建申正得意洋洋地望着他!
何大急忙向人丛中钻去。
何建申也认出了何大,紧随其后。
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何大转过身来,问道:“你跟哪个来的?”
“我一个人。我已经在清溪场过十几天了。”
“你来十多天了?”
“我爸爸死了。”
原来何建申也成了孤儿。
“如果我晓得是你去捡,”建申说,“我不会跑那么快。”
何大有些感动。
“何大,我们俩一起过好吗?讨来的东西,分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