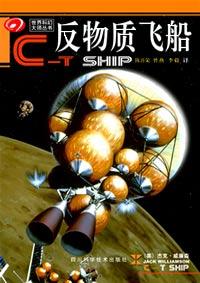破冰船-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牢牢的。一顶保温风帽、一条围巾、一顶羊毛便帽,以及一副护目镜,保护着他的面部;一副达玛树脂手套,外加一副皮革防护手套,同样地保护着他的双手。一只小背囊,装着日用必需品,包括他自己的仿制“斯阿斯”/“斯巴斯”式的厚腰带。
邦德在积雪中徒步跋涉前进。这儿的积雪最浅处也埋到了他的膝盖。他小心翼翼地走着,唯恐偏离了他白天已经侦察好的那条窄窄的小路。只要向左或者向右迈错一步,他就会陷进足以埋下一辆小型汽车的大雪堆。
那辆摩托雪橇正好放在下达命令的军官所说的地方。没有人会追问它是怎么跑到那儿的。摩托雪橇的机器如果不发动起来,搬起来就死沉死沉。邦德足足花了十分钟,才好不容易把它从一堆隐藏它的又坚硬又结实的枞树枝条中间生拉硬拽地搬了出来。然后,他把摩托雪橇推到一条向下延伸了几乎一公里长的斜坡顶上。他用手一推,雪橇便向下滑去,邦德只来得及跳上鞍座,把双腿套进防护档板里。
摩托雪橇无声无息地向斜坡下滑去,直到重量和冲力逐渐消失,最后才停了下来。虽说在冰雪之上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但是现在他已经离旅馆有足够远的距离,可以安全地开动机器了——不过先得用罗盘校正一下方向,打开遮光电筒检查一下他的地图。
小小的摩托苏醒了。邦德打开油门,开动机器,开始行进。他需要旅行二十四小时才能见到他的同事们。
罗瓦尼米是一个理想的地点。他们可以从城里迅速地向北转移到更加荒无人烟的地方。同时,只需驾驶摩托雪橇急行军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芬—俄边境上一些更容易进入的地点,比如像萨拉这样的地点,那是1930—1940年俄芬战争的一些大战役的战场。再往北去,那儿的边境地区就愈来愈荒凉了。
在夏季,北极圈的这个地方还不那么令人生畏,但是在冬季,雪暴、深冻和漫天大雪控制了一切,对于一个毫无戒心的人,这片地区就很可能十分凶险,遍地是陷阱了。
一切都结束了。和“斯阿斯”、“斯巴斯”人员进行的两种训练都完成以后,邦德原以为自己一定会精疲力竭,急需休息和睡眠,以及只有在伦敦才能得到的娱乐消遣。在这次考验的最艰难时刻,他的脑海中确实常常回忆起在他切尔西寓所里的舒适景象。
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两周以后,当他回到罗瓦尼米的时候,他的身体竟会充溢着很久以来没有体会过的旺盛活力和强壮舒畅的感觉。
他是在清晨到达的。他悄悄来到绅宝公司冬季驾驶训练总部安营扎寨的昂纳斯瓦拉北极饭店,给埃里克·卡尔森留了一封短信,说稍后会通知他把“银兽”运到何处。然后他搭了一辆到机场去的便车,登上了下一班去赫尔辛基的飞机。在那一刻,他的计划是从赫尔辛基直接转机飞到伦敦去。
但是当那架DC9 —50 型班机在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左右即将到达赫尔辛基的范塔机场时,詹姆斯·邦德想到了保拉·韦克。这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无疑是由于他新出现的心理上舒适畅快和生理上灵活敏锐的感觉。
到飞机着陆时,邦德的计划已经完全改变了。上级没有规定他回伦敦的时间,而且他还有权享受几天假期,虽说M 曾经指示他一离开芬兰就马上回来。反正在两天之内,没有任何人会需要他。
他从机场坐出租车直接来到洲际饭店,办理了住宿手续。
服务员刚刚把他的旅行箱提进房间,邦德就坐在床上给保拉打起电话来。六点三十分。他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邦德怎么也没有料到,给一个多年的女朋友打个电话请她出去吃晚饭,竟会使他今后几个星期的生活道路,发生如此激烈的变化。
3刀光剑影的晚餐
邦德用温水洗了淋浴,刮了胡子,仔细地穿好衣服。重新换上他的一套讲究的灰色华达呢套服,素净的蓝色科尔斯衬衫,再打上一条他心爱的雅克·法思针织领带,使他心情十分愉快。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季,赫尔辛基的饭店和著名的饭馆还都希望他们的顾客打好领带。
他的那支赫克勒科克P7 型手枪——它如今取代了那支更沉重的VP7O 型手枪——已经妥妥贴贴地放进了他左腋窝下的弹簧夹枪套。为了抵御刺骨的寒风,邦德来到旅馆大厅的时候穿的是他的那件克龙比式不列颠保温大衣。
这使他带上了几分军人风度——尤其是那顶毛皮帽子——不过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种风度一向对他是有利的。
出租车顺着曼纳海明蒂干线不停地朝南驶去。主要的人行道上的雪都整整齐齐地扫成一堆,雪压弯了树木,有些树的枝条,像圣诞节的装饰物一样,挂着长长的冰柱。国家博物馆的尖塔像一只指向天空的手指,在博物馆附近有一棵树长相很特别,就像是一个戴着白色僧帽的修士握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匕首蹲在那里。
透过清澈透明的霜花,邦德瞥见了乌斯彭斯基教堂——大教堂——在泛光灯照耀下的高耸圆形屋顶。它高高地凌驾于一切之上。他在一瞬间便懂得了为什么拍电影的人在需要莫斯科的外景时会选择赫尔辛基。
这两座城市其实就像沙漠和丛林一样毫不相像。和莫斯科那些一模一样的丑陋怪物比较起来,芬兰首都的现代建筑物,在设计和建造上都有其特有的鉴赏力和美感。只不过,在这两座城市的老城区里,那种镜中倒影似的相似之处,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在偏僻街道和狭小的广场旁,一幢幢房屋相互依靠着,建筑物华美的正面装饰使旁观者回忆起还是沙皇、亲王和不平等的时代,在那古老而美好的、古老而邪恶的时代,莫斯科曾经是什么样的。而现在,邦德想道,他们只有政治局、政委、克格勃了,还有……不平等。保拉住在曼纳海明蒂大道东南头,在一座俯视埃斯普拉纳达公园的公寓住宅楼里。邦德以前没有到过城里的这个地区,所以初次来访就使他感到又惊又喜。
公园本身是夹在两行建筑物中间的一长条风景地带。看来在夏天,这里一定是一片林木葱笼、假山庭园、曲径通幽的田园诗般的美景。现在在隆冬,埃斯普拉纳达花园又具有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新用途。年龄不同、才能各异的艺术家们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室外的冰雕陈列馆。
在初冬时节人们精心地制作出来的物体和人形,现在已蒙上了最近新降下的一场雪。那里有抽象的物体,还有细致的冰雕,它们制作得如此精巧,使你竟以为它们是木头雕像,或是千辛万苦铸成的金属雕像。挨在坑坑洼洼、直眉瞪眼的雕像旁边的,是心平气和、沉思冥想的雕像。还有那动物冰雕,有的用的是自然主义手法,有的则只是在有棱角的冰块上凿出个大概模样。
它们一个挨着一个,有的朝匆匆的路人张大了空空洞洞的冬天嘴巴,有的为了御寒,竖着皮毛挤在一起。
出租车停下来的地方,几乎正对着一件真人大小的冰雕。那是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一男一女,只有春天的温暖才能把他们分开。
公园旁边的建筑物大部分是古老的,偶尔夹杂着一两幢现代化的建筑物,看起来就像是在活的历史中填补空白的新的缓冲国家。
[ ·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邦德并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理由,就认为保拉一定住在一栋漂亮的新公寓住宅楼里。相反地,他发现她住的是一栋有百叶窗、刷了新鲜的绿色油漆的四层楼房,积雪像盛开的鲜花一般装饰着它那窗台上的花盆箱,还沿着涡形花饰和屋檐水槽冻成霜花垂了下来,仿佛十二月的汪达尔入侵者拿起喷水壶,洒遍了所有喷得着的地方。
这栋楼房被两个曲线形半砖半木结构的尖顶山墙一分为二。大门只有一个,门上镶着玻璃。大门没有锁上。大门里面有一排金属的邮件箱,标志着谁是住户。一张卡片插在小小的框子里,每一张卡片都讲述了一个关于住户的小故事。走廊和楼梯都没有铺地毯。发亮的地板散发出高级上光蜡的气味,此刻它们正和诱人的饭菜香味混合在一起。保拉住在三楼,3A 号房间。邦德解开不列颠保温大衣的衣扣,开始上楼。
他注意到,每一层楼梯口上有两扇门,一扇在左,一扇在右,门做得又结实又精致,有一只门铃,下面是跟邮件箱上一模一样的框子里的卡片。
在第三层楼梯口,在3A 的门铃下,有一张考究的名片,印着保拉·韦克的名字。出于好奇,邦德看了一下3B。它的住户是一位A ·纽布林少校。他想象出一位退伍的陆军军官,带着他的军事题材的绘画、论述战略的书籍和那些使得芬兰印刷出版界如此兴旺的战争小说,蛰居在这里。那些战争小说使人们牢牢记住了芬兰对俄国的三次“独立战争”:起初是为了反对革命;然后是为了反对入侵;最后则是跟纳粹德国的国防军打得火热,共同对付俄国。
邦德使劲摁着保拉的门铃,摁了很久,然后面对那扇门中心小小的窥视孔站好了。
门里传来了链条的响声,然后门开了。保拉出现了,她穿着长长绸衫,腰间松松地系了一条带子。还是原来的保拉:像过去一样美丽动人。
邦德瞧见她的嘴唇动了动。仿佛要努力说出欢迎的话来。在那个瞬间,邦德认识到,这不是原来的保拉,她的面颊变得芬白,扶在门上的手在微微颤抖着。在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深处,毫无疑问地闪着一丝畏惧。
在情报局的训练中,教师告诉他们,直觉,是某种你通过经验所学到的东西:你决不会生来就具有直觉,像某种第六感那样。
邦德放大嗓门说道:“是我,从海外来的,”同时伸出一只脚,让鞋的一侧抵住门。“你高兴我来吗?”
一面说,邦德一面用左手抓住保拉的肩头,把她转过身来,拉到楼梯口上。同时他的右手已经伸出去掏枪了。不到三秒钟,保拉已经紧贴在纽布林少校门外的墙上,而邦德则已经握住准备好的赫克勒科克手枪,侧着身子闪进了门里。
屋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个子,干瘦的脸上布满麻点,他站在邦德左边,紧紧贴着内墙,刚才就是他站在那里,用一支小手枪对准了保拉。那支枪看上去像是一支38 口径的特许专用特工手枪。在屋子的另一头——这间屋子没有过道——有个大个子男人,一双手又粗又大,脸孔像个不够格的拳击手,正站在一套漂亮的两用镀铬皮沙发旁边。他最引人注意的特点之一,是他的鼻子长得像一个通红透亮快要溃破的脓疱疮。他手里没有拿什么明显的武器。
小矮个的枪指向邦德左边,那个拳击手开始移动。
邦德冲着那支枪去了。大号赫克勒科克手枪在邦德手里仿佛只晃动了一下,就沉重地砸在小个子的手腕上。
那支手枪飞了出去,一声疼痛的喊叫压倒了骨头折断的脆响。
邦德用赫克勒科克手枪指着那个个子大些的家伙,左胳臂把小个子转过来像盾牌一般挡住自己。与此同时,邦德狠狠地飞起了膝盖。
小个子枪手崩溃了,他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无力地拍打着,试图保护自己的小腹。他像一头猪那样嘶声尖叫着,匍匐在邦德脚下蠕动着。
那个大个头似乎没有把那支枪放在心上,这说明他如果不是非常勇敢,就是个低能儿。要知道在这样近的距离,赫克勒科克能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