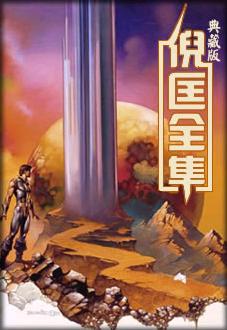头发-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王将“神当然是永生的”这句话,重覆了几遍。我已经看出了国王的心目之中,一定有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想和我讨论,但是看来他又不想将心中所想的突然讲出来。
我只好道:“有一个现象很奇怪,所有宗教,目的几乎全是一样。”
国王道:“是,目的全是离开了肉体之后,人的某一部分,可以到某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或称西方极乐世界,或称天堂。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信仰的人有神存在,而人生活的历程,身体并不要紧,精神或是灵魂,才是首要。”
我点头表示同意,国王忽然又问道:“为甚么呢?”
为甚么?我自然答不上来,国王笑著,那是一种无可奈何,又有点自嘲的笑容,道:“会不会那些宗教的始创人,本来全是由一个地方来的?”
我感到了震惊,一时之间,更不知说甚么才好,国王却继续道:“耶稣、穆罕默德、佛祖、老子,他们四个人本来是不是认识的?”
这是一个怪诞到不能再怪诞的问题。尽管我对一切怪诞的事,都抱著可以接受的态度,在听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也不由自主摇著头:“那不可能吧,这四个人生存的时间,相差很远,好几百年。”
国王却望向窗外,出了一会神:“好几百年,那只是我们的时间,在别的地方来说,可能只是前后几分钟、几小时的差别。”
我感到愈来愈离奇,国王在这方面的问题,有无穷无尽的想像力。将耶稣、穆罕默德、佛祖释迦牟尼和老子李耳联在一起的人,不是没有,但说他们四人根本是相识,这真有点匪夷所思。
我想国王的心中,或者有他自己一套想法,我倒很愿意听他进一步的说明,可是就在这时,御前大臣走了进来:“再过十分钟,飞机就可以降落!”
我连忙站了起来,国王很客气地送我到房门口,我可以感到他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也可以感到他心中有话,但是找不到倾诉的对像的那种寂寞感。
可是我急于赶路,而且,由于“不得已的苦衷”,我甚至不能在尼泊尔的境内停留,所以看来我这个讲话的对像,以后也很难和他相见了!
御前大臣派车子送我到机场,飞机已经来了。驾驶飞机的是一个中校,他不知道我是甚么来历,只当我是王室的贵宾,对我十分尊重。我请他在安全范围的边缘,尽可能用高速飞行,他答应了。
尽管喷射机已是地球上最快的交通工具,等我驾著车,在巴西北部的丛林中向前疾驶之际,也已是三十多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利达教授的实验室我曾经到过一次,路途我是熟悉的,尽管是在晚上,也不至于迷路。
虽然夜晚在丛林中硬闯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我也顾不了许多,吉普车的车头灯,时时射到野兽的眼睛。那些眼睛在强光的照射之下,发出亮晶晶、绿黝黝的光芒,看来怪异和骇人。
愈是快接近目的地,我愈是心急,等到朝阳升起,我已经驶到了河边,那是一条不很宽的小河,但是河水很湍急。
利达教授的实验室,就在前面的一个河湾,大约只有十分钟的行程了,我的心中更是紧张,将车子驶得飞快。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车子有时可以跳到三四呎高,再跌下来,十分钟后,我已经驶进了那个河湾,而突然之间,我用力踏下了刹车掣。
我看到的情形,令我产生了如此巨大的震动,以致我踏下刹车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车子在高速行驶中,突然停下,车子打著转,陡地翻了过来。我也不理会自己有没有受伤,一面发出呼叫声,一面挣扎著自车子下爬了出来,站直身子。
虽然我的身子摇摇晃晃,不是很站得稳,但是眼前的情形,我还是看得十分清楚。
利达教授的实验室本来是六列十分整齐的茅屋,其中四列,是他千辛万苦运来的玻璃搭成的温室。里面种著上千种他所珍逾性命,费了近二十年功夫采集而来的植物。但是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六列茅屋全都成了灰烬,一点也没有剩下。在朝阳的光瓦之下,我看到焦黑的屋基下,有许多闪耀发光的物体,等我踉跄地走向前之际,才看出那些发光物体,是碎裂成千上万碎片的碎玻璃。
根本没有人,如果有人的话,一眼就可以望到,利达教授那里去了?他的助手哪里去了?他雇用的土人哪里去了?更重要的是,白素哪里去了?
我早已知道,就算我用最快的方法赶来,也一定迟了,可是我料不到事情会糟到这样地步!这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我一面发出毫无意义的呼叫声,一面在六列茅屋的屋基上,来回奔跑著。
白素曾说过处境不妙,但是她已曾说过可以应付,除非是情况极端恶劣,不然她至少该留下一点甚么来,好让我推测这里究竟发生过甚么事。
可是我找了又找,却甚么也没有发现,眼前只是一片荒凉已极的废墟!
到了我坐下来的时候,才发现日头早已正中!我完全不知该如何才好,从来也没有这样彷徨失措过,简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我突然又听到了有车声传来之际,我像是遇到了一个大救星一样,陡地跳了起来,迎了上去。
我只不过奔出了一百多公尺,就看到一辆军用吉普车驶了过来。车上有三个士兵,一个军官。车子在我身边停下,那军官道:“卫斯理先生?”
我也不去问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只是点著头。那军官道:“我接到报告,有人在晚间驾车通过森林,向这地方驶来,知道一定是你。”
我想起了老蔡的话,忙道:“阁下是祁高中尉?”
军官点头答应,我叫了起来:“这里究竟发生了甚么事?”
祁高中尉叹了一口气,下了车,向前走去,我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了废墟附近,他才道:“事情很不寻常,你看那边 ”
他一面说,一面指向东边。他手指处,是密密层层的崇山峻岭。他道:“在那里,住著黑军族 ”
我一听到“黑军族”三字,就倒抽了一口凉气,失声道:“黑军族!黑军族和外界不相往来,只要没有人会侵犯他们,他们尽管凶悍,却不会主动去侵犯他人!”
祁高的神情有点讶异,像是惊疑于我对巴西北部深山中的一个人数不过千的印地安部落,居然也有认识,他点头道:“本来是如此,但是 ”
我吞了一口口水,指著废墟,问道:“这……是黑军族的杰作?”
祁高苦笑了一下:“我来迟了!你……也来得太迟了!”
我只觉得头皮发麻:“黑军族……他们……教授和我太大,他们 ”
祁高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我定期巡视,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多月之前,当时的情形,已经很不寻常。从来和外界不通音讯的黑军族,竟然派了一个巫师下山,来找利达教授,要教授进山去。”
我道:“是不是教授在采集标本的时候,侵犯了黑军族的禁地?”
祁高道:“绝不是,教授在这里多年,对黑军族有很深刻的了解,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我到的那天,是那巫师来过的第二天,利达教授对我说起这件事,他还开玩笑似地对我说:‘真是奇怪,黑军族的巫师居然对我说我的儿子在他们那里,叫我去!’”
祁高向我望来:“这不是太无稽了么?”
这当然太无稽了,但是我却感到了一股凉意:“柏莱回来了。”这是白素说的;“我相信柏莱在尼泊尔死了。”这也是白素说的。这其中究竟还有甚么怪异的联系呢?
祁高继续道:“巫师在族中的地位十分高,亲自出山,事不寻常,我还问他那土人是不是真的祭师。利达教授还回答我:‘他的帽子上的羽毛,只有黑、白二色,你说他不是巫师,又是甚么身份?’只有黑白二色,不但是巫师,而且是重大仪式中的主要祭师,事情可真不简单了。当日,当我离开的时候,教授就坐我的车子离去,说是要和亚洲的一个朋友通电话。”
我道:“那就是我,可是我在尼泊尔,正在找他的儿子!我妻子接到了他的电话。”
祁高的神情十分疑惑,我也没有和他作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我一听祁高的叙述,就可以肯定,利达教授对祁高只不过说了一点点事实,而隐瞒了许多。因为单凭一个巫师来找他,说他的儿子在山里 黑军族的聚居地,绝不足以使教授打电话来找我,而更不足以使白素一听到他的电话,就万里迢迢前来。
祁高继续道:“后来,好像又没有甚么事,你太太是我派人送到这里来的,我驾车,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以听到黑军族召集全族人的鼓声,表示他们的族中,有重大的事发生,鼓声持续了好几天,我每隔一天来一次,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你太太要我带一卷录音带去打电话给你,你仍然不在。”
我道:“是的,我听到了那卷录音带。当时,她处境十分不妙,你难道没有觉察到么?”
祁高听出了我的话中有责备他的意思,忙道:“谁说我没有觉察到!我看出她和教授,都十分惊惶,好像有甚么绝不可解释的事降临在他们身上,但是我问了,他们却全说没有甚么。我问不出所以然来,当然只好离去,又隔了一天,再到这里时,已经这样子了!”
我道:“你推测发生了甚么事?”
祁高道:“当然是黑军族的进攻。”
我又道:“人呢?所有的人呢?”
祁高摇头,表示答不上来,我想了一想:“将你车上的汽油尽量给我!”
祁高像立即想到了我想干甚么,他大叫了起来:“不能!”
我道:“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我一定要去!”
祁高极其惊骇,甚至在不由自主地喘著气:“你想去闯黑军族的禁区!你对黑军族既然有认识,难道就不知道亨爵士探险团的事?”
我当然知道亨爵士探险团的事。亨爵士是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他想突破黑军族与世隔绝的现像,招募了七个志愿队员,不管巴西政府的反对,甚至击退了巴西政府派来阻截他们的一队军队,进入黑军族的禁区。当时,英国的赌博公司对他们能生还的机会的盘口是五百对一。结果,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并没有出现。八个人,连亨爵士的尸体在内,被人在亚巴逊河的一条交流上发现、扎在一个木排之上。
八个人全死了,在木排上,有黑军族的标志。自此之后,巴西政府就画出了禁地,不准任何人走近离这个印地安部落三里的范围之内。
我并没有向祁高再说甚么,只是重覆著我的要求。祁高的面色灰白,喃喃地道:“这简直是自杀,我不能供给你汽油。”
我简捷地道:“结果是一样的,即使是步行,我也一样要去。中尉,这里并没有发现尸体,我们不能绝望,这里的人,可能还生存在黑军族中!”
祁高眨著眼,外人能在黑军族部落中生活,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在我而言,不能不如此希望。
祁高道:“那么,至少等一等,等我和长官商量一下!”
我斩钉截铁道:“不行,我一分钟也不愿耽搁!”
祁高叹了一声,指挥著他手下的三个士兵,将六罐汽油,搬到了我的车上,将倾覆了的车子推起来,我立即上车,向祁高扬了扬手,疾驶向前,在我经过了祁高身边的时候,祁高解下了他的佩枪,向我抛来。
我接住了佩枪,一停不停地继续驶向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