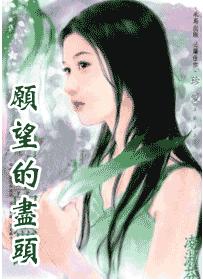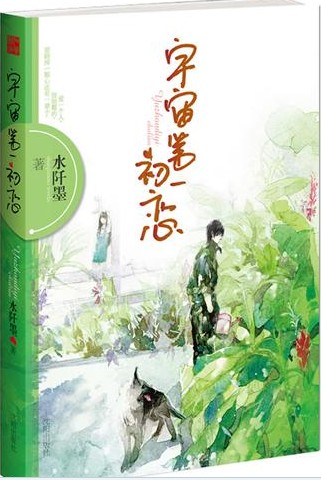宇宙尽头的餐馆-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过一会儿他们就能应付了。”他说。
阿瑟猛地抬起头。
“为什么这么说,”他问。
福特又耸了耸肩。
“只不过是种预感。”他说,然后不再回答阿瑟的任何问题。
“看,”他突然说。
阿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下面散漫的人群中,有一个身影正在移动——更准确地说,正在徘徊。他的肩上似乎扛着什么东西:他从一具疲惫的身躯徘徊到另一具疲惫的身躯,似乎在用肩上的那个什么东西对着他们挥舞,样子像喝酢了。过了一阵子,他放弃了努力,瘫倒仵地。
阿瑟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电影摄像机,”福特说,“记录这历史性的一刻,”
“哦,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过了片刻,福特再次开口道,“不过,我完蛋丁”
他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又过了一会儿阿瑟觉得幅特的这句话需要一点儿注释。
“嗯,你说你完蛋了,究竟是什么意思?”阿瑟问,
“问得好!”搞特说,“我这儿完全没信号,”
从幅特的肩膀看过去,阿瑟看见他正征摆弄一个黑色小盒子上的旋钮。福特已经向阿瑟介绍过这个盒子了,它叫以太感应器。
阿瑟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在他的头脑里,宇宙仍然划分为两个部分一地球,和其他所有东西。地球为了给一条超空间通道让路而被毁灭了,这意味着这个划分观点有点儿不平衡,但是阿瑟坚持这种不平衡,以维系最后剩下的一点儿他和自己家同的联系。毫无疑问,以太感应器属于“其他所有东西”这一目录。
“连根香肠都没有。”福特说,一边摇晃着手里的玩意儿
香肠,阿瑟无精打采地望着眼前这个原始的世界,心想,如果现在能弄到一根上好的地球香肠,让我干什么都成。
“你相信吗,”福特恼怒地说,“在这个愚昧的角落,好几光年范嗣之内措然没有任何传送信号,体在听我说话吗?”
“什么?”阿瑟问。
“我们碰上麻烦了。”幅特说。
“峨,”阿瑟说。对他米说,这听起来像一个月以前的1日闻:
“在我们从这台机器里获得任何信号之前,”福特说,”我们离开这颗行星的儿牢是零。有可能是这颗行星的磁场出现了一些异常波动——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不断移动,找一个清晰的接收隧。你来吗?”
他操起他的家伙,大步走开了。
阿瑟朝下望去。那个带着电影摄像机的人已经再一次挣扎着站了起束。
阿瑟捡起一块玻璃片当成防身武器,大步跟上福特。
第二十七章
“这顿饭一定吃得不错吧,”扎尼乌普对赞福德和崔莉恩说,他们刚刚在“黄金之心号”星际飞船的舰桥上还原,躺在地板上直喘粗气。
赞福德睁开一些眼腈,对他怒目而视。
“你!”赞福德吐了口唾诛。他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想找到一把椅子好倒在上面。他找到一把,倒了进去,
“我已经在电脑里编好了和我们这趟旅程相关的非概率坐标,”扎尼乌普说,“我们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现在,你为什么不放松放松,为这次会面作点准备什么的,”
赞福德什么也没说,他站起身来,走到一个小柜子前,取出一瓶杰克斯老酒,狠狠地灌了一大口。
“等这一切结束,”赞福德粗鲁地说,“结束,对吗?我就能自由地离开,去干他妈的我喜欢干的事,躺在海滩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对吗?”
“这得看会面的情况了。”扎尼乌普说。
“赞福德,这人是淮?”摧莉恩用颤抖的声音问,一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在这儿干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我们的飞船上?”
“他是一个大傻瓜。”赞福德说,“他想和统治整个宇宙的那个人会面”
“哦,”崔莉恩说,她从赞福德手里章过酒瓶,自己喝了起来,“一个一心向上爬的野心家、”
第二十八章
你想统治人,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之一,因为有好几个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想统治的是什么人。换句话说就是,你能找到什么样的愿意受你统治的人。
总结: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最想统治别人的人正是最不适合统治别人的人,原因就是他想统治别人。总结的总结:如果有准非常希望担任总统,那么,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份工作交给他。总结的总结的总结:人真麻烦。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连续多年,银河系总统都把注意力过多放在享受大权在握的乐趣和别人的奉承啦,以至于他们极少注意到自己手中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
权力隐蔽:总统们身后的阴影中的某个地方。
如果任何希望统治别人的人都无能,那么,他们怎能肩负起统治别人的重任呢?
第二十九章
一个狭小而幽暗的世界,位于银河的极偏僻处——也就是说,那里几乎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崮为它被一个阿大的无概率场所保护若,整个银河系内只有六个人有那里的钥匙。那里正下着大雨。
大雨倾盆,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它落在海面上,激起了层薄雾;它击打着树木;它把海边的一片覆盖着灌木的土地搅拌成了泥浆。
雨点打在起皱的铁皮屋顶上,在上面狂舞。这是这片覆盖着灌木的十地巾央的一问小履。雨水淹没了从小屋通向海岸的崎岖小径,把放在那里的一堆整齐美丽的贝壳冲了个七零八落,
雨点打在小屋顶,从屋里听,耶种声音简直震耳欲聋,但屋里的人却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别的地方。
这是一个举止晃晃悠悠的高个子男人,凌乱的淡黄色头发已始被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打湿了。他身上的衣服很破,他的背是驼的,他的眼睛虽然睁着,看上去却跟闭若没有什么区别。
他的屋里,一把弄坏了的……扶手椅、一张被刮花的……桌子、一张旧床警、几块坐垫,还有一个很小却很暖和的炉子。
这只猫象饱经风霜的老狮,它正是这个人面前注意力集中的焦点,他朝着它弯下晃晃悠悠的身子。
“猫咪,猫咪,猫咪,”他喊道,“咕唧咕唧咕唧咕猫咪想要他的包吗?好好吃的鱼。猫咪想要吗,”
这只猫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它犹豫地用爪子拨着这人递过来的鱼,但很快就被地板上的一团灰尘吸引了过去
“猫咪不吃他的鱼,猫眯变瘦了,一天比天瘦。”这人说声音巾带着一丝怀疑。
“我觉得这是以后会发生的事,”他说,“但我怎么能说出来呢?”
他又把鱼递过去。
“猫咪想想吧,”他说,”吃鱼还是不吃鱼。如果我不在这儿搀和的话,情况也许会好点儿。”他叹了口气。
“我认为鱼很好吃,又认为雨太多了。唉,我说什么,凭什么乱下判断?”
他把鱼放在地板上,留给那只猫,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嗅,我好像看见你在吃它丁。”他最厉说:那只猫终于玩腻了那团灰尘所能提供的所有的娱乐性,然后扑向了那条鱼。
“我喜欢看见你吃鱼。”这人说,“在我的想像中,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就会一天天衰弱下去。”
他从桌面上拿起一张纸和一截用秃了的铅笔头,他一只手拿着这样,另一只于章着另样,试验着把它们凑到一起的各种不同的办法。他试着把铅笔放在纸的下面,然后是纸的上面,然后又是纸的旁边:他试着用纸把铅笔卷起来,他试着把铅笔钝的一头和纸压在一起,然后叉试着把铅笔尖的一头和纸压在一起,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丁一个印}己,他对于这个发现很高兴,他每天都会为这个发现而高兴:他又从桌面上拿起另一张纸。这张纸上面有一个纵横字谜他研究了片刻,填了几条,然后就失去了兴趣。
他试同坐在自己的一只手上,臀部的感觉激起了他的兴趣。
“鱼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说,“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或者我想像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些人来的时候…或者在我的想像中那些人来的时候,他们乘坐着六艘闪耀着黑色光泽的飞船‘在你的想像中他们也来了吗,你怎么看,猫眯?”
他看着那只猫。比起思考这些问题来,它更热衷于尽可能快地把鱼吃下去。
“当我听到他们的问题时,你听到问题了吗?他们的声音州尔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体只是认为他们在对你唱歌吧,”他仔细地想了想这个问题,然后发现唯一推测中的漏洞。
“也许他们确实是在对你唱歌,”他说,“只不过我想像成了他们在问我问题。”
他顿了顿。有时候他甚至会一顿好几天,只不过为了瞧瞧一顿好几天是什么样子。
“你想他们今天会来吗,”他说,“我想是的:地板上有泥巴,香烟和威士忌在桌子上,盘子里的鱼——那是给你的·还有就是我的脑海里关于他们的记忆了。我知道,这些算不上什么确切证据,但话又说回来,一切证据都算不上确切证据。咱们来瞧瞧·看他们还给我留下了些什么。”
他走到桌子旁边,从上面拿起一些东西。
“纵横字谜、字典,还有一个计算器。”
他玩了一个小时的计算器。那只猫睡了,外面的瓢泼大雨继续下着。最后,他终于把计算器放到一边。
“我想,我认为他们是来问我问题的想法一定是对的。”他说。“跑这么远来到这里,又留下这么多东西,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你唱歌,这种举动未免太奇怪了,至少我觉得是这样。谁知道呢?谁知道呢?”
他从桌上拿起一枝香炳,在火炉冒出的火苗上点燃。他深吸了一口,然后重新坐下来。
“我想今天我在天空中看见了另一艘飞船,”他最后说,“一艘巨大的白色飞船。我从来投有见过巨大的白色飞船,只见过那六艘黑色的,还有六艘绿色的,另外还有一些,声称他们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从来没有过白色的。也许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六艘黑色的小飞船看上去会像一艘白色的大飞船吧。也许我应该倒上一杯威士忌。是的,威士忌似乎比较可靠一点儿。”
他站起身,从床垫旁边的地板上找了一个玻璃杯,然后从威士忌洒瓶里倒了一小格。他又坐下来。
“也许义有别的什么人要来见我。”他说。
一百码以外,在倾盆大雨冲刷下,停着”黄金之心号”。
舱门打开了,从里面钻出来一个人,他们缩成一团,免得雨淋到他们的脸上。
”在那儿吗?”崔莉恩大叫着说,这样才能盖过雨声。
“是的。”扎尼乌普说。
“那间小屋?”
“是的。”
“太奇怪了。”赞幅德说。
“但这儿这么荒凉,”崔莉恩说,“我们一定是来错地方了,你不可能在这样一问小屋子里统治宇宙。”
他们快步穿过大雨,浑身湿透地来到小尾门前。他们一边敲门,一边颤抖着。
门开了。
“有什么事吗,”那个人说。
“噢,对不起,打扰了,”扎尼乌普说,“我有理由相信…·”
“是你在统治整个宇宙吗’”赞幅德问。
那人冲他笑笑。
“我尽量不这么馓,”他说,“你们淋湿了吗?”
赞福德惊讶地看着他。
“淋湿?”他叫道,“难道你觉得我们还不够湿吗?”
“在我看来是这样,”这人说,“不过你们的感觉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们认为温暖可以给你们烘干衣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