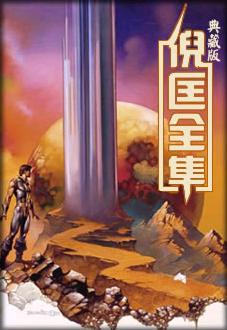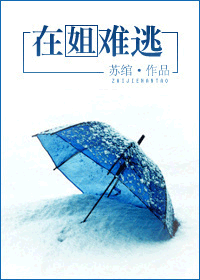在数难逃-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记起来了,那次身在风光如画的小岛上,穆秀珍看来无忧无虑,快活如神仙。但陶启泉曾经叹:“像她那样的性格真好,要是换了别人,处在她的环境,早就烦也烦死了!”
当时,我就曾追问穆秀珍有甚么烦心事,但陶启泉支支吾吾,所以我也没有再问下去。
由此可知,穆秀珍已有烦心事,只不过她处理的方式,与众不同而已。
我不由自主,叹了一声:“真难想像,连她也会有普通人的烦恼。”
我和白素忽然说起穆秀珍的事来,七叔一面喝酒,一面用心听著,等我们的话,告一段落,他才道:“若她就是当年那女婴 ”
他话说了一半,顿了一顿,就没有再说下去。
白素道:“要知道是不是她,下次见面,问一问她原籍何处,就可以知道了。”
我答道:“何必等‘下次见面’,我立刻和她联络,问她。”
七叔一听得我这样说,神情颇是紧张,他举起手来:“等一等,让我想一想!”
他真的眉心打结,好半晌不语,我和白素互望,都不知道七叔在想甚么,也不明白他何以要在联络穆秀珍之前“想一想”。
等了好一会,七叔才道:“好,你联络她,问她。可是千万别说当年我抱女婴入穆家庄的事,且随便捏造一个问她的理由。”
我心想,这倒是个难题 要造一个理由容易,但是要瞒过冰雪聪明,玲珑剔透的穆秀珍,只怕不是易事!
但七叔既然这样说了,自然也只得答应。
于是,我就用电话,与应该在法国的穆秀珍联络。
电话接通,留了口讯 一般“要人”,都有二十四小时的联络电话。然后,等候回覆。
大约十来分钟,在这段时间内,七叔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和白素,也不去打扰他。
等到电话铃响起,按下掣钮,听到的都是云四风的声音,白素问:“秀珍呢?”
云四风的回答是:“老婆不知何处去,老公独自笑春风。”
我笑道:“问你也一样,秀珍原籍何处,请告诉我们。”
这将是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但是也不免有些突兀,所以云四风并没有立即回答。
云四风是科学家,又是工业家,行事作风,必然有条有理,和我那种天马行空的作风,大不相同,所以我也不怪他不能立刻有答案。
约莫二、三分钟之后,他才道:“真是,我完全不知道她原籍何处 兰花姐是哪里人?她们必然是同一籍贯。”
我笑道:“那还用你说,就是不知道,这才问你!”
云四风强调:“我真的不知道,从来也没有问过 从来也没有注意过这个……你为甚么要问?”
我顺口道:“没有甚么,只不过闲谈之中,忽然谈及而已,她有了音讯之后 ”
我话还没有说完,云四风已经紧张起来:“喂!别告诉我她……是外星人!”
我大是啼笑皆非,忙道:“不!不!我说……不是这个意思……”
本来,我想说“秀珍她绝不是外星人”的 但是心念电转间,我想到,我对穆秀珍不能说是太了解,也难以肯定她一定是地球人,所以这才改了口。
云四风心思缜密,一下子就听出了语意之中的含意,便追问道:“那是甚么意思?你要告诉我!”
我有点生气,提高了声音:“稍安!你别神经过敏好不好?”
云四风道:“那能怪我吗?和你这个怪人,沾上一点关系,都会变外星人!”
我又好气又好笑:“混蛋!”
云四风还不放心:“真的没有甚么重要事?”
我向七叔望去,想看看他的意思,谁知他宛若老僧入定,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就应道:“当然没有 你能联络到她,就请她打电话给我们。”
云四风道:“能找到兰花姐也一样?”
我道:“当然,不过小事情,就不必惊动她了!”
云四风竟然相信了真是“小事”,因为若事关重要,我一定会要他去找木兰花的。
云四风没有再说甚么,我放下电话,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七叔在这时,忽然说了一句无头无脑的话,他用大是感慨的语调道:“我一生经历过的时代,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了!”
我和白素,面面相觑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搭腔才好。
七叔又补充道:“或许,这是亲身经历的缘故,感受特别深,所以感觉也强烈。其实,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期又黑暗,又是亲历,只是读史,自然不知痛痒!”
我和白素仍然不知他究竟想说甚么,所以仍然只是唯唯以应。
他又叹了几声,再发议论:“其实,我和你们,也都未曾亲自经历,只不过身处这个时代之中,可以在黑暗的边缘,窥视一下,那已足以令人遍体生寒,感叹人间何世了,真难想像身在其中的人,所感受到的,不知是何等的苦痛!”
我被七叔的喟叹所感染:“是啊,这一个世纪来,人类的苦难,真是说不尽。”
七叔笑得惨然:“最冤枉的是,究竟为了甚么,才形成了这样的大苦难,不但当事人说不明白,就是后世人,冷静下来分析,只怕也弄不明白。”
白素也喝了一口酒,她发表意见:“也不是太不明白,为来为去,只是为了三个字。”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才把那“三个字”说了出来:“争天下!”
我和七叔一起吸了一口气。
是的,争天下!
为了争天下,小焉者,兄弟可以互相残杀,母可以杀子,子可以弑父,甚么伦理关系,全都可以抛诸脑后。大焉者,结党斗争,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意见,不论文争武斗,都必置对方死地而后已,而处死的方法,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与五千年文化相辉映,成为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的,都是争天下,以万民为刍狗,就是为了争天下!
七叔越说越激动,可是忽然之间,情绪一变,又哈哈大笑起来,大声道:“争到了又怎么样?”
白素道:“自然希望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传下去。”wωw奇Qìsuu書còm网
我耸了耸肩:“别以为只有小人物好做春秋大梦,大人物也一样!”
七叔长叹一声:“甚么时候,这种梦不再有人做了,这才真正天下太平了!”
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我们都知道,七叔这一代人,胸怀和我们,有些不同(一代有一代的胸怀感情,再下一代自然又大不相同)。他那一代,饱历忧患,对世上的一切事,长嗟短叹,狂歌当哭,借杯中酒,浇胸中块垒,也还不够。
所以,我们都不再搭腔,七叔也喝了一回闷酒,情绪渐渐平复,忽然,他用很是平常的声音道:“那天,我上了船之后,一直在盘算如何处置那三件喇嘛教的法物 那三件东西,关系到二活佛的真伪,非同小可,我不能老带在身边。”
我和白素都知道,他是把三件法物,沉到了河底,但都没有阻拦他说下去。
他又道:“恰好,我在船尾,见到船家正在用铜油补木缝,我灵机一动 你们都已知道以后的事了。”
我道:“只知道你把盒子沉到了河底,千古不废江河流,那确然是最好的方法。”
二、一堆数字
七叔道:“我在午夜行事,认得了地点,把三件法物沉了下去,船上人虽多,但其时,寂静无比,只有河水汩汩的流动声,我才完了事,转过身,忽然看到,在船桅上那盏灯的昏黄光芒下,有一个人站在我的面前。”
七叔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大口酒,这才继续:“这人一望便知是女子,披著一件大氅,背著光,等我定过神来,才发现她面色苍白,但是清丽绝伦,绝对是水中仙子的化身!”
七叔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显然当时的情形,给他的印象极深,他要一点一滴,把所有的细节,全部从记忆之中挤出来。
我和白素也不去打扰他,各自尽量设想著当时的情景。
其时,正是过年后不久,上弦月在午夜时分,应该十分凄清,河水粼粼,幽光闪闪,船上的人虽多,但其时在甲板上的,却只有他们两人,一个是才把有关一教兴亡的三件神秘法物沉入了河底的江湖豪客,一个是突然出现的身分不明女子,这种组合,已经使场面够奇特,也够诡异的了。
七叔人在江湖,警觉性很高。他一看对方是一个年轻女子,看来虽然纤弱,但是眉宇之间,大有英气。虽然神情有些凄苦,但是眼神坚定,一望而知,是个巾帼须眉,不是等闲堂客。
七叔也不敢怠慢,在两人目光交会时,他向对方礼貌性地略一点头,心中在想:“刚才自己的心动,不知有无落在这女子的眼中?这女子又不知是甚么路数,是要出言试探她一下,还是就此别过?”
他正在盘算著,却见那女子已盈盈向他走近了几步。其时滴水成冰,天气极冷,来得近了,看到那女子的双颊之上,不知是由于寒冻,还是由于心情激动,竟然泛起了两目红晕,看来在清丽之中,增添了几分妖艳。
七叔吸了一口气,直视著对方,等对方先开口。
那女子果然先开口了,她来到了离七叔只有三两步处,才低声叫了一声:“大哥!”
在中国北方,女子称男子为“大哥”,可以是极普通的尊称,也可算是极亲近的称呼。而但凡有血性的男子,一听得女子称自己为“大哥”,总会油然而起护花之心,尤其对方是一个美女。
七叔自不例外,所以他并不逃避这个称呼,而是结结实实,应了一声。
这一下答应,令那女子有了一些喜色,她又靠近了一步,气息变得急促,神情也很是紧张。七叔低声道:“有事慢慢说。”
那女子答应了一声,又吸了一口气,胸脯起伏,七叔这才发现,她双手一直在大氅之中,大氅内鼓鼓的,像是有甚么东西在。
那女子接著说了一句话,却叫七叔这个老江湖,正吓了一跳,感到意外之至。
那女子的声音低沉之至:“大哥,小女子我,已到了绝路,再也活不下去哩!”
七叔在一惊之后,疾声道:“天无绝人之路,大妹子何出此言?”
那女子惨然一笑:“不真正到绝路,我不会这样说 生路也不是没有,大哥看我,若是现在,趁人静跳河,这逃生的成数有多少?”
七叔向黝黑的河水望了一眼,又略抬头,河面宽阔,那女子这样说,自然是要游过对河去,那有约莫三百公尺的距离。
河水表面平静,实则相当湍急,虽然未至冰封,但河水奇寒,也可想而知。
七叔再望向那女子,觉得她不像说笑,他沉声道:“那不知你水性如何?”
那女子道:“也曾在水涨时,泅过淮河。”
淮河在桃花汛水涨时,河面阔度,趋步两公里,能泅得过去,自然水性非凡了。
七叔点了点头:“淮河水涨时是夏日,此除是隆冬,我看,你能游到对岸,成数不足半成。”
那女子惨然:“是不?这说我死定了,也差不多 我死不要紧,但有一件心事放不下,与大哥虽是偶遇,却要斗胆相托。”
七叔一扬眉:“不一定要泅水,一定另有办法。”
那女子长叹一声:“一路上,为了跟我逃走,已经牺牲了不少弟兄,我不能再牵累人 全是些多么好的弟兄,有的则活埋了,有的则割了头示众,有的甚至被剥了皮,再这样下去,我活著也没意思。”
这几句话一出口,七叔登时有七八分猜到了那女子的特殊身分。
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