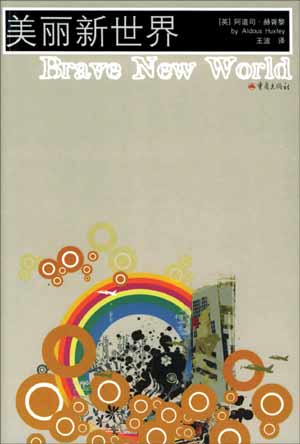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传-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回请她去拉古纳海滨游玩。格雷厄姆还开始参加巴菲特的本。格雷厄姆团体的会议。
他们俩人的性格都很幽默,一部分缘于两人不同的背景和素质。当巴菲特邀请格雷厄姆去奥马哈参观一趟时,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奥马哈在哪里,于是决定开开她的玩笑。登上飞机以后,他叫她画一张美国地图,标出奥马哈的位置。这张地图简直糟糕透顶,他想抢过来留下作个纪念,但格雷厄姆手脚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还有一次,他们到拉瓜迪亚之后,格雷厄姆急着要打电话,便问他有没有一毛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二毛五的硬币。和内布拉斯加其他的百万富翁一样,他舍不得浪费一毛五分钱,于是就跑出去想换成零钱。格雷厄姆大叫道:“沃伦,快把那二毛五给我!”
巴菲特去华盛顿时很少带上自己的妻子,而总是陪着格雷厄姆在城里四处逛逛。“凯的社交圈子扩大了很多。”作家杰弗里。考恩说。另一位朋友说,“《华盛顿邮报》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所面对的人。”突然之间,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类的人物打起了交道。利斯。史密斯,一位随笔专栏作者,报道说自从巴菲特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常客和顾问以后,他变得风靡一时。史密斯又说道:“整个华盛顿社交界都很兴奋,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穿得多么高雅庄重,巴菲特先生总是只喝百事可乐。”巴菲特不喜欢张扬,只喜欢在格雷厄姆家里这种易于控制的环境中和要人们相聚。
格雷厄姆生日聚会那天,当许多大人物们一起用餐时,出版商兼文学鉴赏家麦尔考姆带来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这瓶酒在格雷厄姆出世那年装瓶入窖,麦尔奇姆借此来暗示自己是花了血本买它的。当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时,这个百事可乐的忠实饮者阻止住他:“不用,谢谢。”他说着,一面用手盖住了杯子,“我看我还是节约点钱吧。”
当巴菲特在城里的时候,格雷厄姆总让厨师为他做汉堡包,还在曼哈顿的公寓内堆满了巴菲特最喜欢吃的东西——油花生和草莓冰淇淋。“当他来的时候,”她近乎奉承地回忆说,“这儿只有奶酪堡和炸——你管它叫什么来着?——法国炸薯条,整个儿都沾满了盐粒。”为了让他举止变得更优雅
一些,她带他去试穿皮革,还把他用漂亮的服装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反过来,巴菲特把格雷厄姆带到一些具有文化丰碑意义的地方去,比如位于新贝德福德的哈撒韦纺织厂等处地方。“他想让我去看看。”格雷厄姆说道。她把他当作自己“最贴心的朋友”,而且不论是个人建议还是商务咨询,她都很依赖他。巴菲特也在突然之间变成了格雷厄姆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个月去华盛顿一次,然后在格雷厄姆会客室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更换一遍,连巴菲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拿这些衣服怎么办才好。
在一次采访中,格雷厄姆说,“我还很年轻”——当巴菲特进入董事会时她正好57岁——“这确实让人吃惊”,但这句话并没有激起关于她私情的谣传。汤姆。默菲也曾拜访过巴菲特,她戒备地说:“如果我使用他,那是一种令人皱眉的事。”
巴菲特有一大堆女性朋友——《幸福》杂志的作家卡罗尔。卢米斯、鲁斯。米舍莫尔、芭芭拉。莫罗等等。莫罗认为他是位“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对妇女们都很和善。“他对女人有一种洞察力。”她说,巴菲特身上有一种现在已不太流行的侠骨文士的风范。他对粗俗和下流的玩笑非常痛恨,尽①管他确实也曾讲过一些幽默的关于床帏之间的笑话 。对于沃伦有这么多的女性朋友,苏茜丝毫不觉得紧张。有人提醒她,沃伦在华盛顿消磨了太多的时间,苏茜回答说她对事物的形式本身并不感兴趣,而只注重心灵的纯净——说这些话时,苏茜一点不觉得难堪和羞涩。(当巴菲特在华盛顿时,他们两个人都住在格雷厄姆家。)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巴菲特的生活失去了连贯性。苏茜曾经为他付出和放弃了那么多,如今,她对一个朋友说,她想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了。
她积极投身于一项挽救当地高中的运动之中,由于种族问题,这所学校学生流失十分严重;同时,她也开始独身外出旅行。很显然,她对沃伦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彼得是家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他发现家里越来越松散,爸爸常常呆在华盛顿,而妈妈似乎总是外出,彼得只好自己做饭吃。巴菲特意识到,像自己一样,妻子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家《华盛顿邮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们。他说道:“苏茜,你就像一个工作了23年后又失去工作的人。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苏茜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家里人都不觉得惊奇,因为沃伦工作时,她总是习惯于走来走去地唱着歌。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于是和当地的一个乐队鲍勃。埃德森。特里奥一起配合,在某些私人聚会露面。每当她想到公开演出时,她总是紧张不安,但沃伦很支持她,告诉她如果因为胆怯而退缩,她将来会为之后悔的。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内伯格的朋友的帮助下,苏茜克服了恐惧心理,出现在位于奥马哈郊区的一个名叫“精发泄”的夜总会的舞台上。
自那以后,在位于奥马哈铺满鹅卵石的集市街区的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开始了她的表演活动。这个咖啡店的主人是一对周游过许多地方的奥马哈人。他们是舞蹈演员迈克尔。哈里森和带有文化前卫气派的安东尼。亚勃特。
苏茜曾在这家餐馆主持过一场计划生育的义演。 (查尔顿。赫斯顿也光临了这里,除了175美元一磅的鱼子酱以外,他别的什么都没吃。)另一次,她
① 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巴菲特一家和罗伊、马萨。托丽丝散步,路过一家旅游品商店,看到橱窗里在一
些布料极其节省的比基尼边上有一块求救牌,巴菲特不禁诅咒道:“难道他们需要一个胖女人吗?”
为赈济非洲灾民登台演出了一场——和客人们一样,她穿着波浪形的印花棉布上装,系着鲜亮的丝巾,赤着双脚。在奥马哈,一个40多岁的家庭主妇在台上亮相是令人觉得古怪的一件事,但是城里的人早在此事传开之前就知道沃伦的妻子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人物。
在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在一个刷黑了的石窖中进行表演。她身材窈窕,显得十分性感,浑身缀满的金属片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比当初结婚时还显得美丽动人——高高的颧骨,一头棕色的短发,还有一双慑人魂魄的大眼睛。
她说话的声音略有一点单薄,但唱起歌来,它就带上了一种沙哑的特质,她表演极为风格化的爵士和流行曲调,比如忧郁的史蒂芬。桑德海姆《让小丑进来》。第一轮演出历时6个星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且反应相当良好。
奥马哈的一位艺术家肯特。贝洛斯说:“苏茜作为一位餐厅歌手——充满激情,风格独特。记得有天晚上,沃伦也在场,他脸上的表情显得那样如痴如醉。”
苏茜在台上表演时,巴菲特满脸欢乐地看着她,仿佛着了迷,他对一位朋友说:“苏茜唱歌的时候,声音是多么的甜美,几乎让我停止了呼吸。”
关于了他们的私生活,巴菲特说起时总显得十分甜蜜。他常常说,在见到苏茜之前,自己一直是郁郁寡欢的;如果没有苏茜,他是不会达到现在的成就。作为一对夫妻,他们抛开了一种传统的模式。尽管他们的兴趣,还有他们的安排都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巴菲特一直很依赖她,即使现在,她也会在公开场合依偎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仿佛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她明白自己就像他的缪斯神一样,永远不会对他说一个“不”字。
相比之下,巴菲特和凯。格雷厄姆在一起时就完全不同,她依靠着他,不仅因为她没有财务方面的经验,还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如果说得轻点,可以说巴菲特给予她的帮助和他对别的同事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也想从《邮报》公司里赚得一些利润,但这种意图并没有抹杀这个事实,他被格雷厄姆激发得生机勃勃,而他本人也对她非常宽容和大度。
出版商斯坦。利普西曾看到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同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利普西说,“但是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在一起睡过的人之间表现出的迹象,凯很有权威,同时也很羞涩。1000个人中有999个人都会把自己想对她说的话再三考虑一番,而沃伦则不会这样。他们俩成了知心朋友。”
不论任何“答案”,似乎都无法解释巴菲特为何能在这种关系中处理得十分妥当。也许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与此有关。巴菲特喜欢充当老师的角色,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格雷厄姆是一个非常迷人、接受能力很强的学生,《邮报》的一位董事说:“这想法实在太愚蠢了,她总在会前就餐,除了沃伦,我们都得离开。我从来不认为这件事和性有关。”
主管们看到,巴菲特—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最终对巴菲特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要想让格雷厄姆签发支票是不可能的。
为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被彻底开发为旅游省的麦加圣地之前,广告部的总管乔尔。查斯曼曾有个机会用2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一家电视台。“这真是一场痛苦的交易,”他说道,“现在就可以知道它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是公司上层部门有些人真是令人无法捉摸,它竟然被驳回了。”
“真是有人不可捉摸吗?”格雷厄姆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
它价格太高了。
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机会的事情,于是《邮报》的主管们都很沮丧。巴菲特对蜂窝式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本, (他当初投资《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与航空公司所不同——能产生直接的现金流,利润不必再投回到企业中去)。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太新了,就像把口味从汉堡包变成了外国食品一样。
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仅仅有专家保证的新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主管们所依赖的东西,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他没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会认为自己在投机。
而巴菲特是绝对不会投机的。
由于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性,《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自信的大都会公司执行总裁汤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议各类事情,但他总是有选择地采纳他的建议。但在总管房间的旋转门背后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连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态度逐渐渗透了整个董事会。
在加盟《邮报》之前,查斯曼曾在纽约的Wins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的版式。70年代后期,他曾提议《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特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主意。然而,在《邮报》的第一届董事会会议上它没有被通过。“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买什么,这与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