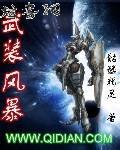明末风暴-第3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产生了怀疑。
俞国振对东林和复社的态度,万时华很清楚:与其中个人保持友谊,与其整体保持距离。初时万时华觉得这可能是不想卷入朝堂中的党争,但到后来,万时华发现,并非如此。
而是因为俞国振根本不屑东林、复社的这一套!
当俞国振的《从屁囘股到脑袋》一文出现之后,万时华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东林也好复社也好,始终没有超脱自己的阶层,他们拿豪伸的钱,或者本身就是豪伸,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为豪伸说话,而当豪伸的利益与大明的利益有了矛盾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豪伸这边,抛出与明争利等等大帽子。
这也是张缚引以为饮的苏州抗税五人墓碑的本质:一群豪伸,为了避免皇帝收税,指使可怜的工人打了锦衣卫,最后又推出五名一无所有的工人顶罪,然后假惺惺地在五人坟前立下了碑文。
他们苏的只是朝廷多征一些税,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却是仿织工。
万时华自己就曾极度贫困,甚至用新襄第一医院里的话说,是极度营养不良。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四处奔波,即使是这样,也不希望放弃读书人的体面。但无论他如何囘文名远扬,如何努力,连温饱都不能解决,更何况体面!
因此比起家境殷实的张缚,他更能理解俞国振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的态度。
他思想发生了转变,便从最初对俞国振这一套的不认可,发展到现在拼命引经据典,从儒家两千年的传承中为俞国振寻找理论依据一一如果单纯的孔孟之说里找不到,他甚至不惜去老庄墨韩等人的言论中去寻找。越是寻找,就越觉得俞国振才是得了上古圣贤一脉相传的道统,也越发地觉得,单纯靠着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伟业的。
故此,他全力邀请张缚来新襄,希望借助张缚的学问与影响力,完成这项伟业。他可以肯定,若是能完成此,自己等人比起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都要影响深远。
张涿前夜来时,他是极欢喜的,忍不住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张缚说了,结果却被张缚批评“离经叛道。”甚至说他是要“破孔门、废周礼、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万时华就想不明白,就连张缚自己也承认,俞国振治理下的新襄拥有整个大明甚至整个天下都没有的“大同。”为何他还坚定地认为俞国振乃是儒家的死敌。
终究是多年挚友,政论不同归政论不同,万时华并不想为此反目,当下哈哈一笑各自安歇。万时华次日专门请假,带着张缚四处转,一边转一边将自己的想法和俞国振的理念解说给张缚听。
他希望事实能说服张缚,结果又是一连串的争执。论写文章,万时华或许不在张缚之下,可是论起口才雄辩,他就差得远了,给张缚一番抢白,弄得他也渐生真火。
分明是他有道理的,可为何到了张天如那儿,白的也能变黑的,黑的能变白?
一天逛完小半个新襄,万时华决定,第二天仍半带着张缚四处转,结果却不曾想,一大早张缚就提出要见俞国振。
张缚发现,自己凭借口才能让万时华闭嘴,却不能让他心服,因此他决定,直接把目标对准俞国振,因为鼻国振乃是万时华变化之源。
俞国振微微皱了一下眉,然后道:“我今日上午要与癸泉子和盗泉子两位道长商讨要务,下午约好了徐仲渊…,这样吧,你问张天如是否愿意夜间与我吃一顿饭,也算是为他接个风吧。”
他工作甚多,若不是看着方以智和万时华的面子,可以让张缚等到后天去。
万时华也知道俞国振忙得连轴转,愿意今天见张缚,已经是拨冗了。因此欢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回去与张缚说,张缚听到却是怒发冲冠:“俞国振也太慢待自己了,见方士道人和商贾都比自己要优先!
“既是如此,那就晚上再见吧。”张缚淡淡地道。
他也不四处去逛,在他看来那些地方全是惑乱人心的,他只是让万时华再领他去学校,连接听了一天的课,中午也在学校食堂里吃了一顿饭。待下午六时左右,俞国振派来的虎卫相请,他才施施然离开。
随着新襄的发展,餐饮业也迅速繁荣起来,每日十小时工作制和加班制度,使得新襄居民用于家务的时间极大压缩,自然而然,大大小小的食堂、餐馆和酒楼就应运而生了。口袋里有了些钱,不用在衣食住行上,难道用在嫖赌之上?就算想用在这二者之上,也要冒极大风险,嫖赌在新襄都是市政署所不能容忍的大罪,逼良为娼与诱人赌缚,上限都是死刑!
俞国振招待张缚的,乃是一家名为“听潮楼”的酒楼,生意甚为兴隆,若不是俞国振派人提前来订包间,只怕还得等一会儿。
“一直忙于俗务,怠慢了天如兄,还请恕罪。”看到张缚一本正经的模样,俞国振笑道。
“我此来新襄,大开眼界,酒菜之类的就不必见识了,济民,我只问你一句,你心中究竟是在想什么?”张缚一开口就带着火囘药味,让相陪的万时华、章篱等人神色不善。介国振洌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此话怎讲?”
“你在学校中将大量的时间都耗在实学之上,却仅在国文中教授少量的经义大道,其内容甚至还不如诗词歌赋多,你莫非认为,孔孟大道还比不上你的实学?”
“我记得张天如也曾称故徐阁老为师。”俞国振平静地道:“如今天下,有张天如这样的人去研究孔孟大道,我和新襄的这些学生,哪里用得着再向这个方向努力?”
此话一出,张缚原本气势汹汹的顿时又哑然,他看姜俞国振好一会儿,然后苦笑:“我就知道,辩论,茂生辩不过我,我却辩不过济民。
这一笑将那火囘药味儿化去了一些,张缚调整了一下心态,讲大道理显然没有用,俞国振借力打力的功底如今已是炉火纯青,那么就只能就事论事了。
“济民,我一大早就求见,你却先见了道人,后见了商贾,如此重方术财货,非待天下英雄之道。”张缚很诚恳地道:“我知道济民胸怀大志,但既是如此,就该礼贤下士,不可轻贱士子!”
俞国振听了大笑起来。
张缚有些讶然,然后旁边的万时华面红耳赤,扯了扯他的衣袖:“南海伯见两位道长,正是为了我华夏大事。南海伯说,孔子亦曾问道于老囘子,道家实为三教之祖,如今邪神教派纷纷入侵,惑乱人心,令我华夏子民不敬天地不拜祖先不礼圣贤,实在是要于根源处坏我华夏根基也。但此事不可以刀兵制之,只能以我三教之精妙意旨,与之争夺人心。可三教之间门户之见甚深,而三教内部也是派别林立,须得有大智慧大毅力,统合经卷,去伪存真,方能得行。此事非一代人能完成,南海伯以为,愚公移山,自今日始,故此请盗泉子道长主持编各教经典之事,以备今后学者辨析盗泉子道长俗姓张,乃龙虎山天师后裔。”
此语说出,张缚顿时激动起来:“俞济民是要编道藏?”
“不只是道藏,儒藏、瘩藏,都要编,诸子百家,都要编。”俞国振目光变得奇亮:“我华夏文明绵延至今,虽有《永乐大典》在前,惜哉专藏于朝廷,我要编一部大百科全书!”
张缚激身求动,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盛世修典,当初成祖皇帝修永乐大典,可是曾经召集文士老儒两万一千六百人,这才编出那部遑遑巨著,而现在,俞国振竟然有此志!
张缚毫不怀疑,以俞国振的财力,确实能完成这事情。这可是千古留名的美事,哪怕只要在其中囘出一分力,都意味着为道统传承立下大功!
然后他猛地想起,自己方才还觉得俞国振先见盗泉子乃是轻慢士人之举,顿时脸如火烧,心中也暗暗埋怨,万时华为何不早说此事。
他还未蠢到问为何找道士编文,成祖编永乐大典,负责主持此事的除了解绪,另一个便是和尚姚广孝。而有了此事,他也不好再说先见徐林的事情,谁知道这里是不是又有什么大事项等着抽他的脸!
“我此次来新襄,一来是拜望万茂声,二来是向济民你化缘的,我要做一傅大事,需要些银钱。”
俞国振目光猛地锐利起来:“要倒薛扶周?”
张缚大惊失色。
四二九、阉戚清流实一家(二)
薛即薛国观,在张至发之后,为现任内阁首辅。周则是周延儒,既是科考时录取了张溥的座师,又在蛰居数年之后站到了东林复社这一边。
张溥这些年来一直运作的便是这件事情,当初崇祯七年时,他便试图募集资金,甚至求到了刘泽清与吴三桂头上,这才凑足了田家所要的银两,可结果却被俞国振在南‘京城外一锅端了。让他此前的计划落空,信誉也坏了大半,至少刘泽清与吴三桂都是不听他的了。
现在薛国观对他追迫甚急,他一方面通过吴昌时打探薛国观的动态,另一方面,决意再次推动周延儒入阁。
可是没有想到,他自以为隐秘的事情,被俞国振一口叫破!
“济民,你如何得知的?”他咽了口口水之后问道。
俞国振抿了一下嘴:“天如兄,你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很隐密,就连阮大铖那边,你都敢伸手……消息怎么会传不出去?”
阮大铖乃是天下公认的阉党,身为复社清流领袖的张溥向他伸手,这个消息的震撼,让万时华霍然站起,厉声喝问:“天如,是不是真的?”
张溥脸青一阵红一阵,觉得又被俞国振狠狠抽了一记。
“虚……虚与委蛇罢了。”他喃喃地说道。
“休得诳我,阮大铖尖刻,天下谁人不知,为了官位,可以认贼为父的……你答应他的条件,莫非就是周宜兴入阁之后。阮大铖也起复?”
“那如何能成,实不相瞒,我也当面说了,他声名太臭,不可起复,不过……他若是有要好的友人,倒是可以推荐入朝为官。济民。你也知道,密之的父亲方植夫先生,便曾是阮大铖好友。”
听得他如此强辩。万时华面sè如灰,眼中说不出的失望。
这就是复社领袖,就是万时华曾经寄予厚望的年轻一代学者!
一时之间。以往俞国振曾经和他说过的许多问题,都瞬间融会贯通了。
“张天如这个人,倒不是什么恶人,但他的道路很明显是错的。他以为可以以风花雪月为幌子,用纵横家的手段来cāo持朝政,其实,他永远跳不出自己的圈圈子,井底之蛙罢了。”
自以为手段圆通,其实……终究是坐在井中望着天啊。
俞国振笑了笑:“这倒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连阮大铖天如都许下了好处,那么我若出银,能有什么好处?”
张溥哑口无语。
他还真没有想过,该给俞国振什么好处,来的时候。他觉得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应该能轻易说动俞国振,而且俞国振也富有,拿个几万两银子出来,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个,朋友有通财之谊……”
“天如兄确实是我俞济民的朋友。却不是可以通财的朋友,交情没到这一步。”俞国振说这话时仍然和和气气,看上去温文尔雅:“比如说,天如兄一路上跟着田国亲派来的人同行,两人可是谈笑风生,以天如兄之聪明,当然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可是天如兄却不曾提醒我,想来也是觉得,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