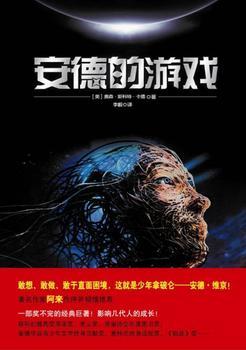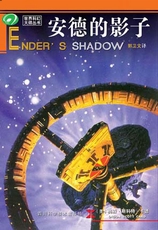论职业道德的必要性-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想这好酒都让她跟他给糟蹋了,跟喝白开水似的,得有多对不起这酒,还没等她替这酒可惜完,奔解放哪里会让她独善其身,自己喝了大半,就硬是喂她喝,瞅着被他滋润过的瓶口子,她满眼嫌弃地想躲开——
“你开的,你来喝。”她打定主意不松嘴。
一张嘴,这完全是个错误,让他迅速地喂过来,她瞪向他,不得不喝,才刚喝了口,酒才往肚子里进,他就把酒瓶子给拿开了,薄唇就堵了上来,舌头还钻了进来。
他想呀,谁喝不是喝呀,他喝了这么多,也得喂给她喝,就是跟她闹上去了,非得缠着她舌头乱裹,好半天才放开她,眯着眼睛,瞅着她在那里喘着气,“别走了?”
她还真没走,真留下来了,把手机都关了,打定主意谁也不理了。
对于这点,奔解放表示非常的满意,搂着她就睡了——
对于这个,弯弯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冷不丁的斯文起来,到叫她认为他是不是“转性”了?
她想背对他睡,偏让他搂着,非得让她的脑袋埋在他胸前,让她睡得战战兢兢,都快凌晨了,才捱不住磕睡虫,睡着了。
也不知道是几点,她睡得迷迷糊糊,身下是柔软的床,这个到是舒服,可腿间不知道是夹着什么东西,硬硬的,就那么抵着她,隔着薄薄的料子,像是要冲过来,让她十分不自在地睁开眼睛……
双腿给掰开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嘴里却是呜咽出声,眼泪一下子矫情地涌出来……
☆、026
她可能是慢了拍——
但他从来不知道叫什么慢了拍,男人嘛;大清晨的一柱擎天才是正常的事;让她睡了晚,不是说先放过;在他眼里心里那叫是情趣。
肉嘛;不能一时心急来了。
得有个过程,叫她没得办法了。
他想的就这么黑,好歹睡到大清晨的,一睡醒,底下支得老高,他还真不会对不起自个儿“兄弟”,只有这里好了;他身心才会一起好。
别嫌弃他想的这么直接,这么肉/欲,谁要是碰到一个男人,自个儿“兄弟”都不能立正好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才一睁开眼,就见她大半个人都裹在被子里,两条藕细撩撩的手臂,把被子夹住,露在外头,胸前更是一无遮拦,大半的坨坨肉儿毫无顾忌地诱惑他的眼睛,本就是清晨一柱擎天,再加上眼前看到的,他觉得肚子里都饿了。
是真饿,全身心的饿,饿得让他立即化身为狼,扒开她身上的被子——
“干嘛呀——”
结果,她挥过来一记,他没个防备,脸上就挨了下,顿时微带恼意地瞪着她,可她到是翻了个身,根本没理会他。
根本没醒。
他怒了,不带这样的,把人勾起了兴致,她到是不醒——
可摸着下巴,不醒更带味儿呀,最好是他让占领了她的领地,被他撞得一颠一颠的,才醒了,那才最好。
都说是恶趣味,还真是恶趣味了,他一向就这样子,很爱完成脑袋里想的东西,想到一出就是一出的,真叫他自个儿高兴了就好,通常不太去关注别人的想法。
“捆绑,真是个技术活。”
把人的双手都用他自个的领带绑起,绑在她的身后,就这,她还没醒,跟睡死了一样,这让他无比庆幸她睡得死,不会轻易给弄死,更是得意自己的捆绑术,把捆敌人的最佳方法都在她身上淋漓尽致的用上了,还不让人发现,更不让人立即醒来。
他赞叹地看着她,被子早让他给踢到地面上了,她整个人硬是让他小心翼翼地摆成趴睡式,两腿儿微微张,隔着薄薄的蕾丝底裤,里头聊聊地映出里头的幽色,隔着薄薄的料子,他的手指就急不可耐地按了上去,跟个急色鬼到是一般无二。
才那么一碰,他就把薄料子给拨开,瞅着闭合的娇艳花瓣,连眼睛都顿时染上红色,整个人趴着,黑色的脑袋她两腿间挤——
许是下意识的,她的双腿并拢了,刚好中间把他的脑袋给夹着,不能进,也不能退,他到是不恼,索性控出舌尖来,舔/着那花瓣儿,一下一下的,想叫花瓣立时就开了,好把他的“兄弟”给迎进去。
可——
她偏就跟他作对似的,让他那么使出手段一逗弄,她到是动情了,渗出来的晶莹玉液,都让他咽入嘴里,眼瞅着她眼睫毛一动,估计是真要醒来了?
还真是,当她一睁眼,他再顾不得,迅速地坐起来,把她的腰儿一揽,就让她光明正大地坐在他身上,而底下,他的好兄弟已经是老马识途般,一鼓作气的进去,他盯着她,刚好瞅着她瞪圆的眼睛——
那一双眼睛,是震惊,是惊愕,更多的是委屈!
低下头,凑到她眼前,舌尖点过一点点湿意,“惊慌什么呢,哥哥想你了呢——”他说话的同时,还别有意味地顶向她,顶得她呜咽出声,都没觉得有什么,“好歹也叫哥哥尝尝你的味,不是吗?”
她顿时脸就红了。
却让他撞得上下起伏,高高低低的。
她的身体,开始疼,后面接受的到快,天雷勾地火的,一勾就着了,连她的那点委屈看上去都有那么一点假。
两拳头有气无力地朝他身上捶,她到是清楚自己的位置,没点付出就想让奔解放为她办事,除非太阳打从西边升起来了,她到是不介意这个,太阳就是从东边落下,她也不在乎。
说白了,她这个人说好听点是圆滑,事事都面面俱到,说难听点,那就是她这个人自私自利,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把自己从各个方面扩散出去。
“都是你,把我弄疼了——”她抽噎,还瞪他,拿捏着一个分寸,不想太过头,也不想太没有表现,“怎么能这样子,趁我还睡着,就、就……”
后面的话都能嗓子眼了,愣是没叫她说出来,都是他狠狠一撞,像是撞到她心口上一样,叫她急慌慌的。
她自己送上门来,都说是早料到有这么一回事了,有一点叫她意外,原以为是昨天晚上就会发生的事,到是成了早上来发事儿了。
“我就、就怎么了?”他还贱,学她不稳的气息讲话,还把脑袋手搁在她肩头,往她嘴边偷咬了口,一脸的得意,“哟,我怎么了?”
里头涨涨的,叫他塞得满满当当的,都塞满了,还嫌不够似的,还往里推,仿佛要把他的所有都往她身体里送,她一张口,全是呻/吟的声,落在她自个耳朵里,却让她都觉得自己是在享受,而非是磨难。
这念头叫她脸一黑,还没等她反抗,人已经让他压向床里,都说了,她背对他,于是这么一压,就成了后那什么式的,据说这样子能入的最深最长——
还真是,她觉得自己都快透不过气来,每每的进来一次,她的胸疼,叫他的手给捏着,不止是捏,还揉弄,揉得她老疼,都快有种要不得的错觉,觉得那些都快叫他给捏爆了——
她这是纯天然的无毒副作用,被捏爆了还得去修修补补的嘛,虽说尺寸会大,她还是敬谢不敏的,只是,这姿势更难受,感觉血液全往脑袋里涌去,臀部高高地翘起,就他一手提着她腰,窄臀那撞得狠。
一下下地,肉体撞击的声音,“啪啪啪”的响,她的眼睛盯着自己腿内侧滑下来的湿意,让她羞意顿时涌到最高点,“混蛋,你给我出去呀——”
她懒得再装了,在他面前还叫他“哥哥”,叫得她都恶心死了,再说了,甭管她身体是多么的敏感也好,还是能享受这种事也好,反正她现在火大了,一时间就不管不顾了。
她还推人!
就是奔解放没料到她这么做,冷不丁地就像上次那谁谁的,叫她推开了一样,两身体相接处,也分得开开的——
她立即躲到一边,拉起被子,无视腿间的空虚感,戒备地盯着他,只盯着他的坚实胸膛,别的一点都不敢看,生怕一不小心,就看到他那个儿。
镙丝一下没了镙帽,他能善罢干休?
别的还能纵容她一下,就这事儿,他一点都不想纵容——所以,他笑眯眯地看着她,用眼神跟她说明一件事:她今天必须倒在他的床里!
☆、027
愿望可强大了,强大的叫人不忍直视。
瞅着她酡红的小脸;他眼里流露出不容错认的意乱情迷;或者说迷恋也成,不对;就是迷恋又怎么了?他从来不在乎承认这件事;早在他疯狂地想把这地儿都翻过来找人时,就晓得他早就给她迷住了。
的确不是个好消息,先动/情的人,总是比较卑微,他一贯觉得自己卑微,低头瞅着她,被他硬生生掰开的腿儿;娇怯怯的菊/花儿,紧紧地闭合着,再往前,湿漉漉的,浊白的与透明的液体都相聚一块儿,叫她的腿间找不出一丝干净的地儿来。
“乖乖,这颜色还跟以前一个样嘛,是洗过了?”他问的可不给面子,还打趣她,偏一打趣完,都不管她会不会生气,径自扣过她的小腰,把自个儿都给送了进去,不是浅入门口就算,而是一鼓作气的往里冲——
冲的她快翻白眼,许是刚才的滋润,让她再没有感觉到疼,可那么种硬被撑开的感觉还是留在脑袋里,双手立即挥舞着想让打他,却让他还是换了个姿势,给压趴在床里,是他最爱最爱的姿势……
“你才洗过了,你洗过百千回了——”她嘴巴不饶人,心里也奇怪呢。
谁也不会没事就盯着自己那里看,可被人逼着看,那也是有的事,尤其是奔解放这样的,非得压下他的背,非得提起她的臀部,非得就用那么个羞耻的姿势,让她自个儿的眼睛好好地看着她那里——
还真的,她看得一清二楚,那里还直是粉色的,连她自己都奇怪,都说做多了,这颜色会变的,她到是没觉得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不是粉色了,是那种娇娇的颜色,被他不知怜惜的弄过一回,早就变了色,都充了血,跟个刚绽开的花朵儿没什么两样。
此时,那里正好一抽一抽的,她都能觉得自个儿那里面都是抽抽的,空虚的叫她忍不住想闭紧双腿,却叫他的双手拉住了两细撩撩的腿儿,烫得跟被烧得火红火红铁杵一般的物事,往她那里挤了进来。
“唔——”她忍不住闷哼出声,脚趾头崩得极直极直,脑袋一下子全埋在柔软的枕头里,淹没了她所有的声音。
好胀、好烫!
他往里一送,跟她唇瓣一样色彩的小嫩瓣儿,被他硬生生地挤开来,那种颜色叫他的眼底更深,再往后轻轻一撤,像是极不情愿的,被迫地吞出来,连带着一点点淫/糜的白沫,是那么的叫人他心乱神迷。
“乖乖,怎么能说这种话,跟你开玩笑也不行了吗?”他恬不知耻反问,把握全局的神情,让他看去更加迷人,一边说话,还一边撞她,叫她还再敢乱跑,再乱跑一下让他找不着,就有她好看的了,——比如做死她,比较好。
嗯,他最喜欢这个办法,再慢慢地滑出来,提着她想乱扭的小腰,脑袋凑到她腿间,凑得近近的,他的手指开始作怪,将早已经迫不及待闭拢的花瓣儿给微微的分开——
嗯——小小的洞口,被染成艳红色,从里面渗出来的液体,晶亮亮的诱人光泽,还更叫他眼神儿发狂的是她在抽抽,一下一下的抽,他用手指试着往里探,才入小小水帘洞口,里头的内壁就疯狂地朝她挤压过来,一瞬间,似乎从他尾椎骨里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