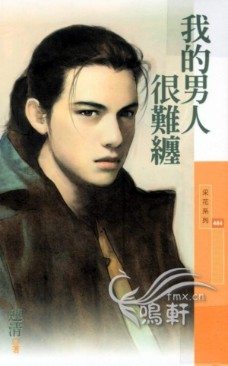我的大学不恋爱-第2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找词劝慰,还一口一口地喂我妈吃饭。我妈边吃边掉眼泪,哽咽着说小财以前也这么喂过她。
那是蔡小财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妈病了一场,病得下不得地,在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蔡小财每天傍晚下课后就赶去医院,用饭盒去医院食堂帮妈打好饭,然后坐在床沿喂妈妈吃,很细致,很用心,常常是一餐饭要用上半个多小时。那次妈病得多重啊,差点就走了,可每次我哥喂她饭的时候,她都会笑,开心而满足的样子。等病奇迹般地好起来后,妈有次告诉我说,那回要是她走的一病就走了,不担心我哥,只担心我,但想着蔡小财那么懂事,也会把我照顾好,就好像什么都不担心了。
暑假期间(4 )
妈妈这么说,终归有她的道理。
记得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跟蔡小财一起坐卧铺汽车回老家。说是说冷暖空调,也只不过写在车身和车门上骗骗人吧了,一路上压根就没空调。大冷天的,都有了下雪的迹象,就算把车窗关得再紧,也还是觉得冷,气温低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风从罅缝里嗖嗖地齐进来。
车开出没多久,睡下铺的蔡小财却神经病地问我热不热,说他都快热死了。我当时已经冻得流鼻水,于是借题发挥地把他臭骂一顿。可过了一小会,他又开始叫热,接着就把外套给脱了下来扔给我,说他想睡睡觉,外套里有东西,叫把外套压在头底帮他保管好。我有些不情愿地照办了,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好处。外套睡在脑袋下,再把两边一拢,耳朵很快就暖和了。
半路,蔡小财问我:“小菜,你还冷不冷?”
我刚学着他那腔调,反唇相讥:“小财,你还热不热?”
他说:“我现在不热了,刚刚好。”
我说:“我现在不冷了,刚刚好。”
那时候我根本就不晓得,蔡小财这小子原来也歹毒得很。他明明不热,他明明知道我冷,也明明知道要是他脱件外套给我挡风我不会肯,所以才虚晃一枪,玩了个小伎俩。现在想起在车上的那几句对话,怎么都好像有种心酸的幽默。
最好的兄弟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在你叫冷的时候,他在边上叫热,他当然不是真的热,他只是想往你身上加件衣。可是从今往后,我冷了,蔡小财他还会叫热吗?在没有阳光的天堂,他冷了,我又如何在他身上加件衣?
抬起头,操场的上空是一朵朵的云,我想知道,这个时候我哥他躲在哪一朵后面。昨天才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我哥他走时穿的那件黑色外套是不是已经被淋湿?我突然毫无来由地问信海欣。
“你说我哥他会冷吗?”
“为什么会冷?你是不是又想起什么了?”
“我没想什么,我不想了。你再跟我说说我妈对你讲过的话吧。”
信海欣告诉我,我妈并不知道蔡小财是自杀的。我妈没文化,她只知道她最心疼的儿子死了,到在楼顶,却不知道蔡小财是怎么死的。
我妈说——小财这孩子懂事,拿上大学来说吧,才上了一年,就没再问家里要过一分钱了,学费生活费都是自个挣。后来小菜也上大学了,他连小菜也一块负担了起来。听他们说城里挣钱也难,这孩子怕是累坏了。姑娘你说我家小财他是不是累坏了?
他跟小菜不同,他忠厚,小菜就调皮多了。年纪小那会,小菜再高的树都敢爬,他就不敢,看见小菜爬上去了,他劝不下来,很害怕,就跑回去叫我去劝。这孩子肯做事,但胆子小。姑娘你说他们学校怎么连屋顶都要打扫?那么高,上上下下,小菜怎么都会害怕啊!姑娘你说我家小财他是不是在屋顶给吓着了?为了多挣那么几块钱,这孩子咋就啥都不怕了呢?
我们农村,最讲究兄弟和睦。小菜没他懂事,人也懒,以前还动不动就欺负他,打呀骂呀的,都有过,可他在我们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都护着小菜。有了什么成绩,都说成是兄弟俩一起的。他还说以后工作了,要跟在城里买个大房子,跟小菜住,再把我们接过来。
小财每个礼拜都写信回去的。我不识字,每次都是他爸拿着信念给我听。他总说他很好,小菜也很好,叫我们不要挂念。虽然离家远,可他在信里叫爸妈,我就感觉这孩子在跟前一样。现在好了,想挂念都没得挂念了……
百里挑一的女研究生(1 )
第十章百里挑一的女研究生秦琪,因为去南京呆了几个月,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淡出了高老头的生活。这对我而言,也勉强算是件好事。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看不得女生,长得漂亮的,看着难受,因为要刻意去憋住某些冲动;看得丑的,看着更难受,比如秦琪,我是看一次晕一次,从没出过意外。
下午上课的时候,信海欣已经约好一起吃晚饭,叫了我和高老头。回到寝室,高老头拨了个电话,找的正是秦琪,说自己有事,叫秦琪自己去吃饭。我在一旁听着,挺纳闷的,问高老头:“上回不是都说已经一拍两散了吗?”高老头嘿嘿笑着,不吱声,我就懒得追根究底。这段时间里,我自个心情坏得透顶,没心思掺和别人的事。
高老头没叫秦琪跟我们一块去吃饭,真是谢天谢地。连续好几天了,就是从信海欣告诉我,我爸妈早已知道蔡小财不在人世时起,我的胃口就差了许多,要是秦琪一到场,我怕是真的什么都吃不下了。我的情绪糟糕到了极致,似乎变得异乎脆弱,常常不苟言笑,脸就像内心的伤痛一样,沉默着,沉寂着。这是一件比蔡小财的死更让我难以面对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出门之前,接到盛可以的电话。很奇怪,知道是她之后,我心竟然止不住地激动。她没有按时来学校,我嘴巴上不说,心里头却天天在担心着,即便在情绪乱七八糟的时候,依然剔除不了对她的担心。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我不承认这种担心是因爱而派生出来的想念和牵挂。
盛可以说:“蔡小菜,你还好吗?我昨天晚上梦见你了。”
我急切地问:“你到底怎么啦?开学都好几天了。”
“我有点事,过段时间就去。对了蔡小菜,我不在学校,你要照顾好自己。我昨天晚上梦见你哭了,我抱住你,你还是哭。”
本来只是胸口闷,听盛可以这么一说,我还真想哭,还真想抱住她。她让我感动了。这种感动也信海欣和高老头他们带给我的感动似乎不尽相同。为此,第二天我还偷偷请教了一位对感情之事颇有研究的老乡,终于知道有些感动里头是藏着心动的。感动加心动,很快就变成了冲动。我没告诉任何人,我有点想跟盛可以谈恋爱。
我平生第一次认真地想跟一个人谈恋爱。想谈恋爱属于意淫范畴,意淫对象:盛可以!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以前我只是想她来泡我,怎么都显得不正经,再说她也没真的来泡我。
去校门口跟信海欣会合,一路上,高老头把手搭在我肩上,叽叽喳喳说了一大堆,我什么也没听清,我的思想正悬乎着呢,正要想,要是盛可以真的来泡我,我要不要上钩这个天大的难题。
我给自己上钩列出了几个前提:第一,我对盛可以有情;第二,盛可以对我有意;第三,我哥对盛可以的感情很纯粹;第四,我哥在天有知,同意我提前谈恋爱。我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的,觉得这些前提基本上都可以成立。也就是说,在我的想象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指的当然是盛可以对我放线下饵。
没想到信海欣会迟到,而且一晚就差不多半小时。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只要是约我蔡小菜见面,她九次有十次会提前。难道现在学会耍大牌了不成?我和高老头等得很不耐烦,但仍然很一致地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脸和面子可是两回事,脸大并不代表面子大。
抽了两支烟,信海欣没等到,倒是冤家路窄地等到了秦琪。我假装没看见,高老头好像也想假装没看见,但秦琪没假装没看见,三下两下就蹦到面前,摘星星似的提了高老头的耳朵,十分花痴相。看样子,这老女人是一动情就糊涂了,虽然高老头对她忽冷忽热,但她还是把他当成幸福在依靠。高老头责任重大,可他怎么看怎么不像负责任的人。
高老头被秦琪强行带走,我求之不得。他们刚走几分钟,信海欣就到了。遗憾的是,我还是不小心占了下风。趁高老头走而信海欣未到这个空档,我去体育馆上了个厕所,大门关了,走的小门,也就是后门。一泡尿,把所有的优势都给冲跑了。我再转到校门口,信海欣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
信海欣张牙舞爪道:“蔡小菜!你什么意思,我请你吃饭你还敢迟到?!”
我百口莫辩,只好耍赖:“我有什么不敢的?我刚才上厕所还敢走后门呢!”
“好,你胆大包天好了。对了,高老头还没来?”
“被那个百里挑一的研究生带走了。”
“啊,不会吧?他们到底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啊,谈个恋爱怎么跟玩魔术似的。”
“你管那么多干吗?别人玩魔术又不是玩你。”
找了家餐馆,坐下来,点好菜,信海欣跟我说起盛可以。她晚到了半个小时,是在接盛可以的电话。盛可以估计是找了我之后就打电话到女生寝室给信海欣了,跟信海欣说她一时半会回不了学校,要她帮忙请假。
我问:“盛可以她怎么回事?是生病了还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信海欣说:“没有啊,她是叫我帮她请病假,不过压根儿没生病,她只说她在外面有事。”
“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我问她,她也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我越来越看不懂她了。”
“哦。那她有没有跟你说起我。”
信海欣的神情突然阴沉下来,很难看地笑了笑,说:“蔡小菜你想知道什么?她说她其实挺想跟你在一起的。”
我不再说话,一种心理的落差压迫着我,有些许受伤的感觉。信海欣的表达,似是话中有话,其实挺想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意味着不会跟我在一起?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我的逻辑推理能力一直都还可以。
想起盛可以在白玲玲面前的失态,想起信海欣说她回到寝室骂自己婊子扇自己耳光,想起那天晚上在九教看见的那个奔跑的身影,我也觉得,盛可以变得神秘莫测了。
九教再次闹鬼的时候,我正坐在床上,两脚泡在半桶冷水里。
才十点半,我还是准备睡觉了。寝室里除了我,别的室友都还没回来,自习的自习,恋爱的恋爱。好些日子没睡过好觉了,脑袋和眼睛似乎都有点充血,说不出来的难受。原来在大学里我是没有睡前洗脚的好习惯的,这也不能全怪我,大家都差不多,我又怎么好意思标新立异?
记得刚入校不久就听一位学长讲过句挺经典的话,说是在大学里,只有脏一点才能与同学打成一片,要是太爱干净了,拿不准就会遭人恨。为什么会遭人恨?我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悟得其中真谛。分析起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如果某个人太爱干净,那么别人偷起懒来就会有对比,对比中自然就会产生心理压力,就会不自在。
其实这天晚上我决定洗脚前,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首先,我害怕我这么一来引起寝室其他兄弟的众怒;其次,我自己也是不情不愿的。我洗得再干净,就算用洗衣服粉使劲地搓啊搓,等他们脱了袜子上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