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给熊猫笑一个-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摇了摇头,不想再麻烦自己的脑袋,光把龚千夜和白翟塞在里面,就已经超我负荷了。如果再把这个认知中非常单纯的家伙给想复杂,那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不是每个人的大脑,都能生得像白大少爷那样,可以无限使用的。我笑自己多心,抬眼一看,居然已经轮到我们结帐了,莫怪这家伙叫得这般急。
我连忙把篮子里的东西取出来,抬脸时,依然无可避免地瞅见了售货员异样的眼光。两颊不由地发烫,我闷闷地说了句:“Sorry!”
白翟,果然是我命中注定的大克星。什么事只要一牵扯到他,铁定倒霉,不是丢脸,就是惹事,真是见鬼了!
我提着一肚子的怨气,气呼呼地拉起袋子就走,把付钱的光荣任务全权交给了身后的齐放,率先走出超市。
一踏出大门,迎面扑来一阵热风,火辣辣的烫,扑得脸颊一阵疼痛。眼睛还没来得及眨一下,就看到了刚从对面香港超市走出来的白翟。
他似乎也没料到我们这诡异的碰撞,微微楞了一下才别过脸去。面上的表情,清清冷冷,骤现在烈日下的细瘦身型,如一道和煦的微风,却透着莫名的冷冽。
哈,躲我?他白大少也会有避开我的时候么?我冷哼一声,觉得自己真该抛弃形象,很不给面子地给他来个仰天大笑。可不管怎么想,都无法压下心中那股不停上窜的酸涩感。
凭什么啊!这死男人!我愤恨地甩头,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也走出超市的齐放,正用比目瞪口呆还夸张的表情死死盯着我。他那双漂亮的浅眸中,满满的都是诧异。
“做啥?”我没好气地问。看毛啊看,别以为你是老外,我就不敢喊视觉非礼!
“彤琪,你……”他稍稍犹豫了下,才在我狰狞的表情下出了声,“你……不会觉得重么?那个袋子里起码有40斤的东西。”
“什么?”40斤?我么?我赶紧低头一看,果不其然,一冲动,还真把所有东西都给提出来了,难怪……难怪我老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啊!小心——!!!”他突然的叫声,却抵不过地心的引力。
只听得“砰”得一声巨响后,是我无脸见人的那声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呜,我错了!真的对不起啊,齐放,我不是故意的,真的、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没想到你的脚放得那么近啊,呜呜……
别恨我,要怪……就怪那个从一脸不可置信,到笑翻天的臭家伙吧!
死白翟!
哼!
————————————墙角画圈圈的分界线———————————
郁闷地坐在台阶边,吹着晚风一阵阵。我望着干净的马路,心里却有几分寂寞。
忍不住地,我望向了厨房的窗口。那里人影闪动,喧哗吵闹,嬉笑怒骂声连坐在这边的我,都能听得清楚。
过年,或许就该是这样的吧?热热闹闹、兴高采烈;一大堆人围在一起吹牛打p,聊聊天,谈谈地,打打牌。
纵然现在我们身在异国他乡,纵然身边尽是些生人陌客,但这样的我们,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温暖。
不过,其实光这天气,就已经太过温暖了,我挥去满头的大汗,嘴角尤然带笑。活了二十来年,夏天的新年倒还真是第一回过。
我低头看了看表,时间已过五点半。今天的天气还算捧场,已稍稍有了些凉意。原本计划五点开始的party,如意料中的推迟了。
澳洲的夏天,哪怕到九点半都未必见黑,我的homestay嫌天气太热,早早打来电话,说要六点半到。正好我们手头的活儿也做不完,云南妹当然高兴地答应了。
那会儿,家里早已翻天覆地,连显然不擅长制作中式餐点的齐放,和不怎么会做家务的白翟,都被招呼成了免费苦力。只不过一个做得兴致勃勃,一个干得面无表情。
我收拾完自己房里的东西,就跑到院子门口等客人上门,反正别的忙也帮不上。刚才尝试性地踩进厨房,没几分钟就被踢了出去。
厨房里那叫一个乱啊,喧闹得简直不像话,客人来了后都在帮忙,包饺子的包饺子,洗菜的洗菜,拥挤的餐厅,热得可以不点火就煮熟所有人。而帮忙的人中,估计有些个和我差不多,非常的碍手碍脚。所以尽管大家都很努力地尝试着完成任务,不过过程却极不顺畅。略嫌没有耐性的云南妹,八成已等得一肚子焦躁。
于是,我这个麻烦二世祖想要进场,别说门了,连窗都没有。无奈之下,我被分到了外场——迎宾的。
这岗位听上去还满有魅力的,我也就屁颠屁颠地去了。反正心知肚明自己今天惟一的建树,就是邀请到了胡谷雨同学——他可是一能人,很有效率地和李沛霖同志平分了厨房天下。
看着渐暗的天色,心里突然有点哆嗦。于是自然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没有犹豫地拨出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枯燥单板的眩铃响了不久,就由一个中年妇女接了起来。她熟悉的“喂”声让我不由习惯性地拉出微笑,甜甜地喊了一声“舅母”,然后有习惯性地拉了拉家常,说了些客套话,再提前拜了个早年,才和电话真正的主人——我的外公外婆说上了话。
不长的电话,却打得笑逐颜开,并没有听到什么好事,连往常必有的红包今年也没了影踪。会觉得开心,单纯因为为听见了他们健朗的声音,轻快得让我好不怀念。
二老都已年界九十,外公更是九十二的高龄,不过身体还很强健,力气可不比我小。可尽管如此,这几年我被父母叫回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照母亲的话说,已是见一次少一次了,有机会就要多去见见,珍惜这两位从小就关爱我的老人。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有些害怕。我的爷爷奶奶去世的很早,死亡对我而言,总觉得是个过于遥远的词。小时候,常常会看到有同学红着眼睛,手臂上别着黑布,却是不明所以,只道是他的家里有人去世。
死亡,究竟是个什么样东西,我不知道。只觉得是很可怕的黑暗,消失的恐惧。其实有时候觉得有个信仰也不错,起码不会那么的怕死。
我承认自己天生胆怯,怕死怕得要命,连同害怕着……身边人的消逝。
听到熟悉的脚步声,我微微一笑,心情突然变得很好,自然地转头对上了那张和记忆中相差无多的脸:“怎么,偷懒?”
“你以为我是你啊?”白翟没有横我,只是将手中的饮料扔了过来,“尝尝吧,我从自己家里带来的。”
“是什么?”难得得,我没有任何怀疑,直接开了出来。或许,是因为现在的气氛,实在太过静谧,和谐到不想烦恼任何的不愉快。
“自己喝一下不就知道了?”白翟淡淡地回答,身体一躬,坐到我旁边。
“呵,也是。”我轻轻啜了一口,是以前未曾尝过的饮品,有点点甜,带着点酸,很爽口。有种依恋和怀旧的滋味,慢慢在胸口弥漫,漫得心里酸涩一片。
我知道白翟为什么给我带这个,因为它的味道,很像我们小时候常买的柠檬味棒冰,我和他那时的最爱。
我到现在都记得,它只需要两毛钱。在囊中羞涩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去院子里找啤酒瓶,然后卖给收破烂的,以换取一份棒冰钱。而这样的事,绝不只一次两次。
“你外公还好吗?”他突然问。
“恩,很健康。”我照实答。
“他是个好人。”
“当然了。”
“他那时教我的功夫,我都还没忘呢。”
“是吗?我倒是半点没记住,他老和我妈抱怨说我一点儿也不用心。”
“那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学,早上死赖在床上,怎么叫都不肯起来……”
“哈哈,你……还真是不记好事。”
“是吗?我倒不觉得。”白翟挑了挑眉,在我发作前,聪明地换了个话题。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普通到没有滋味。可是谁也没有停下,就这么简单地继续着对话下去。
我没有转头看他,只是小口、小口地喝着饮料。他贴着我坐在一边,两手向后搭着,撑着他消瘦的身体,偏偏又是很man的姿态。
我的余光,可以看到他微抬的下巴,勾勒着迷人的曲线。
小仔,从来都是那么漂亮,比女孩更清秀动人,我不知嫉妒过多少次。比起齐放,他更多了一份成熟的魅惑,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男人味,像极了让人昏昏欲睡的熏衣草,诱人犯罪。
我有些害怕地转开视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所动,那明明应该是被我看到发腻的脸。传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那个就……
莫非,我已提前步入了如狼的年纪?妈呀,俺不要!俺才二十放出头啊,不能这样堕落!
我默默念叨,将心里那些可怕的杂念统统抛开,反反复复地啜饮着他送的汽水。
为什么会这么慌张?这样的靠近,本该理所当然。可现在,却已算不出流年。我不记得有多久没像这样挨身贴坐在一起,只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总这样相伴。
白翟完美的下颚曲线,像刀刻般留在我的心底。不曾,淡忘。
他像最特别的存在,最诡异的风景,明明已经远去,明明已经离开,一切的一切,却又如同冤魂不散,始终停留在我的心里。
有时,我和卓奇爬完山,也会这样的贴身而坐。每每那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去比较他们表兄弟的下巴,中了邪般的罪恶。
往昔的一幕幕,如此清晰地在眼前流转。可那些都已过去,现在,连我的男友都已经不在。
时间过得快么?既然这么的快,那为什么那么遥远之前的事,却还是忘不了?
…小仔,小仔,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生日愿望可以说的吗?
…为什么不可以?
…那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的?我的生日愿望啊,是……长大以后娶小仔!
…啊?真的吗?
…对啊!我会保护你的,小仔!
…可是……
…可是什么?
…我是男孩子,应该是我娶才对吧?
…但我比较强啊!
…总有一天,我会变得比你强的!
…切,怎么可能!
童言,纯真得好不可笑,无稽而无忌。
我还在为往事笑不可抑,白翟却突然在那边微笑开口,目光深邃,唇型妖异:“小彤。”
“恩?什么?”
“你说我嫁给你,好不好?”
乒——乓——
一声巨响。
瞪到快爆的眼睛里,刻上了白翟略微慌张的眼神。
他有些焦急的询问,传进耳里,却触不进脑海。
无法消化。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嗡嗡阵痛的脑袋里传来无数次的反复——“我嫁给你,好不好?”
他他他……说了什么?他要嫁给谁?啊?
长大的气息(一)
嫁给我,嫁给我,嫁给我……
我觉得自己的眼前就像出现了一道滚动条,扯着“嫁给我”三个字,配着从小到大不停巨变的白同学,来回地转个不停,转得我两眼发绿,头晕心慌。
待回神时,我已正身坐在餐厅里吃饺子啃牛肉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好的红酒,已盛满了漂亮的高脚杯。满桌的盘子皆布着红红绿绿的菜,虽算不得色香味俱全,倒也颇具诱惑。
当完大厨的胡谷雨同志似乎情绪很高,酒是一杯接着一杯,很快就喝了个红光满面,操着一口破到不行的英文,和我的homestay大侃特侃。
而那两位不懂半点儿中文的中年夫妻,因为被我熏陶甚久,所以对破英文的理解力也不同凡响,和他是聊得有声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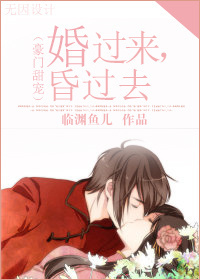


![[综漫]一觉醒来,穿越成神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33/332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