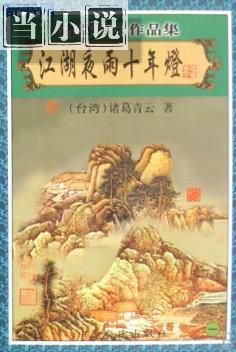夜雨霖铃-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面四个字像拳头般重重打来,征豪咬着牙说:“胡说八道!攸君是我的未婚妻,七年前有婚约为盟,七年后有皇上指腹为证,你要命的话,别随便信口开河!”
“别拿婚约或是皇上的指婚来压我,你应该问问攸君,她真正想嫁的人是谁?”张寅青冷笑地说。
两个男人的眼睛同时盯向攸君,只见攸君惨白着脸,艰难地说:“征豪,我一直想说,我们……不可能了……”
沁凉的秋夜,他怎么觉得身上的汗却一直流呢?在这几个月中,征豪就觉得攸君有满腹心事,对他有距离,一点也不快乐。
原来,在这他无法触及的七年中,美丽的她仍然被别的男人占了先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攸君甚至连最起码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他。
“攸君,我不会因为你的话就轻易放弃的!”征豪说着,叫手下丢过一把剑给他,再狠狠地看向张寅青,“你要我的未婚妻,就得先看我的剑同不同意!就我和你,单打独斗!”
这也正是张寅青要的。好个征豪!还算是个人物,没有以多欺少,用地势及人势,不光荣的取胜。
两剑交锋,在漆黑的夜里,处处是寒光,看得人屏气凝神、心惊胆跳。在几个招式后,连攸君都看得出来他们不是闹着玩的,那每一个举手投足,都能够达到致命的效果。
“你们快停止呀!”她心焦地喊着。
男人对男人,无论是以什么理由开打,到最后都会迷于那邪魅的剑术,不分出胜负,绝不终止。
结果,征豪的帽子被打落,张寅青的衣带被削掉一截。
然后,招式较正规的征豪,渐渐不敌各家剑法兼有的张寅青。在几个翻滚后,张寅青击落征豪的剑,但他没有进一步直指他的喉间,只是暗自调匀气息说:“好身手!不过抱歉的是,攸君我必须带走了!”
“本公主不许!”建宁长公主指挥着说:“来人呀!将张寅青这逆贼抓住!”
“额娘!”攸君奔到张寅青前面,阻挡地说。
“姜嬷嬷,将格格带回房,我不准吴家人碰她一下!”建宁长公主狠厉地说:“谁要带走格格,就是死路一条!”
“额娘,他不是吴家人……”攸君挣扎着,眼看无望,又叫道:“那么也抓我吧!我才是吴家人,为什么不抓我?我也要去刑部,像阿玛和阿哥一样的死!一样的死!”
“攸君,不要说死,我会活着来带你的!”张寅青一面心痛地大喊着,又一面要抵抗准备抓他的禁卫军,在这寡不敌众的局面下,他的哲学是就义也要从容,所以,仍一派镇静地说:“爱我,就要信任我,我们是彼此的精神支柱,不准说死,明白吗?”
攸君只觉得肝肠寸断,经过征豪的身旁时,她以泪眼望着他恳求地说:“征豪,帮帮我们……”
征豪凝视着手上的血,并不看她,只是沙哑地说:“不想失去你的不仅是我,还有你可怜的额娘。”
看起来,一切都是她不对!有婚约在身,又爱上张寅青,既已要委身张寅青,偏又不舍北京,到最后,除了伤害还是伤害呵!
在月洞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她看到张寅青披众人押走,张寅青回首望她的那一眼,是他向有的洒脱和笃定;而征豪也抬头看她,那是一种梦碎的表情,令她涌出新的泪水来。
攸君不能吃不能睡,日夜就是痴望着那缀满琥珀、珊瑚的串铃子。姜嬷嬷哭着劝她,句句的话却如耳边风,吹不出一丝涟漪。
建宁长公主来时,母女就是互不相让的争执。攸君坚持要衙门放了张寅青,她说:“寅青根本不是云南的奸细,你们不能随意诬赖他,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呀!”
“看他的行止,也不像正派的人。”建宁长公主固执地说:“论家世人品,他都没有征豪好,你年轻不懂事,他就是看在你是格格的身分上,一意的攀龙附凤,这样没来历、没背景的人,岂是你能下嫁的对象?”
“额娘,寅青完全不希罕我的身分,他甚至不屑我是吴三桂的孙女,女儿嫁他,算是高攀,他……”
攸君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怎能吐露张寅青是反清志士的后代,孤傲地不愿依附清朝呢?现在他在大牢里,还抓到与云南有关的证据,若她表明了,不是正好罪证确凿,让他因大逆之罪而往死路送呢?
建宁长公主以为攸君是误入歧途,一时迷昏了头;而攸君又有太多不可说的的内情,弄得刚团聚的亲人,净站在自己的立场想,将七年的隔阂无情地梗在面前。
就像张寅青给她串铃子时所说的,那是他的世界、他的家,毫不保留地交到她手里,而他也真的做到了,甚至连性命也要为她而丢,倘若如此,她也只有以死来相报了!
他在刑部大牢,她在公主府,不是共存,就是共亡,绝对没有一人独活的道理呀!
建宁长公主看出女儿顽固的决心,心急之下,又把征豪求了来,希望他以一腔柔情唤回攸君的理智。
好几日过去了,征豪一直没有从混乱的情绪恢复过来。攸君,这个他心中最完美的女孩,如山、如水、如花、如玉,已高高地供在他生命里的殿堂,谁知坠入凡尘,竟改变了初心,化成一道利剑,直直劈裂他的爱!
所以,那牡丹花的软轿,真的在七年前花飞花舞的春天消失,不曾再回来,也不能再回来了……
但他们有婚约啊!攸君怎能绝情负义呢?
他想恨,又恨不起来;想气,又痛到无力,他甚至连张寅青也不愿看,只交代手下去调查,就是今天建宁长公主求他来劝攸君,他亦是百般勉强,不过,他或许应该更清楚的表白自己多年的心和受到伤害的爱。
但当他看到那完全失了颜色又病恹恹的攸君时,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了。
倒是攸君坐直身子,迫不及待的问:“寅青还好吗?你们有没有折磨他,将他屈打成招呢?”
他!
征豪冷讽地说:“他好得很呢!在刑部有吃有喝有住,还和大伙打成一片,根本不必你担忧!”
攸君低下头,轻轻地说:“我只是不愿大清律法滥杀无辜,冤枉好人!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寅青绝对与云南没有瓜葛。他夜闯公主府,都是为了我,若要论罪,我才是祸首,你们要治他,也必须治我!”
这不是征豪要听的话,他的回应只有一句:“为什么?”
攸君直视他,不懂他这没头没尾的问法。
“为什么?为什么有了我之后,又冒出一个张寅青?”他终于说完句子。
攸君明白他要追根究柢了,有些话,其实她早该坦白,只是时机始终不对,现在不得不明言了。
“为什么?世间有太多理不清又探不得的疑问!征豪,自从我回北京后,你们一直把我当成七年前的攸君,十二岁时的天真无邪,仿佛中间的离别不存在。
“但无论你们在期待什么,或者想要视而不见,但衡州那些年的确是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被迫成长、被迫改变,再也不是从前的攸君了!所以,我生命中有其他人出现,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难道你不知道我多重视我们的婚约吗?不管你在哪里,怎么改变,都不该忘记我的爱。”征豪用力握着手说;“那个张寅青哪一点好?竟能取代我们的青梅竹马,甚至让你舍弃你的额娘?”
攸君也被这段情冲击着,她忍住激动说:“征豪,我当时才十二岁呀!哪懂什么情或爱的?即使是订了婚约,在我心中,你仍像我敬爱的哥哥,我待你就如同洵豪和我阿哥一样。
“结果……结果来了抄家的剧变,一切发生得措手不及,我的世界整个天翻地覆,生我、养我的父家和母家反目成仇,即使是个成年人都难以承受,何况是小小年纪,未经人事的我?在那巨变中,连生命都一捏就碎,你还能期望一个婚约吗?”
“没错,我期望!”征豪感觉凄凉地说:“尽管不知你的生死,我仍—意要守到底,只是没想到,一片痴心的竟只有我一个人!”
他在指责她吗?那她这七年无法释怀的苦,又该找谁去索偿?一时之间,攸君压抑许久的惯怒,冲破她向来端静的外表,决堤而出。
“是的!你期望、你守信、你不变、你高贵,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因为七年来,你无波无澜,你没有父亡母离,靖王府没有抄家!你每天过得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信手拈来的是富贵功名!
“一个养尊处优的贝勒爷,哪能想像流离失所和无所依归的苦?你要求我守信,但当我有难在身,朝不保夕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连我的平安都守不住,又怎能要求婚姻呢?”
门外,建宁长公主正好悄悄来探情况,听到这段话,整个人无法动弹。这几个月的重逢里,攸君的口中不曾提到一个恨字,但此刻,那恨意吐露出来,竟像鲜红的血汨汨地流。
屋内的征豪早就被她的话淹没了,攸君竟在怪他?那感觉再也不是凄凉,而是支离破碎,他说:“我……我是要救你,但事情发生得那么快……我那时也才是十五岁的孩子呀……”
“不只是你,根本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以前公主府里高朋满座,多少人攀亲带故,结果一出事,就只剩两具尸体,我还记得那下雨的夜……”
攸君的眼眶中满是泪:“连我额娘,堂堂的大清公主,皇上的姑姑,竟也救不了自己的丈夫、儿子。人家说虎毒不食子,他们连我阿哥都不放过,所以,我压根不信任你、不信任额娘、不信任爱新觉罗的人,你要我怎么把终身托付给你?”
建宁长公主踉跄的往后退,若不是姜嬷嬷,她早跌坐在地了。
“攸君……”征豪极力的想辩白。
“你,没吃过一日的苦头,根本无法体会我遭遇过什么,但寅青懂,因为他也家破人亡过,他了解人世的沧桑与无奈,所以处处护卫我。”攸君知道这些话伤人,但却不无法忍住不说。
“我由北京、衡州到苏州一路地逃,早非不沾人间烟火的格格,我遇过盗匪,成为乞丐,脏兮兮的一身,全都是寅青救我,给我找食物;可以说,没有他,我已不知死了多少遍!而在那些天地不应的时候,你在哪里?额娘又在哪里?”
“攸君,这不公平,你从没给我机会,上天也没给我机会……”征豪涨红着脸说。
“现在不就是吗?”攸君掉着泪说:“你若如你说的,一切真心为我,就该放了寅青,因为他死,也就是我死!”
“不!我不相信你一点旧情都没有!”他沮丧地说。
攸君看着他痛苦的神情,一些话又吞入肚里,好半晌,才轻轻地说:“征豪,何必呢?你是天之骄子,有多少名媛淑女任你挑,何必苦守着已经不存在的梦呢?况且,我嫁了你又如何?我永远去不掉吴三桂孙女的印记,谁知哪一年上头的皇帝又不高兴了,要找个罪办我,不就又连累到你了?
“我回北京是为了额娘,但我怕留在这里,怕噩梦又重现,你和额娘又和我成对立的局面……能不能一次,就一次,你们别站在爱新觉罗耶边,就站在我这边呢?”
倚在石柱上的建宁长公主,很困难地移动身体,脚步缓缓地下了台阶。攸君果然没有原谅她,攸君恨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儿子死去!方才的—段话,把她—生的悔恨全都狠狠地挖掘出来,可她只不过是一个软弱无用的女人而已啊!
在门内的两个人,都没察觉建宁长公主来了又去。征豪沉默着,实在是不知要说什么才好,反正攸君已经把他们的世界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