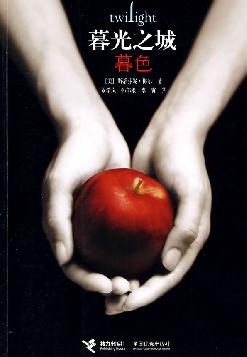罪恶之城-第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周若愚俯下&身体,抓住她柔软的长发,一把将人提起来,周围发出不少抽气声,人群窃窃私语,却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止这场暴行。开玩笑,连警察都对他点头哈腰,谄媚讨好,谁还有胆量在他面前叫嚣?这个世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终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上飞机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漂亮女人爱惹事,你又不是不明白。
“算你走运,子弹并没有穿过心脏,只是失血过多,现在仍在抢救中。”一辆黑色SUV,宁微澜与周若愚都坐在后座,只不过她的双手被反折在身后,锁在一幅货真价实的警用手铐里。
宁微澜眼下总算平静过来,对周若愚的话爱理不理,等到她开口,却发现被周若愚伤了嗓子,嘶哑如同老人,“他仇家那么多,躲得过这一次,下一次就难说了。”
周若愚板着一张脸,阴森森说:“宁小姐,明人不说暗话,能有机会近距离射伤霍先生的,只有你。不过是仗着霍先生喜欢你,便为所欲为,不知所谓!我劝你适可而止,再这么作(zuo)下去,小心人财两空。”这语调,透着浓浓的鄙夷。
宁微澜对他的挖苦嘲讽似乎不以为意,至歪着头,露出轻轻浅浅笑容,这倒让周若愚发了傻,觉得尴尬,却又听见她说:“所以你就在第一时间把我抓回去?言听计从,事必躬亲,啧啧,真是一条好狗——”一句话,足够把周若愚气得不能自控,面色通红,双眼外凸,布满老茧的手就要扇过来,却又硬生生停住,一口气冲到头顶,还得自己咽回去,胸口发闷,实在难受,他一贯得意的自制力,似乎就要毁在这个矫情做作的女人手上。
“呵——”周若愚怒极反笑,冷哼,“等回到霍先生别墅,看你还能高兴到几时。”
然而她不听劝,高昂着下颌,带着满身狼藉与敲不碎的傲骨,“我活着每一刻都是挺直脊梁的人,不像你,为了活着,跪下当狗。”
周若愚却保持沉默,转过头看向窗外快速后退的斑斓霓虹、流光掠影。
又是一场秋雨,淅淅沥沥,冷冷清清,是悲泣的节奏。
她被扔进霍展年居所内所设的地下室,阴冷潮湿,暗无天日,周若愚关门时说:“每天三餐定时有人送,不过我劝你,最好日夜祈祷霍先生度过危险期,不然,你就等着做陪葬品吧。”
时间仿佛又倒回十五年前,她与父亲宁江心,被关在地下室里,任由高涵霍展年一群人昼夜折磨,最后也免不了死亡结局。
生命即是一场又一场轮回,此刻她站在原点,却依旧看不清未来轨迹,也许猎物始终是猎物,弱者始终只能是弱者,不管你如何挣扎,如何努力,如何想要撞破这操蛋的命运。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是她被关押后唯一的陪伴。
大约从第五天开始,女佣送来的只有水,一丁点食物残渣都没有。起初她也曾闹过,反抗过,试图逃跑,却无路可去,尝试求饶,却无人搭理。周若愚像一尊地狱神像,站立在她眼前,毫无感情地说:“我劝你还是省省吧,再叫,再闹,也没有人敢给你一块面包。”
她已经被饿得没有力气反驳,“难道你们真的打算饿死我?”
“你说呢?”周若愚难得地扯了扯嘴角,接下来却转身锁门,隔绝她的渴望与祈求。
“*的周若愚!”骂过粗口,眼泪终于涌出眼眶,随即一发不可收拾,停不了的抽泣与悲鸣,她始终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难道她真会被活活饿死在这里?自杀的方法,死亡的可能,她想过无数遍,却从没有体会过饥饿的滋味,它贯穿你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每一秒都在脑中叫嚣,饿啊,太饿了,饿得恨不得啃掉沙发,咬掉桌脚,斩断手臂生吃!
什么是痛不欲生,什么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短短四五天,她全然体会透彻,她想念着家中温暖昏黄灯光,想念着厨师南北交织的手艺,想念着所有能够用来充饥的东西。
这是粒米未进的第六天,她是刚梦醒,或是仍在梦中,恍恍惚惚,朦朦胧胧,已忘记自己是谁,活着的滋味又是什么。
一众密闭的黑暗中,门开后的微弱光线是她灰暗人生的一道曙光,那脚步声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是来拯救她的神祗,还是解脱她的死神。顾不得了,哪怕只是饥饿产生的幻觉,也要拼最后一次。
她想要站起来,努力许久,最终只是从沙发掉落到地板上,实在是没有力气,浑身上下皮肤与肌肉似乎早已不属于自己。她几乎是匍匐着一寸寸向前爬,像一条狗,一条吃不饱的死狗,尊严、骄傲那是什么,那又算什么?此刻只要谁肯给她一口吃的,叫她跪下舔鞋底都愿意,噢,听说皮鞋也可以果腹,也能让她撑过一时。
一分距离,艰难地抬起手,终于抓住他深灰色裤腿,想发声,讨一口吃的,却咿咿啊啊,说不出正常字句。
“在天台上不是很神气?现在饿成这副样子,给你枪也扣不动扳机,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
她已经抬不起头,去看高处,那张面白如纸的脸孔,居高临下的姿态,掌控一切的语调,仿佛她是一只随时可以被捏死的小虫,存在的意义只是他的喜好。
“求求你…………求求你…………”
霍展年笑着,膝盖点地,蹲下*身子,附在她耳边说:“求我什么?嗯?求我一个重伤未愈的人为你做什么?”
“我错了…………我以后都听话…………我想吃饭……干爹,我想吃饭…………”大颗大颗的眼泪坠落,她已经彻底被击垮,被摧毁,被泯灭,从此再无尊严,无自我地活着,宁微澜不是宁微澜,只是隔岸灯火,霓虹陷落,一抹他人肩上的装饰而已。
霍展年满意地笑,温柔地将她扶起,理了理她散乱的脏污的头发,抚摸着他曾隔空描绘过无数遍的脸,低声说:“饿了这么久,不能吃太多,要先用流食让身体适应,不然胃出血又是大麻烦。好了,你看你——”似感叹,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慈爱宽容,“乖乖听话不好吗?一定要闹成这样,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在他怀中闭上眼,久久地,只剩下呼吸。
作者有话要说:我知道,我是个禽兽。。。。
☆、62孤星
是地狱也是天堂。
金新月湿热躁动的空气中;杀人与被杀不过一线之间;每一天都当做末日放纵,情与欲失去底线,拥有更多、享用更多才是终极奥义。
金钱、权利、女人,男人的所有欲*望在这里;都将得到满足;前提是——你足够强大;足够冷血;不折手段地活下去。
七月,正是蚊虫肆虐的时候。白色的蚊帐已发黄;懒洋洋一层层挂在床边,屋顶一盏老式日光灯;照得简陋房间一片惨淡光景。卫生间里淅淅沥沥流水声断断续续响,他光着上半身,古铜色皮肤包裹着一块块饱胀肌肉,却遮不住皮下粗壮的脉络,低头翻书的瞬间,留给从洗手间里探出身体的玲,一个诱惑至极的背影。
“吱呀——”老旧腐化的门发出一声缠绵呻*吟,一只脚迈过湿哒哒地垫径直才在冰冷粗糙的木质地板上,浅红色指甲油接近斑驳,麦色小腿结实紧致,墨色图腾蜿蜒妖娆,是针尖刺破皮肤留下的永久不灭的痕迹。“阿炎——”她伸手,从背后环住他肩膀,丰满柔软的胸便如此紧紧贴着他,勾引着,撩拨着,是玲的专属方式,咬着他的耳朵,不断向前,用他宽阔坚实的后背碾压者亟待蹂躏的乳*房,“又读书?读书最没有意思。这次去了那么久,阿炎都不想玲吗?想念玲的身体,玲的□,还有玲的……嗯……这里……”她早已习惯这种事,抓住他的手便往□的下半身送。
在这里,生存法则最粗暴也最直接,只有最强的男人才配拥有最漂亮的女人。玲曾经是孟邦大人的宠物,自从阿炎出现,她便被当做礼物或者说监视者送给他——年轻,蓬勃,充满力量与神秘感的男人。
就连伏案温书的动作都性*感得要命——她张嘴,不轻不重地啃咬着他的肩胛、脖颈,进而是耳垂,一双细长的手向下,抚摸他那位怒涨的小兄弟。“怎么?出任务受了伤,女人都上不了了?”
他腰上缠着绷带,三天前子弹穿过皮肉,人肉烧焦的香味,如今还记得。
一笔画错,他终于扔开原子笔,一把扛起全身赤*裸的玲,重重扔在小床上,屋顶那只日光灯也在晃动,忽而明灭,照出他的脸,英气勃勃的五官,一道狰狞的疤痕穿过眉骨,险险错过眼角,窜进乌黑浓密的短发里。
“你太吵。”他拉开拉裂,放出凶兽。
“我就爱闹你。”她敞开腿,发出邀约。
一沉腰,猛地闯进去,玲舒服得尖叫,细长的腿更盘紧了他的腰,蛇一般勾人。
可怜身下小床也是个不中用的老家伙,他每每往前一寸,小床就跟着玲一齐呻&吟,哼哼唧唧,像是有旁观者,三人行,越发刺激。
事毕,玲瘫在床上没力气动弹,而他还却还能下床去冲洗,冲掉一身黏腻,又能清清爽爽出来,继续坐在枣红色破书桌边翻他的书。九月就要交毕业论文,等飞回伦敦戴上眼镜,他仍有职责未完成。
玲说:“阿炎,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在这里,居然还能像好好学生,杀完人又回来读人人平等?阿炎你为什么不能和孟中、Tan他们一样呢?”
阿炎破天荒地从那堆英文字母中抬头,瞟她一眼,说:“我和他们一样。”
玲急着反驳,“不一样的,阿炎你好像随时准备离开这里,离开玲。”
“首领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首领叫我读书,我就去读书。”
“是吗?”她仍存疑惑,而他却已经不愿再多说了。阿炎似乎永远都是这样,沉默的,凶猛的,不同寻常的一头猛兽。
五年的蛰伏,一千八百天的等待,那些早已寂灭的星火又透出微光,那些远在来生的渴望再一次被点燃,不可抑制的是血脉冲顶的期待与兴奋,即使粉身碎骨,即使一败涂地。
戬龙城的盛世华章,无可比拟的盛大喜宴,最炙手可热的钻石单身男霍展年,与新晋影后白素素,经过五年爱情长跑,终于手牵手走进婚姻殿堂,台下多少小女生尖叫,男才女貌,天作之合,哇咧哇咧,终于又再相信爱情。
仔仔细细不偏不倚系好他喉结下方黑色领结,细白的指尖划过他肩膀,再为他理一理不小心卷了边的西装领,宁微澜适才抬头,笑意盈盈地同他说:“祝干爹干妈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哦?真心话?”霍展年微微向前倾着身体,一只手捏住她下颌,将一只迷离口唇呈送眼前,“这话我听了,实在高兴不起来。”
对于霍展年时时刻刻施加的压迫感,她早已习惯,这么多年相处,他的脉络神经,喜怒哀乐,她都铭记在心,不敢不仔细。而此刻,他需要的显然不是诚惶诚恐的道歉,而是进退有度地任性,于是仰起脸坏笑,干干净净的眼睛里,偏有一股娇媚,让人心痒难耐,“那就祝你们日日吵架,同床不同心,好不好?”
霍展年摩挲着她的唇,喃喃道:“这张嘴,说什么都好。”语毕,便狠狠吻住这双令人神魂颠倒的红唇,含着它,啃咬着它,吮吸着它,直到彼此的呼吸节奏都被打乱,才推推搡搡纠缠着往床边靠,才系好的领结又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