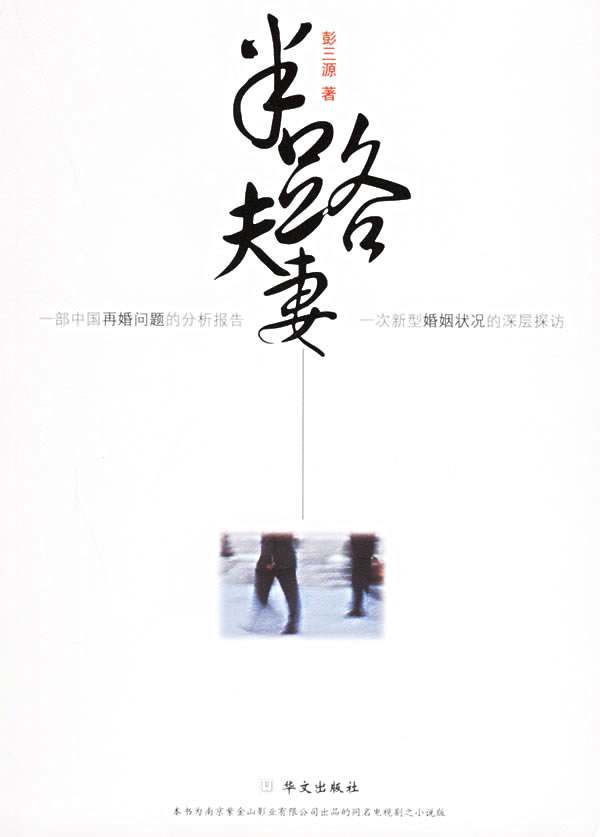挂名夫妻-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很……生气?”她问得迟疑。
庞霄望着她的美眸,绮君给他看得羞涩的低头。
“是很生气。”他回答。
绮君难过得不知该说什么,但随即庞霄又接口。“不过……我更担心你的安危,昨天的事是我不好。”
她惊异地抬头对上他黑暗中晶亮的眼眸,他说他担心她,是真的吗?
“以后我不会再限制你的行动。”他继续说着。
“你的意思是……”
“如果想出门,老陈会载你出去的。你说得对,这是一场政治婚姻,我们都是这桩婚姻的牺牲者,我没有理由约束你,何况……你并不是心甘情愿嫁给我的,不是吗?”
不是……不是的!绮君心中凉了半截,她并没有不甘心情愿,也许一开始是,但其实她是喜欢有他在身边的,可是她说不出口,想说的话全卡在喉咙里发不出声来。
“如果你想跟你喜欢的男人在一起,我不会反对,若想离婚也行,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吧。”
她听得傻住了,庞霄刚才的一席话表达得很明白,他并不在乎她,甚至还鼓励她去找别的男人,离婚也无所谓,为什么她感到严重的失落和悲伤呢!
看着面无表情的绮君,庞霄仅存的一线希望全没了,绮君对他说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在乎他的提议,他好傻,还以为自己在她心中至少仍占有一些分量,看来他这次是真的清醒了。
“早点回房休息,外套你就先披着吧。”
忍住想抱她的冲动,庞霄快步走回屋子,再不离开他不知道下一秒自己会对她做出什么事来。
豆大的泪垂落在她无瑕如玉的面颊上,她捂住唇怕哭出声,震惊于自己失控的情绪,这是什么心情?为何她觉得心好痛?
※※※
文骏不知绮君发生了何事,两个礼拜没有她的消息,好几次在庞家附近徘徊等待机会见她,却一直没看到绮君出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从庞娟那儿套消息了。
在大学校园树林中的一角,庞娟拿着画板坐在石头上专心画着素描,专注的神情融入在四周洒泻的阳光中,构成另一幅美景。
在不远处的高文骏,坐在草坪上脚着树叶欣赏这幅美景许久,瞧她全神贯注的样子,神情端庄、气质秀丽,不同于以往的泼辣刁蛮,看不出她也有这么迷人的一面,让他舍不得打扰她而在树丛后静静的欣赏。
不过,别人可不像他这么不杀风景,一名漂亮的男子走过来,打断了庞娟作画的情绪。
“庞同学,真巧在这儿碰到你,咦?你在画画呀!”
什么真巧!文骏不屑地瞧着闯入者,企管系四年级的杨文生,每学期名次都拿第一,颇有女人缘,女朋友一大堆,长相还不错,但是太过于脂粉气了,尤其自命风流的个性是他最讨厌的那一型,相信庞娟也不会喜欢。
刚才就看到他在庞娟周围打转徘徊,故意想好了台词才走过来假装遇到,会有人柏油路不走而走草丛的吗?以泡女孩子的技巧来说简直太差劲了,根不无技术可言。
“是啊,真巧遇到你。”庞娟应付着,她故意选了隐密的地方作画就是不想被人打扰,怎么会被他发现呢?
“画得真好,你常这样在校园里画画?”
“这是下礼拜美术社参展要用的。”
“喔?那我真是幸运,在参展而能够先睹为快。”
“没有啦!只是随便画画充数而已。”
“什么!随便画画就能画这么好,真令人佩服,根本就是未来画家的料啊!”
高文骏冷眼瞪他,这家伙是白痴吗?讲话这么夸张,听了令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搞不懂这家伙为何会有女人缘,讲话就讲话,身体还不安分地靠过去,真想扁他!
“没那么夸张啦!我纯粹是喜欢画画而已。”他怎么还不走啊!庞娟挪动身子与他保持距离。
“你也教我画画吧。”杨文生越靠越近。
“我?不行啦!”对他有意无意的靠近感觉不太舒服。
“别这样,我是诚心的。”
庞娟已退坐到死角,杨文生却越来越大胆,索性握住她的手。
“你——”
庞娟已忍到极限正要开骂,此时却传来冷冷的一句。“我来教你。”
杨文生与庞娟同时吓得跳起来,什么时候有第三人他们完全没发觉到。
“你是谁?”杨文生瞪着高文骏。
“我也是美术社的一员,告诉你!要学画得先交一千元入社费,然后要个别向已入qi书+奇书…齐书社的前辈打招呼兼奉茶、捶背,此外还要经过千锤百炼大考验,通过之后才承认是正式社员。”
“什么是千锤百炼大考验?”
高文骏邪笑冷冷的说:“就是一入社之后,新社员每天要擦拭所有画具、负责打扫画室、帮大家采购各式用品,有必要时还要脱光衣服当大家的模特儿。”
“胡说八道,我才不信!”杨文生嗤之以鼻地不屑。
“是不是胡说,问问你旁边这位社长就知道了。”
杨文生转过头看着庞娟,庞娟立即很配合煞有其事地加油添醋。“不只是当裸体模特儿,在初学阶段还要跟着前辈们到处去学习,特别是有些学长们尤其喜欢男见习生,不知是什么原因。”
“也许他们有同性恋倾向。”高文骏补上一句。
“不知道!不过每次跟着他们见习的男生最后都吓得退社就是了。”庞娟严肃地说。
“哈哈……是吗?那我再考虑看看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拜!”杨文生脸色难看地告别。
待他走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捧腹大笑,乱没气质地笑作一堆。
过后,庞娟斜眼瞪他,收起笑容问:“你怎么也会在这里?”
“散心呀!”
“少跟我打哈啦,我才不信有人会往草丛堆里散心。”
“喓喓!别一副过河拆桥的脸嘛!别忘了刚才幸好有我帮你打发掉那个杨文生,他可是有名的花心萝卜。”
“谁要你帮了?”她坐下来继续作画。
高文骏也跟着坐下,只手托腮静静地看她。
庞娟才懒得理他,跟他辩口舌只会气死自己,索性将他当隐形人,反正没人跟他讲话自然就会走开。
但是,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庞娟再也忍不下去,双颊泛红地大骂。“看什么看!你到底想怎样!”
“你好美。”高文骏突然冒出这一句。
“什、什么呀……”她心跳狂猛不休。
“你专心画画的神情好美,怎么我以前都没注意到?”他一本正经地赞美,甚至还努力思考这个问题。
真、真、真不知道该生气还高兴!庞娟被他搞得满脸羞红却又下知从何骂起,突然想到那张他抱住嫂子的照片,脸色一转站起身气愤而去。
“喂!等一等!”他拉住她的手。
“干什么,放手呀!”
“先告诉我为什么突然生气?我只是赞美你,又没惹你。”
“你和那杨文生一样都是花心男人!”
高文骏被她搞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何突然被冠上花心的罪名。
“我哪儿花心了?别血口喷人!”他也气愤不平地问。
“反正那是你的事,我也管不着,你快放手啦!”她挣扎着。
高文骏反而抓得更紧,这女人就不能温柔点吗?才夸她一下马上又恢复原形,而且还突然给他加上这莫须有的罪名,搞得他心情大乱。
“你今天不说个明白,我绝不放手!”语气非常强硬。
挣不开他铁一般的手腕,庞娟气得开始大骂,高文骏可受不了女人歇斯底里的叫骂声,要她住嘴最快的方式就是——封住她的唇。
也不知哪来的冲动,他的唇覆上她的,一股柔软湿嫩的感觉酥麻全身,庞娟腿软了,像被施了魔法般身子软酥酥往下掉。
味道真好。高文骏忘我地浅尝樱唇柔软的滋味,搂抱怀中软绵绵的身躯躺在草丛堆内,周围高耸的树丛成了最好的遮蔽。
许久,庞娟推开他,想骂他的话语却变成了哽咽的哭泣。
高文骏不知所措地安慰她,惊觉自己刚才的行为实在像个侵犯的色狼。
“你好坏!明明有喜欢的人还这样对我。”她伤心地捶打他。
他摸不着头绪地急问:“谁说我有喜欢的人?”
“别骗我了!坏人、坏人……”泪水不听使唤地涌出,哭得楚楚可怜教人看了心疼。
高文骏不得不承认女人的眼泪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所谓梨花带泪,真是形容得好啊!不过,现在不是欣赏的时候,他得搞清楚为何庞娟说他已经有喜欢的女人。
“别哭嘛!我又没说不负责。”
“谁要你负责呀!我可不要成为你众多女朋友之一!”她甩开他的手。
“等等!我先声明,我高文骏不是花花公子,也没有一大堆女朋友,请注意你的言词。”他严肃地指正。
“睁眼说瞎话!我可是亲眼看过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而且还是有夫之妇!”
“你再乱说我可真的生气了!”高文骏被她激得脸色铁青。
“我没乱说,因为那个有夫之妇就是我嫂子——王绮君。”
高文骏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张得大开,这是哪门子的误传,突然他觉得事有蹊跷,这或许跟绮君一直未出现有很大的关系。
“跟我走。”他抓起她的手。
“我干么听你的!”她不依地挣扎。
他用着耸动磁性的声音配上俊酷的表情,加上咄咄逼人的目光,散发出无法抗拒的魅力将她环在双臂之中,蛊惑中含着不容人抗拒的气息包围她,轻柔地命令。
“我说过我会负责的,既然你的唇已用我所亲触,那么以后也不会有别的男人有权碰触你的唇,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我们的约会从现在开始,你若不跟我走,又怎么让彼此有机会互相了解呢,是不?”
她呆呆地点头,似迷惑又似不解,在脑筋会意之前,高文骏可不让她有时间清醒过来,半哄骗半强硬地掳她而去。
第九章
清晨醒来,床的另一半是凉的。
绮君呆坐在床上好一段时间了,人与人之间实在很难相处,她不懂庞霄的心,也不明白自己的心境,若要简单地形容自己目前的心情,或许只能用“失意”两个字最为贴切吧。
从前不管发生什么事,与她有关或无关的,她一向是将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看淡一切是她的个性,平静的心起不了一丝涟漪,如今却在夜深人静时,庞霄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占据她整个思绪。
其实庞家上下的人现在都对她恨好,仆人们甚至常常会送些小礼物给她讨她开心,年轻一点的女仆总是爱围绕着她抢着讲话,她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这么受欢迎,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比以前健谈许多,也变得爱笑了。
这样的生活可说是无忧无虑,不愁吃穿有如人间仙境一般与世无争,但是为何她仍不快乐呢?
她想,她一定是生病了!怎么办?她不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郁郁寡欢,她该找谁倾吐?脑子里突然冒出钟少薇的影子,上一次钟少薇送她回家时,顺道给了她地址和电话,要她有空就去找钟少薇。
于是,绮君带了地址决定去找她,或许钟少薇可以给她答案。
※※※
庞霄神情肃穆地审查几份公文,虽然年纪轻轻身居中央政府主管要职,但他却己十分倦怠,每天有应付不完的交际应酬和关说,尽管他有满腔的热诚和学识想要一展长才,但政治其实就是利益输送的同义词,许多在位者只做对自己名誉及地位有利的事,其他吃力不讨好的事则一概不管。
也许是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从政一途原本就非他志愿,只因爷爷和父亲对他的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