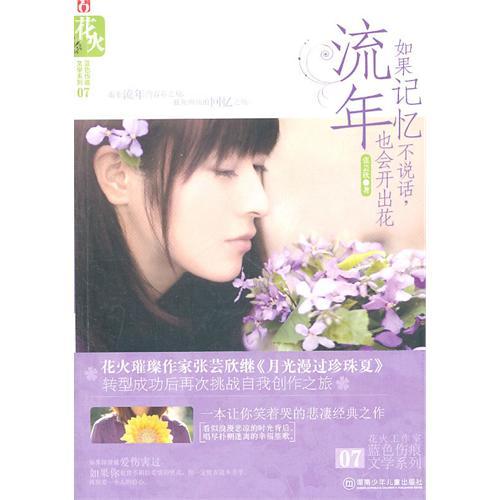莞尔流年-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吧。” 安宸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张磁卡来,冲着黑色的大铁门一刷,那么门就自个儿打开了。姜莞尔这才发现,两幢房子都被黑色的栅栏围了个严实,葱绿的树隔绝了外头新起的屋宇,有点世外桃源的意思。
她几乎是蹑手蹑脚走近了自己旧时的家,走近了自己儿时所有星点甜蜜的回忆。她走过那条蹒跚着步伐奔跑过的青石径,踏上那阶曽铺过龙凤呈祥地毯的石阶,手在触感冰凉的门把上停了停,轻叹一口气,终于轻轻转动,推门而入。
一层的光线很暗,曾经的麻布床帘被换成了开合的百叶,把阳光尽数挡在了外头。姜莞尔的眼神在客厅南头的墙壁处停了片刻,搁置过皮质沙 发的角落已然空空如也
若干年前,她和母亲坐在那张没有温度的沙发上,相拥而泣。那时的她,见到了母亲的脆弱,亦见到了自己的绝决。那时的她,做出了一个痛彻心扉的决定,从此人生截然不同。
女人踏上盘旋的楼梯,每一声鞋底敲击地板的声音,都击打着心底莫名涌起的的情愫。右手边第一间,是她的房间。
奇屋子的采光很好,无论冬天夏天,总可以享受暖洋洋的照射。浮沉在阳光里头无处遁形,她环视空荡荡的屋子,唯有旧到不成样的地板,还是她离开时的那套。
书通往窗台的门居然是开着的,姜莞尔正自纳闷,目光突然又被墙根处一片小片字迹吸引。女人蹲下身子仔细端详,指间拂过的瞬间,嘴角已然翘了起来。
潦草的笔迹赫然写着:XX年9月18日,今天是安宸哥哥走的日子。哼,等着瞧,我要一年不和你说话。
下面是煞有介事的倒计,365、364、363……一丝不苟的数着,却只到353便停了。
曾经她每晚都要钻下写字台来,把对抛下她跑去法国的他的怨气,都狠狠的刻在数字里。
可是某一天,当安宸第四次给她家拨来国际长途的时候。母亲掐腰站在门口,一边用手挥舞着话筒,一边示威似的抿着笑问她:
“你到底接是不接?”
问到第三遍,她已然倒戈。蒙着脑袋的枕头往身侧一丢,女生翻身下床便抢过了话筒。
“莞尔,姜莞尔?”回忆中,她听到安宸在唤她,一时竟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姜莞尔愣了愣,突然明白,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了阳台。
正对面,是安宸家二楼的阳台。
曾经安宸与她一样,也是住在面南的房间里,享受一年四季和煦的日光。可没住多久,男生便搬到了北向阴冷的客房。
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做,不过为了能离她近一点。
两户的阳台,探出去,围栏与围栏之间仅仅一步之遥。有时他会踩在上头,纵身一跃,便跳进了姜莞尔的屋子。莞尔同母亲冷战,赌气不下楼吃饭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个法子,给她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吃食。
小时候她只觉得好玩,甚至会拍着手小声称赞:“安宸哥哥好帅。”
可渐渐大了,她开始胆战心惊,甚至捂住眼,不敢看男生爬上栏杆。心心念念间,怕他会有一分一毫的闪失。
于是安宸不再上演动作戏码,有什么东西,直接轻手轻脚扔进她怀里。
而有什么话,她偏偏也不肯同他直接说。写在白纸上,折成飞机,神秘兮兮的一只一只丢给他。他从不笑她幼稚,她掷过来的每一句话,他都仔细的收在抽屉里,原封不动。
折飞机的法子,还是安宸手把手教给她。再轻再薄的纸叠出来,也能飞出去好几米去。
此刻的安宸,正垂着头,全神贯注的折叠一只铜版广告纸。每一个步骤,每一处纹路,都是她所熟悉。
“安宸?”姜莞尔小心翼翼的唤了一句。
对面的男人完成了手工,抬起头来,温暖的笑容如昨。
简简单单的,他应了一句:“恩。”男人话音刚落,右手已然举起在脸侧,轻轻一送。纸飞机在半空中划出虹般的弧线,左摇右晃,飘飘荡荡。
是她的错觉吗?为什么当飞机跃入阳光的刹那,闪烁出璀璨的光,耀的她无法正视。
姜莞尔条件反射的伸出双手,牢牢的把小东西包在手里。
下一秒,安宸已经随着飞机朝她“落”了下来。女人短促的“啊”了一声,向后退出一步,他稳了身子,伸出手去抓住她小臂,才叫莞尔不至于失去平衡坐在地上。
记忆里最后一次他的纵身一跃,已然是十六七年前。那时她从指缝里,自男生渗出细汗的脑门,看到微微弯起的笑眼,然后撅起嘴巴说:
“喂……以后别这样了,我害怕。”
而此时的她,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沉吟了半晌,女人突然“噗”的一声笑了出来,声音越笑越大,越笑越无所顾忌。捂着肚子,她缓缓的蹲下了,肩膀却还因大笑而颤抖个不停。
一分钟以后,安宸拍拍她的头发,试探着问:“笑完没?”
头埋在膝盖里,姜莞尔点点头。然而立起身子的瞬间,嘴角仍旧狠狠的抿着。
“那么好笑吗?”他偏了脑袋,故意做出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女人摇摇头,又点点头,进而望进他眼里低声回道:
“我只是……很开心。谢谢你。”
“要谢我,待会儿也不迟。”他笑,神色竟略有些紧张,“莞尔,我有话要同你说。”
“恩?”姜莞尔仰起脑袋,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却看到安宸的视线落在她手里的纸飞机上。她当下会意,举起飞机来有些好奇又有些不解,轻轻撑开机翼,指甲盖大的银色东西便滑了下来。
姜莞尔伸手去接,冰凉的触感正落进掌心里,展开来一看,笑容霎时间都凝固在了脸上。
是一枚戒指。镶的钻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微微泛着蓝色。配着那细长流畅的银环,将将恰到好处。
原来那刹那耀眼的光,并不是她的错觉。
“莞尔。”恍惚中,她听到安宸叫她,熟悉的声音在那一刻竟有些不真实。
姜莞尔茫然的抬起头。
“莞尔,嫁给我吧。”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每个音节每次律动,都是从心底里做出的承诺,“我一定会让你幸福。让你每天都像刚才那样,可以肆无忌惮,无忧无虑的笑。没有烦恼,只是开心。”
她无言以对。
向她求婚的这个人,也许是剩在这世界上,陪她最久,最懂她,也是最爱她的一个人。他从来不曾提高了嗓门与她说话,不曾忤逆过她任何任性的要求。他甚至从未对她说出过一个“不”字,从未朝她哪怕是皱一皱眉头。
在法国的日子里,她像一只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的茧。疼也不知道,恨也不知道,没有喜悲,没有情绪波动。他就不发一辞陪在她身边,从不问过往,从不触及伤了她心的旧事。
她偶尔开口,他便去做;她不开口,他就陪着她一起沉默。他的存在,似乎是不在。但每当她疲惫不堪的回过头,他就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带着温暖的微笑,为她留着他馨香的拥抱。
是,安宸就是这样。不催促,不索求,不质问,不迟疑。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处坎坷,他就站在她身后,搀扶着她走过。
只一步之遥,他便可以与她肩并着肩,手携着手。但他却从不曾试图逾越,那一小片戳手可及的方寸之地。
他在等她对他打开心结。他总是很有耐心。
应该说,对她,他总是无所不能。
当安宸将车开进姜莞尔的小区时,夜幕已然拉了下来。熄了火,男人打开车内的灯,向后靠在座位上。
两个人都没有动。
“还打算搬家吗?”他突然问,转过头,看着她线条柔和的侧脸。她却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老半天才回了句:
“不知道,还没找着合适的房子。”
他点点头,收回视线来。仰面看看天色,又没头没脑的说:“白天明明晴的那么好,怎么说下雪就下雪了。”
正说着,车前的玻璃上,已然稀稀拉拉的沾上了几滴雪水。雪下的不大,一片就只有丁点。她出神的望着那漫天漂浮而下的白,咬咬牙,终于还是说:
“安宸……”
“莞尔。”他突然插话,手覆上她的左手,正盖在她套着戒指的指头根,“不是说好了?咱们就像小时候,这戒指,你戴三天。三天以后你再告诉我,还要不要把它摘下来,还给我。”
她无法拒绝。
很小的时候,她拉着安宸陪她玩结婚游戏。他拿可乐罐的拉环给她做戒指,戴在手上,她固执的三天不摘。有时甚至会故意显摆出来,给这个妈妈看,给那个妈妈看。
没再说话,姜莞尔轻轻点点头,合起右手从他掌心下抽出,开门下车。安宸没有送她,而是打开车前灯,为她照亮了黑惘惘的路。她回头看他一眼,算是无声的感谢,对上他专注望过来的眼神,又慌忙转过了头。
走到楼跟前时,隐约觉得门洞右侧的阴影里停着一辆车,太黑了,姜莞尔看不清楚。一直上到了二层,耳畔传来安宸驱车而去的引擎声,她才恍然了悟什么一般,步子也停了下来。
是她想得太多了么?若就这么返回去,却发现不是,那她心里头的狼狈,该交给谁来收拾?
……也罢,难道她为他狼狈的还少?多一次少一次,谁知道谁不知道,她早该不在乎了。
这么想着,女人早已转身下楼。一直到看清楚了那熟悉的银色,说不上为什么,竟长长舒了一口气。就好像在人多的地方与同伴走散了,寻来觅去,发现他就在灯火通明的地方,微笑着等她。
仲流年双手交叠在方向盘上,撑着额头。身子微微前倾着,整张脸都埋起来,让她看不清楚表情。
她就一言不发的望着他,隔着车玻璃,仍然可以感觉到男人身上深入骨髓的疲惫。雪渐下的大了,贴在脸上,一瞬便化成了水。一时间她有种错觉,那是她的眼泪,一颗凉过一颗,一直凉进心底。
可姜莞尔很清楚,那些液体,不是从她身体里涌出来的东西。眼眶干干,她比谁都感觉的真切。
她伸手,用一只指头敲了敲车窗。
仲流年动了动,缓缓抬起头来。额前的发有些凌乱,一如他此时的眼神。他的嘴型,仿佛是拼出了她的名字,她听不真切,不自觉的向前探了探身子。
男人按下了车玻璃,却没有要下车的意思。望着她的眼神从迷离变成清醒,从清醒变成犀利,又从犀利变成了深切沉底的悲。
“你怎么来了?”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她只得下意识的问出了心口的问题,声音有多喑哑,他们都无心顾及。
他怎么来了?她病的日子,他每天早早结束了工作,把车停在对街,望向她不常打开的窗子。不给她电话,不上去找她,就只是坐在车里,静静的守着。
他在守候什么,是在期待她偶尔向外看看,把视线投的远一点,就可以看见不请自来他?
仲流年自己也不晓得。
他只是知道,说过要放手,百般努力了,却放不开。若是能放,六年前他便放了,但蹉蹉跎跎两千四百多个日夜,他从没能把她自从心里面抹去过。
他的自尊,早被她扯烂了揉碎了丢在脑后。偏偏剩那么一点,固执不化。
于是他尝试着拼凑失去的自己,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却还是回到原地。才发现没了她,再怎么努力,他也回不到完整的样子。始终是少了一块,始终是无法抛开过往笑笑了事。
他说他不爱她,是假的;说他不恨她,却是真的。
谁说爱到了极致,受了伤,便会因爱生恨?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