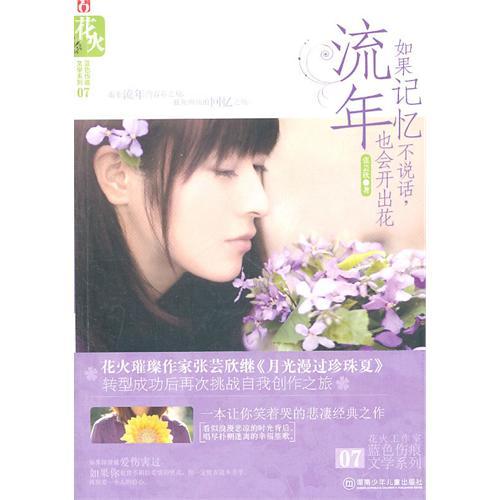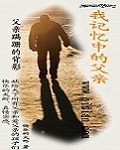记忆与现实交错-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窗外是一面墙,隐约能看见一个白色的背影在晃动,仔细听,又辨出有些失音准的旋律。
小星星,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绿袖子,后面的听不出来了。
乐器的声音轻柔,像笛子,又更飘一些。不熟练还会漏音,蹦跳的旋律过后,很长很长的停顿。白色的身影从墙的一边逛到另一边,低声喃喃的哼唱着旋律。
太远也太黑,眼前还不太适应黑暗,孔谦一时看不清,随着歌声往走廊方向又挪动了几步。
远处渐渐驶近的车声,一道强光射过来打在白色影子上。扬手的瞬间,孔谦眼前晃过一道银光。
投在地上的影子斜长,光圈里站着一个女孩,手里握着一支长笛。车灯打在她脸上。这次看得再清楚不过。眉眼还是几年前,但也长大了些,似乎长高了,还来不及辨清她的表情,突然见她转头往门口的方向跑,好像见了什么不喜欢的东西。
没多想,把杯子放在窗台上,孔谦随着消失的背影往客厅走。正听见砰的一声,门开了。
大家的谈话不约而同停下来,注意到门口的人。亦诗显然没想到厅里这么多生人,跑了几步感觉不对,赶快停住,楼梯在中堂后一时过不去,立马折返身子,冲着孔谦的方向奔过去。
匆匆自身边掠过,纤细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客厅的角落,孔谦来不及看清亦诗的面孔。走廊里传来愈加快的脚步声,一时恍然,再回身看厅里,门口站着一对母子。
母亲把小男孩放在地上,牵着他的小手缓步向客厅中央走,笑着和厅里的客人打招呼。三年没见,脸上添了些岁月,孔谦还是一眼就认出是亦诗的继母。
她手边的小男孩从没见过,只是她看他的眼神多了呵护细心,孩子摇摇晃晃每迈出一步,她脸上就多一丝笑意。深情的模样,让他不禁想到几年前在山脚下抱亦诗的一幕。太讽刺的反差,那时候她没当过母亲,少了细心爱护,任她细瘦的胳膊垂在冷风里浑然不知。
这个男孩,肯定是她自己的孩子。抱着孩子坐到沙发上,一手慈爱的抚着孩子头顶黑黑的短发,不时亲吻一下,谈话间回身叫来阿姨嘱咐给孩子准备糖水,温婉动人的语气,引来几个女客人笑。
和乐的一幕看过反而觉得刺眼,孔谦没有上前,只是一言不发的转身,快步随着亦诗跑走的方向赶过去。
走廊很长,没有灯,离大厅越远越暗,只能勉强靠视力辨别廊子里的路。白色的背影早消失无踪,孔谦不熟悉亦家的布局,沿着走廊在黑暗里前行。
不像华丽的大厅,也比不得小楼里其他修缮过的房间,布置简单,经过的几扇门都紧闭着,越往里越像是回到了几年前,判断方向大概已经绕到了楼的另一边。终于到了尽头,在刻意搁出的小厅前停住,目光寻到某扇门缝里泄出的光。
想放慢脚步,不确定她是不是在里面,会不会在哭。迈步走得很急,在门外犹豫该不该马上进去。
三年前她独自在藤萝架下和娃娃说话,失去母亲的伤痛就挂在脸上,如今大一些了,逃开之后会怎样呢?
手放在门把上,思忖着刚要推开,门里传出轻柔的音乐声。有些意外,是一段长笛演奏。比刚刚听到她在楼外吹奏得娴熟优美很多,但每过一个地方会规律的降一个音,应该是张唱盘。
沉一口呼吸轻轻推门,光线在眼前一点点铺开,眼前是一间陈旧的小房间。像个书房,又摆了几件乐器,空间不大,对墙却是整面的窗。没有合拢的窗帘透出朦胧的月光,照到窗前的钢琴上。琴盖开着,好像刚有人演奏完,谱架上的琴谱翻到某页上,用个小夹子别住。琴键上躺着一束小花,只看到娇小的花蕊,已经枯干了的颜色,孤零零的衬在黑白键盘之间,多了份落寞。
顾不得深究,就着壁灯注视着她的背影。果然在这里,藏在走廊尽头的房间,没被开门声惊扰,只是蜷着腿趴坐在几步之遥的软塌旁边,好像陶醉在音乐里。
她身前的旧唱机不停转,音乐随着滑转流过耳边,旋律很美,又很哀伤。长笛就随手立在塌边,碎长的流苏一直垂到地毯上,绞在笛身上。旁边的地毯上躺着一张老式唱片封套。封面上绘着一片紫色的鸢尾花田。
音乐惆怅,弥散在月光下,一时心神恍惚,眼前似乎不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这是谁的琴房?环顾房间,钢琴上摆的像框像框泄露了什么。里面是亦诗,只有两三岁的样子,揪得高高的小辫子,白色带滚边的小裙子,抱着一本厚厚的书坐在地毯上,膝上躺着漂亮的娃娃,似乎正看得开心。
孔谦踱过去两步,不敢太近,怕扰了她。照片里的笑容,他从没见过,从第一次见她开始,从不知道她也可以笑得那么开心。
手里正翻着一本薄旧的五线谱,朦胧的光线照到谱上娟秀的音符,投下的身影盖住了一行行小字。
一颗小水珠落在页角,濡湿了一小片纸页,她马上用指尖遮住,又翻到下一页。新的水珠掉下来,在暗黄的纸页上晕开。这次亦诗没有擦,只是专注盯着母亲留在线谱上的字。
心里拧痛,不忍看她这么难过,孔谦俯下身,本想说些什么,却不由先伸出手,盖在了那片字迹上……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得他看得到她瞳仁里自己的倒影,那谭幽黑慢慢要将人溺毙,甚至忘了她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泪珠落下,孔谦感觉手背上碾过滚烫,粉碎了不伤心的希冀。她哭了,孩子似的伤心哽咽,不像几年前只是默默落泪,独自和娃娃说话。
亦诗就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发帘下含泪的眼睛,睫毛每闪动一次,更多泪水不受控从眼角滑落,努努嘴仰头望着孔谦,不管是不是认得清,感觉他并不陌生,就只想哭,埋在心里的悲伤尽数沉在眼底。
阿姨生了弟弟之后她只会躲着,以为把自己藏起来就不难过了,可其实反而更难过。她记不得什么时候拉过妈妈的手,也记不起妈妈讲过的故事,她只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娃娃,妈妈留下的那些乐谱,可它们都不会说话,不会给她说故事,然后,她才发现了乐谱上的字。
在被废弃锁着的房间里找到第一本有字的乐谱,看到妈妈在书角画的小花,和唱片封面上一样的紫色小花,她记得妈妈喜欢这个颜色,有件很美很美的紫色衣裙。之后,碰到有手迹的书或乐谱就一本本收集起来。难过了就来落灰的房间听音乐,抱一本妈妈的乐谱,努力认上面的字,试着记起妈妈的样子。
可太多字她不认识,不知道妈妈在上面说了什么。描绘着一笔一划,感觉好像妈妈在写在画,自己就坐在她身边,可以听见她说话,看见她的样子。妈妈的怀抱是什么感觉她已记不清,连妈妈的样子都淡忘了,找不到她的照片,只好在房里努力在脑海中勾勒妈妈,依偎在音乐里。
谱子上的大手固执的挡住了她和妈妈唯一的交流,她用手去拨,碰到伸张有力的手指,又缩回去。孔谦不肯挪开半分,不想再让她看,心乱得不知怎么安慰下去。
他的手比她大太多,她奈何不了,迟疑一会儿又把两只小手盖在他手背上,求助的望进他眼里。她在求他,眼神的交流,霎那像一根刺扎在孔谦胸口。在海地目睹过很多生离死别,破碎的家庭,和家珍离婚形同陌路再无交集,这些都没有此刻疼得厉害。
小手反复抚摸他的手背,很轻,很小心,流落的泪水纷乱的滴在谱子上,把谱子润皱了。他压得太用力,把心里的憋闷传到手上,甚至暴出了筋脉,对视间无声的要求已经有些敌不过。她不张嘴说,也不敢,就是眨掉泪水,幽幽怨怨的望着他。小手从手背摸到手腕上,喃喃的想说话,又胆怯了,转而轻轻摇他,抓住袖口一点点布料不肯放手。
亦诗想要的不多,不是阿姨给她买的无数新衣服,不是爸爸为她重新翻修的大房间,她只想开口叫妈妈,可以像弟弟那样扑在阿姨怀里,大声地叫妈妈。她已经好久好久没叫过了。
头发帘被推开,温暖的指腹拂过额头,她微微瑟缩了下,对他不恐惧反而很亲切,透过泪水回想着眼前熟悉的面容。藤萝架下他讲过小王子的故事,她一直铭记在心里,因为妈妈和小王子一样,有了独自居住的美丽星球。
孔谦低下身,看她不怕才伸出手,小心翼翼抚在她头上。陌生的局促不安很快被心疼代替,缓慢的动作渐渐流畅,透过昏暗的灯光,顺着她长长的黑头发,试着读出她眼睛里的伤痛。
谱子悄悄从手里抽走,阖上放到身后的地毯上,她还只是孩子,没有母亲的孩子,现实已经太残忍了,不想她再徒劳的追忆什么。
“诗诗,还记得孔叔叔吗?”想说些什么分散注意,她却更紧的抓着他的袖子一个劲摇头,回身找谱子,一看不到,立时心慌意乱的松开手,抹着眼泪要爬起来。
“诗诗,还记得小王子吗?”赶紧换了话题,扭过去的小身子一滞,又转过来。认真地点了点头,忍不住掉眼泪。妈妈也在小王子的星球不回来了,她以后再也没有妈妈,不能叫妈妈,看不到她。越想越害怕,整个世界成了巨大的漩涡,黑暗没有尽头。
“诗诗,小王子的星球……”笨拙的想继续故事,刚讲了一句,就见亦诗眼里带着恐惧,踉跄了一大步,一下扑进他怀里,小手死死扣在他脖子上,不顾一切的放声大哭。
“妈妈不要一一了……妈妈和小王子住……妈妈不要一一了……妈妈……”
真切的感受怀里无依无靠的幼小身体,嘴边的话变成苦涩的弧线,刺痛到无法压抑,一瞬间孔谦的眼眶也湿润了。
她一定是怕极了积压了太久,死死搂着埋在他身上,抖动着单薄的肩,哭得肝肠寸断。快十岁,也是有心的年纪了,比别的孩子经历的又多,过得并不开心。
孔谦不忍,即使别人的家事不便插手,她又是最敏感的小孩,还是一手揽到亦诗背后,把个小人抱进怀里。
小小的雏鸟羽翼稚嫩,需要躲在成鸟翅下遮风挡雨,可她没有得到足够照料。生在富足殷实家庭,她一点不像几个孩子圆润,更比不得客厅里的小男孩。她很瘦,抱在怀里更觉得弱得无力,肩膀突出的小骨架,依在他身上还瑟瑟发抖。
“一一”
把唱机的声音旋大,伴着音乐缓缓的叫她的名字,这次,是她妈妈叫她时用的昵称,声音柔软小心,带着些无奈,他实在不会哄孩子,只能当她是个小婴儿。
音乐很美,长笛吹奏的旋律,窗外天幕上月朗星稀,扶着塌起身,带着她一起站在钢琴旁。他不懂音乐,指划过键盘,落下了轻轻的一个音。
怀里的呜咽很重,抽抽泣泣的又往他脸边蹭,泪水漫在衬衫上,肩头都湿了,也有一些沾到他脸颊上。想了很久,不知道给她说什么,小王子的故事已经失效,只会让她更形难过。
在海地时,战乱的不幸历历在目,人会慢慢变得麻木,第一次眼眶还发热,之后渐渐习惯,没有眼泪,除了无力感只剩痛心。可她给他的感觉又不一样,不是简单地别人的孩子,好像总带着奇妙的联系,能牵动他脆弱的神经。
又敲了一个键盘,在琴凳上坐下来,就着光看清了那束小花。干枯了失去本来的颜色,又依稀带着鲜活时淡淡的紫色。记忆在她脑海里也是这样吗?褪成黑白,剩下一片模糊的委屈。
“一一,”拿起琴上的相框,沾到些灰尘,举到近前,看清她笑时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