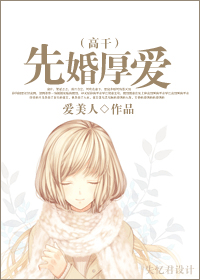东来莫忘(高干)-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耳边起哄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蒋东林朝那帮狼笑笑,也不再看被撂在一边的那个叫茜茜的女孩,就自斟自饮,又干了两杯,才说到:“哥们儿今晚尽兴,我请。”
那帮人还没有走的意思,蒋东林又喝了一圈,准备起身先离开。李明辉一把就将茜茜推进蒋东林怀里,嬉笑着说到:“东哥,我们知道你最近的调调,特意找这么个口味的来,你可得负责带走啊,哈哈。”
叫茜茜的女孩没有说话,温顺地就贴上蒋东林,蒋东林看了看她,又笑着对一众人说:“呵,你们这帮狼,走了。”说完,也没拒绝也没拉她,就自顾走了出去。
女孩转头看了看专心开车的蒋东林,上了妆的脸庞还是浮现出一丝羞涩的笑,这个男人很好看,很不一样,女孩不住扭头看他,他却并没有什么反应。
“你住哪?”蒋东林淡淡开口。
“嗯……?”女孩听他突然这么问到,有点不可思议,“不是……去宾馆么?”
“我送你回去。以后少混夜场。”蒋东林淡淡答到,方向盘一转,就掉了个头。
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满满都是烟头,和漂亮的绣珠桌旗有点不太搭调,蕾丝遥控器盒子下的那片薄纸,被风吹得翘起了一角,蒋东林摁掉手里燃了一般的烟,走去窗边又将窗户开大了一些。仲春的午夜,风儿也没有了初春时候的料峭,吹进客厅的时候,蒋东林不自觉挥手帮着散了散空气中的烟雾,丫头不喜欢香烟的味道。计算着日子,很快就要到她的生日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丫头还被关押在里面,生日那天没有人陪着,想必又哭鼻子了吧,那时候应该肚子里有宝宝了,只是她和自己这个当爸爸的都不知道。自己那天是怎么过的?好像还是在到处找人托关系。今年的这个时候,桃花依旧笑春风,只是人已远走。她去了哪?她现在可好?一路颠沛辛不辛苦?是不是,已经有其他人陪伴身边,一起过今年的生日了?蒋东林坐在沙发上,盯着眼前一角飞舞的纸片想得有些出神。
“砰砰砰,砰砰砰”,这个时候响起的急促的敲门声,让蒋东林倒是有些意外。从杨沫出走到现在快一年,蒋东林只要在北京,几乎天天住在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儿,甚至自己的母亲,也常抱怨说怎么东边公寓里的电话总是没人接。
母亲开始的时候还老是问起杨沫的情况,见蒋东林总是闷哼着打着哈哈过去,再加上这半年多也没再见到那丫头,慢慢也就不问了。父亲已经准备回京任职,有次蒋东林去南方看他们,父亲倒是破天荒来了句:“那丫头玩够了回来,找个合适的时机我和你妈妈去他们家拜会一下她父母,该有的礼数还是不能少的,那丫头吃了那么多苦……不然我早当爷爷了,其他事情,你自己摆平。”蒋东林讶异于父亲从未有过的直接,嘴上应承着,心里却更加不是滋味。
蒋东林起身没看猫眼,就开了门,门外是满脸是泪得汤小元和一脸讶异的王译。
“怎么了?……”蒋东林看汤小元一脸着急忙慌,惊讶地问到。
“东哥,你真在这啊,打你手机一直关机……”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杨沫……出什么事了?”蒋东林看她这样,心里不禁一阵紧张。
汤小元看电脑开着,抽抽搭搭也没理他,走过去就一阵“噼里啪啦”,扭头对蒋东林说:“你自己看吧。”
蒋东林走过去看,却是电子邮件的页面。
“小元,我到青海了,这几天会启程去玉树县结古寺看看,一切安好,放心,勿念。”
寥寥几个字,时间是4月10日。蒋东林的心被猛地一擂,差点就觉得找不到呼吸。退了出来点进收件箱里,10号之后却再没有杨沫的来信,再往上看去,从去年6月开始,断断续续的邮件一封又一封,看着发信人“杨沫”两字,蒋东林止不住揪起了心,再顾不得看前面的信,忙扭头看汤小元。
“杨沫到现在都联系不上……呜……手机打不通,根本联系不上,……叔叔阿姨急得要死,已经往青海去了……呜呜……他们俩前天就从西宁包了车往灾区走了,但那儿现在一路都军事封锁了,根本进不了,没办法了……你快想想办法,去找找她……”汤小元从进门开始哭,现在更已经泣不成声,哭喘着对蒋东林断断续续说到。
仿佛是一把业已出弦的利箭,“嗖”地一下直往自己胸口射来,来不及躲藏,来不及避让,心口已然被钉死,钉死在一架叫做“绝望”的十字架上,蒋东林心口被这把利箭射了个穿,刺了个透,脑子仿佛供养不足一般“嗡”得一下就一片混乱。
“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蒋东林觉得连吼人的力气也没有了,手忙脚乱间却全然找不到车钥匙放在了哪。
“呜呜……她一直不让说……一路也没出什么事……呜呜……你快想想办法,把沫沫找出来,想想办法……呜……”汤小元早已乱了阵脚,只是一味说着。
“去香山爷爷那,走,王译,你跟我一起去。”
47
47、第 47 章 。。。
在爷爷那联系好部队的关系在青海接应,一切都还顺利。民航航班早已没了,蒋东林觉得无论如何等不到明天,更何况明天能不能走还是问题。杨沫是生是死现在分分秒秒都牵扯着他的心、他的命。如果可以,用身家性命换张可以立马飞到青海的机票他也愿意,又怎能这么毫无目的等待煎熬,又是一通联络疏通,竟然就找了辆军用运输机,立马从南苑出发飞青海。
从北京到青海高原路途遥远,从东到西地势节节攀升,再加上军用运输机机舱条件简陋,一路气流颠簸并不安稳。蒋东林却好似全然没有觉察周遭不时的颠簸晃动,盯着手里的一摞纸,看得有些出神。
出发前蒋东林不忘从汤小元的邮箱里把近一年来杨沫所有的来信都打印了出来,封封件件,竟然能订成厚厚的一摞。从内蒙开始,丫头走过了呼伦贝尔的草原,大兴安岭的森林,蒋东林感觉自己跟着她的悲喜而悲喜,跟着她的心情而跌宕;之后一路往西到了西藏,日喀则的寺庙、那曲的寒夜,蒋东林心疼她独自在清冷艰苦的雪域高原的一路跋涉艰辛;再往后看,原来丫头独自落跑之后又去了云南,香格里拉神秘的碧塔海、泸沽纯美的摩梭女儿国、腾冲还不太为外人所知的侨乡和温泉、怒江沿途的雄浑壮景,蒋东林看她时而心境开阔,时而又陷入无故低落的漩涡,心情也起起伏伏,酸涩苦辣,说不清、辩不明。之后杨沫还走了陕、甘、宁,几乎西部跑了个遍,山山水水、大漠荒沙、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挑灯垂泪。蒋东林一页页看过去,几个小时的航行,仿佛跟随着杨沫一个又一个深深浅浅的脚印,看她看过的风景,听她听过的山歌,体会她暴走岁月中点点滴滴的心情,抚摸她心弦一次又一次被打乱时滚滚而落的泪。每次看到信里的那个“他”,蒋东林都感觉自己的心被狠狠地拉扯了一下,有点不敢看下去,怕这个“他”不再出现,但又急不可耐地想继续往下看,因为忍不住想知道这分别的300多个日日夜夜,她是怎么度过的,她的心里,可还依旧有他!
蒋东林赶到西宁的时候,机场灯火通明,丝毫没有高原暗夜本有的宁静。民航早已全线临时管制,跑道和航道提供抢险部队和专门航班用以运输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协调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急需物资。民航航班大量延误或取消,机场被滞留的旅客为数不少,能降下的航班寥寥无几,更别说顺利起飞的。如织人流来来往往,忙而不乱。
停机坪上早已等候着前来接蒋东林的军区的车,林政委是蒋爷爷的老部下,看到蒋东林走出机舱,就迎了上去。一路上,林政委都在跟蒋东林描述现在玉树的灾后情况,派出去专门找杨沫的人已经赶到了那,蒋东林听着地震灾后的情况,揪着的心更觉生疼起来。电话,一直在拨,杨沫那边,永远关机。
再见到杨沫父母的时候,二老比上次见到时苍老了许多,杨沫父亲两鬓仿佛一夜染白,倒比上次见到好似老了10岁,杨沫妈妈还是止不住地抹眼泪,蒋东林看在眼里,心下更不是滋味。安慰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却还是忍着心里万分的焦急与苦痛,抚慰他们在西宁等消息,自己去玉树寻找杨沫。杨沫父亲仍旧冷眼相待,母亲一边抹泪一边恳求,无论如何也要一同前往,活要见人,死,也要亲自把女儿的尸骨找回来。
西宁往玉树县走,还没到一半的路途,就已经军事管制了,来往车辆一律禁行。军区的车挂上特殊通行证,越往里走,蒋东林和杨沫父母的心就越往下沉。四月本是芳菲天,但高原的春意却并不盎然,灰蒙蒙的天连着灰蒙蒙的地,没有几丝绿意。再往里走,县城外围的地方已经陆陆续续搭起了应灾帐篷,或悲痛、或麻木的人们散座期间,县城里却是触目之处皆惊心,震碎铺面而来,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路,找不到一座完整的屋,找人的,救人的,穿梭混乱的人群夹杂着时不时散出的震天的哭喊声,血迹处处可见,遍地废墟中,弥漫着灰尘和石灰消毒粉混合的味道。
蒋东林再也按捺不住,第一个下车就往帐篷点跑去,一座座、一间间,多数都是藏民的脸,每个人都在哭泣,每个人都絮絮叨叨诉说着什么,但哪里有杨沫的影子?越往后找,杨沫妈妈的哭声越大起来,她在活的人里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她不信杨沫会躺在那堆再不会说话的人中间。
站在临时停尸场前,杨沫妈妈一下就瘫软了下来,泣不成声间竟然拉不住蒋东林的衣角。杨沫爸爸也有些站不住,开始止不住老泪纵横,蒋东林一把接住杨沫妈妈瘫下去的身子,死命搂了搂她,说:“阿姨,我去。你们等着。”
临时停尸场设在靠山的一片空地上,藏族人很多信奉天葬或水葬,来这祭奠烧纸的倒不多,只有寥寥几个家属,在躺着的尸身边嚎啕哭泣。死灰一般的土色和光秃秃的山堆,衬得这里更加死寂,天空开始下起蒙蒙细雨,冰冰凉凉地吹过蒋东林的脸颊。
镜片已经模糊了,蒋东林有点看不清前路。这是从没有经历过的场面,生与死,就在眼前,只有一线之隔,触手可及。蒋东林心里一百分、一千分、一万分的害怕,害怕那几百具尸身中就有自己朝思暮想,到最后爱到深处不可自拔的那个。短短的一段甬道,走起来却仿若漫无止境的修罗路,步步锥心,周遭仿佛百鬼夜行,狰面獠牙直要吞了他的一颗心。脚下却停不住,往前走,一步、一步、再一步。
蹲下去,揭开积满雨水的塑料裹尸布,蒋东林真正体会了心提到了嗓子眼,虽血液仿佛凝固,却也挺着直视了过去。
不是,不是杨沫。
一具,一具,再一具。不是,不是杨沫。
杨沫妈妈的哭声此时听起来遥远又飘渺,却还是悠悠地传入蒋东林的耳朵,一声一声,混合着冰冷的雨水,敲打着他的心。雨渐渐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