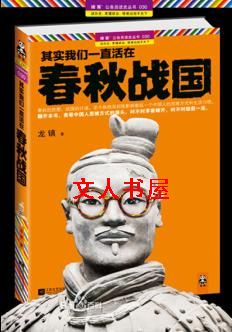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81.3%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
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欲望,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20世纪60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19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
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
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
()好看的txt电子书
到了医院,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瞄过去,没找到玲姐,我有点失望,同时松了口气。
我在玲姐曾经住过的一间病房门口多停了一会儿,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看见玲姐曾经躺过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老太太,一个干瘦的老爷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给老太太喂着饭。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了我认识的那个女医生的声音,女医生说:“咦,你来做什么?”她本来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懒得整个转过来,只把上半身转过来望着我。我说我来看看表姐。她慢悠悠地说:已经出院了,本来应该再观察几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几次出去很晚才回来,一身灰呀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糟践自己的病人呢。”
女医生还没说完,我就联想到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看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势很像玲姐。我脑袋里立刻有沙尘暴一样的东西呼啸起来了。女医生后来好像提到过美国甜橙,问我在哪买的。我没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就往楼梯口走过去,女医生跟着我走了几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层楼了,才听见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谢我什么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还没谢谢你呢。”
出了医院,天光变得有些浑黄,好像又要刮沙尘暴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憋闷难受,恨不得大声叫喊起来。我觉得我真是太混了!我决定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车驶进玲姐家所在的小区,我忽然又觉得这么干很不合适,就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我打算去能看见玲姐家阳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后坐公交车回去。
太阳又钻出了云层。玲姐家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见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亲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阳光中轻轻摆动。我心中一阵酸痛,想要转身离开,却像是给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样,又站了一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东西时,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场,还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别的事。我站在阳台下的这天,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洗我的衣服,也没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让我产生了等待玲姐到阳台上来收衣服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既然站了这么久,不如干脆再等一等吧。我继续在一棵树后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阳台。有个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视了我一会,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给吓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赶紧走开了。
天越来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灯光照亮的雨滴划过一道道稀疏的斜线,那些斜线很快密集起来,让人分不出是斜线还是直线了。冰凉的雨水浇在我头上。有一瞬间我又跌入了某部电视剧中的某一幕:一个没带雨具的年轻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处的窗口。
见玲姐没有出现,家里也没亮灯,我忍不住拨通了她家里的座机。听到玲姐轻轻地喂了一声,我赶紧挂断了。没几分钟,灯亮了,玲姐走到了阳台上。她站在阳台一侧,朝楼下望了望,然后慢慢挪到阳台另一侧,又朝楼下望了望。
她收起衣服走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阳台上来了。我看见她拿起了手机,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我赶紧关掉了手机。她俯身朝阳台下黑暗与光斑交错的树丛里四处张望着,问:“天儿,是你吗?”
玲姐的那一声呼唤和询问,像亲密的魔法咒语,让我情不自禁地嗯了一声。我迷迷糊糊地从一棵槐树后面走了出来,走到被灯光照着的地方。大雨如注,脚旁垃圾横流。我仰起脸望着玲姐,雨水无遮无拦地落在我脸上,我不时抹一抹湿淋淋的脸,继续望着她。
玲姐朝我喊:“天儿,你快上来!快上来!”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时间忽然停止了。一颗颗雨滴和几朵槐花悬停在空中。几秒钟后,雨滴和槐花又纷纷落下了,像灵魂的碎片。意识一点一点回到了脑子里。一切都有些朦胧变形,我能看见几座阳台上出现了人影。我用玲姐能听懂的那种单音节哑语喊了一句:“我不要你管!”掉头就跑。附近传来了嘻笑声,有人说:“原来是个哑巴疯子!”我心里跳动了一下,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他躲闪了一下,像是要躲开朝他飞去的什么东西。我跑出了小区院子,跑过了巷子,跑到了大街上,坐公交车回到了住的地方。一路上觉得脑袋又重又痛。
我一连发了三天烧。有好几次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我都以为是玲姐来了。我梦见玲姐抱着我,轻轻揉我的额头。我梦见玲姐在厨房里给我熬药,屋子里飘荡着草药的气味。我梦见玲姐在挤一只|乳头上的小疖子,她抱怨说,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看得见。我安慰她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继续挤,|乳头突然像玩具水枪似的往外喷射着奶水,其中一些射到了我脸上,我很生气,让她不要再挤了,可她勾着头,继续挤啊挤的,仿佛沉浸在一种不可抗拒的乐趣里。我对她说,本来已经好了的,不停地挤,就永远也好不了啦。她像个婴儿一样笑了,望着我。我说,好吧,我来帮你挤。我趴在她的胸脯上挤压着,骨节缝里充满了泡沫……醒来雨声一片。
第四天,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发现许可佳站在面前。
许可佳说:“哎呀,原来是生病了!这几天正琢磨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跟我妈一说,她让我一定来看看你。”
我告诉许可佳,我头疼,怕吵,就拨掉了电话线,关掉了手机。
许可佳说:“这样可不好,这样不是自绝于人民嘛。”
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立刻在心里涌起来了。那股滋味,像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细品一下,也许对许可佳的感激还是要稍稍多一些。几天后,我问许可佳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许可佳歪着头笑了笑,说这是一个小秘密。过了一会儿,又说是去派出所查到的,问我信不信。我当然不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把我的住址告诉她的人是玲姐。
许可佳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摸着我的额头,然后要我跟她去她妈妈所在的医院。我不肯去。许可佳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把我的症状描述了一遍。两个小时后,她妈妈带着输液瓶来了。两天后,我感觉基本上好了。许可佳请假照顾了我两天。我要她去上班,她坚决不去,还说我要是不让她呆在屋子里,她就去楼梯上坐着。我只好答应她晚上睡沙发。 早晨醒来,却发现她蜷在我怀里。
我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把头埋在她胸前,哭得还挺伤心的。
许可佳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像在拍怀中的一个大玩具娃娃一样。拍着拍着,她笑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醒过来,就哭成这个样子?”
我这才感觉到了羞愧。我想找个什么地方钻进去,往被子里钻了钻,觉得不对劲,爬起来去把脸洗干净了。然后我坐在沙发上,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许可佳。
许可佳弯着腰,垂着头发,正在理床单,叠被子。一会儿,大约她发现我在打量她,抬手捋了捋头发。又过了一会儿,她勾着头从腋下望着我,噘着嘴做了个鬼脸。我努力笑了笑。
见我基本上能照顾自己了,许可佳才去上班。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胡思乱想的,觉得我也许应该做比较现实的选择。许可佳各方面都很不错,在常人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