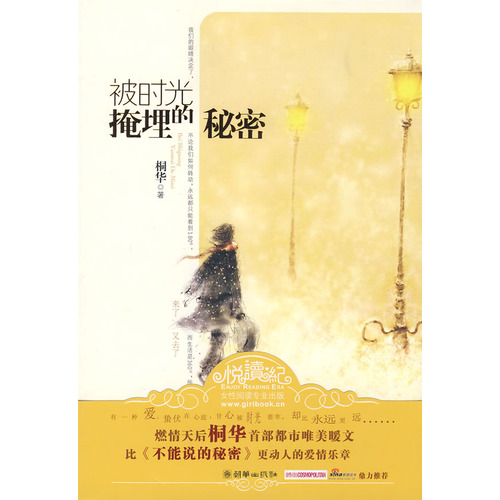b小调旧时光-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张彻说:“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想法的呢?”
黑哥说:“不知道。总有几年了吧。”
张彻说:“连什么时候开始想自杀都不知道,你这自杀也太糊里糊涂了吧?”
黑哥说:“就是嘛!我也觉得糊里糊涂,而且一直都没想好,究竟怎么自杀呢?比如说我屋里只有这三样东西好用:安眠药、刀片和麻绳。究竟用哪种好呢?我选来选去,也拿不定主意。你给帮忙出出主意。”
张彻说:“这三样东西,你琢磨多久了?”
黑哥说:“怎么也有五六天了吧。”
张彻说:“看来你并不急着死?”
黑哥说:“倒是也不太着急,又不是赶火车嘛。不过自杀还是得自杀的。”
张彻说:“既然不着急,咱们还是再琢磨琢磨吧。”
黑哥说:“可不是!自杀可是人生大事,一辈子就一回,不像结婚什么的,一次不行还有第二次。所以自杀可得一定选好方式,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张彻说:“那既然不着急,你帮我个忙行么?”
黑哥说:“干什么?”
张彻说:“你会弹吉它?”
黑哥说:“那自然。”他把张彻让到屋里,屋里一片霉菌肆虐的味道,桌上摆着一把吉它、一瓶安眠药、一个剃须刀片和一根麻绳。看来他刚才正在一边弹吉它,一边看着三样道具,反复考虑应该用哪一件。
6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6)
张彻说:“您空有一身好手艺,就这么死了岂不可惜?我倒不是不同意您自杀,我是想,您如果死之前把手艺传给我,岂不也算对后人有点儿贡献?”
黑哥说:“无所谓,教你就教你。不过有两条——”
张彻说:“金属还是朋克?”
黑哥说:“我都不想活的人了,还会在乎那套虚头巴脑的吗?我是说,第一,如果我想好了怎么死,立刻就得去死,你别拦着我。”
张彻说:“绝不拦,我还帮着你。”
黑哥说:“不用不用,那就是他杀了,不算自杀。我对自杀要求很严格的,必须保证品质,毕竟是那么重要的事,一辈子只有一回嘛——”
张彻说:“那第二件呢?”
黑哥说:“在决定死法之前,我没钱吃饭了。我已经排除了饿死这种死法——”
()好看的txt电子书
张彻说:“这个没问题,我虽然也没钱,可我有一哥们儿,我哥们儿虽然也没钱,可他有个有钱的姘头——”
黑哥立刻拎起吉它,把安眠药、刀片和麻绳等杂物放进破烂帆布包:“咱们走人。”
就这样,张彻和黑哥回到地下室,和我们见面。见面以后,黑哥劈头盖脸便问我:“安眠药、刀片还是麻绳?”
我只好说:“都不合适都不合适。”
黑哥说:“那你说什么合适?”
我说:“人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我自己的看法是,总得死得轰轰烈烈点吧?我觉得抱着一颗核弹头,飞到某个大城市,轰地一声化成齑粉,如此死法最壮烈不过,可谓死得其所。”
黑哥说:“我到哪儿去找核弹头?找到了人家也不发射。这种死法的前提是打起核大战。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我已经看出黑哥眼神木讷,表情僵硬,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士,便也不再逗他。黑哥却认真地唠唠叨叨:“而且你说的这种机会,千载难逢,很可能我都已经自然死亡了,还是没赶上。这不就自杀失败了么?什么事情都要在理想性和可行性之间取得恰当的结合,此法实在不足取。我还是回到既有的思路上来:到底是安眠药、刀片还是麻绳?我排除了近两百个选择,只剩下这三个,但又难以取舍。”
他转向动物般的女孩:“你说呢,哪个好?”
动物般的女孩说:“你哪个都用不着。”
黑哥说:“什么意思?你怀疑我不敢死?”
动物般的女孩说:“不是,我知道你确实想死。不过用不着就是用不着。”
黑哥不得其解,动物般的女孩也不再说,兀自点上了一颗烟。我又拿出老论调:“想不明白的问题就先搁着吧,这是希腊先哲教给我们的。”
黑哥说:“反正早晚得自杀,搁着就搁着好了。”
动物般的女孩说:“反正早晚难逃一死。”
暂时摆脱了这个死结般的问题,黑哥拿起吉它弹了起来。那确实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的技艺实在精湛。虽然不会弹吉它,但我可以确定,在我所听过的吉它手里,没有一个比他弹得好。通常所谓高手,对待吉他可以像庖丁对待一条鱼一样,但黑哥不存在“对待吉他”的问题,吉他变成了他手的一部分。通常高手和他的差距就像我和鲁宾斯坦在弹钢琴上的差距一样。那是不可能以人力飞跃的鸿沟。
我瞠目结舌,张彻大概听不出来,动物般的女孩无动于衷。我认为,黑哥完成了技艺上“人力”与“神力”的跨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活腻歪了。万念俱灰之下,天人合一。
而我还认为,人之所以会选择一死,大概是看到理想世界在未来的道路上永远消失了。内心变成灰烬,手上却因此弹奏出天籁般的声响,音乐与生活不可兼得。黑哥的幸运与不幸都在于此。即使张彻崇拜的约翰…列侬没有死于意外,他也终有一天会选择自戕,因为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已经被现实彻底否定了。
约翰…列侬的幸运与不幸也在于,他还没来得及走到那一步,就在1969年被发疯的歌迷用手枪击中了胸膛。
7神秘人(1)
心如死灰的黑哥在地下室教张彻练琴。黑哥作为一个老师的好处,在于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希望”或“失望”一类的感情,因此即使张彻弹得一团狗屁,他也不会烦躁。
“再练练,再练练。”做过示范后,他只会说这一句。其他时间,他继续看着安眠药、刀片和麻绳发呆。而这三者用在自杀上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也许正因为没有本质区别可言,黑哥才会长久踌躇不定。
在此期间,我们再次迫切需要一般等价物。
卑贱是卑贱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贱与高尚之间的界线,聪明人也搞不清楚,不过傻子都知道一般等价物是这个世界上的通行证,如果没有它,剩下的只有墓志铭。
长久以来,我一直隐隐感到,眼下的生存环境并不是久留之地。我无法也无心融入其中,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远走高飞。至于离开这里去哪儿,却模糊不清:希望是到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钢琴。
认为自己不属于当下,却不知从何处而来,一心想要逃离现状却不知该向何处去,就像一个捡来的孩子,我与外部世界之间隔着一堵无形之墙。
动物般的女孩大概是我的同路人,她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一切都充满诡异,暧昧不清,却能以空洞的眼神穿透我的心扉,使我感到两滴水融合在一起般的同质性。
我盘算着,假如与她一同远走高飞,需要多少一般等价物作为保障呢?那大概不是一个小数目。具体多少我也无法估算,但蝼蚁一般的白领一年的工资肯定不够。
归根结底,还是一般等价物的问题。无论你的想法有多多,无论你的感觉有多微妙,无论你的处境有多荒诞,那些复杂的东西全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一个:有或没有一般等价物。
花光了一般等价物,又无法为社会提供无差别人类劳动,脑子里想的一切都是扯淡。这段时间,不要提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横亘欧亚大陆的火车旅行和靠着厚砖墙静看莫斯科的雪景了,我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三千块钱像自来水一样从手缝间淌走,我、张彻和黑哥本就一贫如洗,动物般的女孩当初出手大方,但和我在一起后,我发现她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没有来历、没有住处、没有名字也没有钱的姑娘,是如何生长发育到这般年纪,无论如何也是个谜。虽然她可以变戏法般地搞到厚厚一叠纸币。
“也许你实际上是一女大款,要不就是某大款的女儿或姘头,逃出封建家庭,追求理想爱情——这么猜想是不是太老套了啊?”我叼着“都宝”香烟的烟头恋恋不舍地嘬着,对她说。
她也拿着半支“都宝”香烟,不置可否,一心一意地抽着烟,仿佛在进行一项高技术作业。
“或者你干脆是个仙女,就像黄梅戏里的那种,私自下凡,留恋人间繁华乐不知返,连累我跟着一块儿遭天谴——也特别老套吧?”我笑道。
她吐出一口烟:“你那么想探我的底?”
“没那个意思,说着玩儿嘛。”
“你要是想不明白,就照你说的那样理解算了,反正你怎么理解我也无所谓。”
“实在没辙的话,也只能这样,”我说,“否则你让我怎么理解你的来历?”我忽然想到奥黛丽…赫本演的《罗马假日》。那电影的情节实在是假得不能再假,不过赫本近乎不真实的美与之相得益彰。每当看到赫本的黑白海报,我都会蓦然想起小时在动物园看到的鹿的形象。但眼前的女孩并不像鹿,而像一切动物。
“咱们又没钱了,”她轻轻把烟头扔进可乐罐子说,“再去弄点儿吧。”
“你瞧,还想隐瞒自己的资产阶级出身?”我说,“说得那么轻松。不过按照传统剧情,我是不是也应该表现自己是一个有志青年啊,否则你怎么会爱上我——不,我不能用你的钱,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我要劳动!”
“别逗了行不行?今天晚上跟我出门。”
7神秘人(2)
我不再开玩笑,换成正经八百的语气说:“其实我好好找找,也能找到弹琴的地方,你依靠我一回行么?”
“不是谁依靠谁的问题,而是谁弄钱更方便的问题。”她说。
我放松语气:“既然你那么仗义,我只能被你说服了。”
晚上,空气湿润,仿佛酝酿着小雨,我和她穿好衣服走到楼下。黑哥在地下室里铿铿锵锵地弹琴,我把两包方便面放到张彻的自行车筐里。
“你听得出来,黑哥的技巧是不是不同一般?”她问我。
“简直不是凡人弹的,那是一双魔手。大概只有活腻歪的人才能达到这种水平。”我说。
“也有这种情况。”不知她指的是“魔手”还是“活腻歪了因此技巧高超”。
我们并肩而行,向初次相遇的酒吧街走去。她把手深深插进兜里,我搂住她的肩膀,感到她头发飘动轻拂着我的脖颈。猛然之间,我紧紧搂住她,几乎把她挤进胸膛,但两人都没说话,调整好脚步后继续走路。
到了酒吧街,她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数着灯火辉煌的门脸。两家欧洲乡村风格,一家模仿巴黎塞纳河畔,两家典型的纽约酒吧中国翻版,两家音乐主题,但一律粗暴地用高音喇叭播放着电声音乐。动物般的女孩一家一家地点过去,又从尾到头点回来,最后在一家挂有巨大的“喜力”啤酒广告的门脸前停下,放下手说:“就这家吧。”
“这儿的买卖全是你们家开的?”
“要是我们家开的,我直接进去要钱就是。”
“你不就是直接进去要钱么?”
“才不是。”她说着走过马路,擦着一对怎么看怎么像偷情的男女的肩进去。我紧跑两步跟上,拉着她的胳膊:
“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弄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