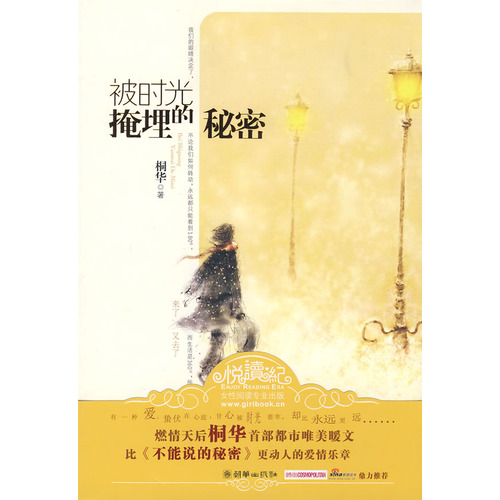b小调旧时光-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彻终于添置了几件衣服:条绒裤子、棉布衬衫、有帽套头衫。他也开始听音乐。“没钱的时候,爱好不起这个。”他买了大摞的盗版摇滚乐CD,其中以甲壳虫、老鹰乐队、皇后乐队、收音机头和地下丝绒最多。听过一遍之后,他摒弃了其他,只听甲壳虫。地下室里终日响彻约翰…列侬的声音,“其他乐队有一句潜台词:现在的生活就是现在的生活。惟独已经和‘现在’脱离关系的甲壳虫,让人走进从没经历过的往日时光。”他哼哼着《黄|色潜水艇》和《昨日之爱》对我解释。
“从没经历过的往日时光”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概念,一言以蔽之:生不逢时。这和我热爱东欧作曲家不谋而合。我这才知道,我们为何能成为莫逆之交。
吃饱之余,我和他一起在地下室里听甲壳虫。我们的身边再次堆满瓶装啤酒,香烟也换成了走私的“万宝路”牌。窝在行将报废的筒子楼下面,心照不宣地对瓶喝啤酒,想着外面的一切窃笑,这就是当代寄生虫的快乐生涯。受了那么多罪,可算让我们赶上了。
张彻也曾问我钱是哪儿来的,我实言相告并坦白了不安的感觉。他吼道:“不要不就白不要了吗?”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是他染上的惟一一个资产阶级毛病。
一连两天,我都在等待动物般女孩的造访。
独自坐在楼上的窗前时,我不禁向斑驳的水泥路尽头眺望。动物般的女孩从未出现,除了张彻,也没人敲响我的房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头四个音被称为“命运的叩门声”,我此刻的心境仿佛是坐在即将上演这部交响曲的舞台下,百无聊赖地翻阅着节目单。
我重新弹起柴可夫斯基为N…鲁宾斯坦而写的三重奏,想像着一双动物般的女性眼睛正在冷漠地盯着我。初次与她见面的背景音乐竟然是一支挽歌。此刻房间内的灰尘味儿变得格外明显,这种味道暗示着岁月的流逝。
有些人一经见过,便再也不会出现。就像站在铁路旁边看着缓缓开过的客车,忽然发现车窗里的某一张脸似曾相识,但还没细想,列车早已呼啸而过,一切终成浮光掠影。直到某次午夜梦回中再次见到那张面孔,才会感到元神脱壳般的失落。
时光不能逆转,河水不能向西流淌,列车的车轮不能倒行,人生的遗憾大抵如此。从这个角度说来,刻舟求剑者也许是最勇敢的人,守株待兔者也许是最聪明的人。
我独自下楼,在一层楼梯口听到地下室轰鸣着甲壳虫的《嗨,裘德》。如此迷恋一样东西,必然是在酝酿着什么后果。张彻、我,任何人都是一样。
()好看的txt电子书
我沿着水泥路走向师范大学。路边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不少车座被雨淋得锈迹斑斑。小区里几乎空无一人,《嗨,裘德》的音乐声一直传出很远,走到了师范大学门口,似乎也未消失。大学生们进进出出,迎着阳光或逆着阳光地传达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我到学校门口的一家小卖部买了几包“骆驼”牌香烟,看看时间已经接近中午,又向食堂走去,想买一份烧茄子、一份排骨和两个馒头作为我们的中午饭。学生们每到此时都饥肠辘辘,吃完饭又会心满意足,生活异常充实。女生们端着浅黄|色、浅蓝色、印有卡通人物的塑料饭盒,由于几年如一日的程序而显得很文静。我远远地看到了尹红,她一言不发,和一个女生低着头,默默地走着,脸上和肩头树影斑驳。怎么想也想不出她如何会一链子锁将我的脑袋开了瓢。她有一双圆圆的单眼皮眼睛,一副地包天的下嘴唇,面相清秀,无论怎么看都是人类。
5维纳斯的Ru房(2)
我在食堂买了饭,在橱窗里随便看了几眼社团活动的海报和寻物启事。素食协会将在今晚召开辩论会,讨论吃鸡蛋是否有罪。一个女生丢了西方哲学笔记,“望速还,有重谢”。
楼间花园里的老子像被擦得一尘不染,假如没有文字标题,任谁也不会想到这个额头巨大的老人是老子。说是罗丹雕刻的巴尔扎克被穿上了中国古装也有人相信。老子一手伸出,手指蜷成一个半圆,但里面却空无一物,总令人感到缺点什么。我曾经用一个啤酒瓶子来填补这一缺憾,将酒瓶子正着插进手的下方,老子如同拎着瓶啤酒边走边喝,如果将酒瓶子反着插进手的上方,就变成了要敲谁脑袋的架势。
我把盛饭的塑料袋扎紧,以免凉了。在转身向筒子楼走去时,忽然想到,这一路连一只动物也没看到。无论是猫、狗、鹞鹰、鸽子,哪怕是一只麻雀都没看到,更别说美洲豹或印度湾鳄了。即使是城里,怎么会彻底没有动物出现呢?以前从未感到诧异,眼下微微有些震撼。
回到筒子楼,上了几段楼梯,拐进楼道里,我在靠门一侧的墙边看到了静止不动却又酷似动物的女性身影。
楼道纵深狭长,光线应该暗得可以,七八米之外能辨出男女就算不错,但我明明感到她如同某只动物靠在墙上。她半弯着腰,一条腿向前伸出半米,两手插在兜里,耸着肩膀。这种姿势,很多不拘小节的女性等人时都会摆出来。看到我走过来,她嗖地转过头,盖住脖颈的短发像只开一秒的花一样绽开又收收拢。目光明亮而又冷漠,仿佛天生的无可期待,无可怀念一般。
“如约而到。”她说。
“确实没说好什么时候来。”我说,“所以就是夜里踢门也算如约而到。”
她侧身闪开,让我掏出钥匙开门。进门后,我把饭放到没有抽斗的木桌子上问:“还没吃饭?”
“没吃。从那天你走后就没吃。”
“别说得那么可怜,你可给了我三千块呢。”
“确实没吃。”她声音不大,但一口咬定。
“那吃,那吃。”我拿出一个馒头给她,把饭盒摊开放好,又拉过两把椅子。说得这么不苟言笑,看来是真想开玩笑,我还没见过谁两天没吃饭还能照常行走的。
我更没见过谁两天没吃饭,见到食物还这么冷静的。她简直像履行任务一般小口咬着馒头,用筷子夹排骨吃。吃得不紧不慢,无动于衷,而且只吃了一个馒头就停手了,菜基本没动。
“是专程来听弹琴的?我随时可以弹。”
“你先吃饭,我不着急,反正随时可以听。”
听别人弹琴还“随时可以听”,我只好说:“我也随时可以弹。”说罢也吃起来。
“你这儿有什么酒?”
“只有啤酒,瓶装的,而且不多。”我想起她无限量畅饮烈酒的模样。
她已经从地上捡起一瓶啤酒,找到起子打开,把酒倒进杯子里咕咚喝了一口,随即又问:“有烟么?”
“你还抽烟呢?”我把刚买的“骆驼”烟拆封,递给她,“劲儿有点大,估计女生抽不惯。”
她无所表示地“唔”了一声,从兜里拿出火柴点上。我看看放在桌上的火柴盒,是一家高级宾馆套房里提供的蜡杆火柴。用这种火柴的点烟人,无缘无故给人三千块钱固然荒诞,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我拿起火柴盒端详了一会儿,发现上面写的宾馆位于云南昆明。
我问她:“你是云南人?”
她微仰着头吐烟,头也没转:“不是。”
“最近去过云南?”
“倒是。”
“就这两天?”
“对。”
()好看的txt电子书
“在云南什么东西也没吃?在飞机上也没吃?”
“没吃。”
我不想问了。她一口一口有条不紊地把烟抽到根部,我也草草吃完了饭。暴饮暴食之后,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的食欲反又变小了。她把烟按到用作烟灰缸的酸奶杯里捻灭,在细长的大腿上蹭蹭手,从兜里拿出一块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布来。布展开之后,原来是一幅长约一尺的蜡染,她双手举着布,按到钢琴对面的墙上比了比。
5维纳斯的Ru房(3)
“干吗?”
“墙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么。”她说。
我听任她从桌子里找了两个图钉,把蜡染钉在墙上。这表示她从此以后会经常来这里也未可知。蜡染的图案抽象迷离,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她钉好蜡染之后,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抽颗烟,就开始弹吧。”我也抖出一颗烟点上,透过淡蓝色的烟雾看着她。屋外的阳光温暖而强烈,照在屋里的部分如同晶体般具有质感。烟雾灰尘善于反射蓝色光谱,因此烟雾呈淡蓝色。
一个姑娘抱着双臂站在木地板上,一侧是明亮的木窗,背后是白灰墙面,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其自身的鲜活与陈旧的背景形成反差,如同文学杂志封二经常刊登的油画。题目大多是:“秋韵”、“阳光”或“青春”。
我们之间只有夹烟的手指与烟雾是动态存在。在这种默默无声的站立中,一瞬间晃过了几十年,也大有可能。假如不能判断出她像哪种动物,那么或许能够找出她与“人”这种东西的差异。抽烟的时候,我尝试做这个角度的努力。但烟抽完时,以失败告终。
“想听什么?”我坐到“星海”牌钢琴边,打开琴盖问她。十秒钟之后没听到答复,我便自己弹起来。从柴可夫斯基弹起,先是钢琴曲《四季》,然后是《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某一部分,接着是肖邦的两首夜曲,之后挑战了拉赫马尼诺夫暴风骤雨一般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由于最后一首曲目难度太大,其间出现了两次失误。
弹琴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蜡染壁挂下方静立。也许她找了个地方坐下,也许像来时在门口那样靠着墙。她是否又喝了啤酒或者抽了烟,也不清楚。更有甚者,她是否悄悄溜出门去上厕所,我也未曾察觉。
弹完这一轮曲目,阳光已经没那么明亮,窗外出现了桔黄|色光线。我头也不回地拿出一颗烟点上,休息休息手指,抽完烟开始弹奏第二轮。这一次的曲目有斯美塔那、德彪西将《天鹅湖》改编而成的钢琴曲和俄罗斯“强力五人组”的某些作品。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键盘上的手指,时间久了竟感觉手指在自行弹奏。最后一曲终了,我才发现琴键几乎看不清楚了。抬起头来,已近黄昏,窗子右侧大片大片的如同泼墨染就的红色,晚霞如血。
这就是动物般的女孩将手搭在我肩上时,窗外的景色。此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见过色泽和血那样相似的晚霞。直到通常意义所谓的“生命”终结以后,这一景色才再次重现。
下面的事情无不与“动物”这一具体感觉发生隐约关联。我停止弹琴,一阵头晕眼花,但还是感到肩膀上多了一只手。我也把手伸到肩膀上,按住了她的手,随即和她握在一起。我想站起来抱她,无奈两腿发软。她不作一声地坐到我腿上,和我接吻。对于接吻这个行为,我一向习惯于做技术化的分类处理:有唇与唇相触的、唇与舌头相触的,还有最淫荡的舌头与舌头相触;各种技术的应用要根据时间、场合、对象做进一步区分,比如说与女孩的头三次接吻不会涉及舌头,一般女孩除去Zuo爱时不会接受纯粹的舌吻。但这次接吻摆脱了技术的束缚,接吻就是接吻,接过之后,究竟是哪些部位相触我全无印象。最强烈的感受是和人类不可能完成这样的接吻,感觉自然美妙无比。
我喘了两口气,从弹琴的疲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