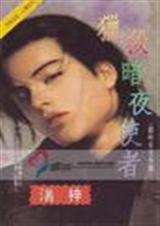暗夜慧灯-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右查,又加上陈女士阴魂不散,终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情郎不但摸过她,而且简直是简直啦。本来二人约好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谁晓得情郎早已安排下抽腿之计,用陈女士的口气,先拟好一篇把自己恭维成大情圣的绝命书,教她照抄一遍,然后骗得她先行服毒,而自己临阵脱逃。事情真相一经发现,傅斯年先生第一个没光彩。
我们介绍这件往事,不是翻旧账,而只是介绍当时对傅斯年先生的那些评论,几乎一致挖苦他阁下是“好事之徒”,说他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底细哩,就冒冒失失地乱发动,为一个普通女孩子折腾,有失身份。
天下无完人
傅斯年先生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出在事情发生了变化,陈素卿女士虽然死啦,情郎却没有死,而且即令情郎也死啦,事情却没有死。对死了的人赞扬尚且如此困难,对活蹦乱跳赞扬,自然更加危险万状。盖人不是石头,三十年前是啥模样,三十年后仍是啥模样;人是一种感情动物,三十年前虽非礼勿视,三十年后却可能被情妇的丈夫照屁股上给一枪。吾友汪精卫先生年轻时行刺清王朝的摄政王,在死因狱中吟诗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壮志凌云。可是到了老啦,却窝窝囊囊当了汉奸。人生如放演电影,电影正在放演,千万别下判断,必须等电影演完啦,大家一哄而散,再下判断,才能无误。
不过,赞扬是赞扬,最好判断是最后判断,赞扬是就一件事论一件事,就一种行为论一种行为,最后判断则是总体战,内容复杂得像太空舱。傅斯年先生这件事并没有做错,不但没有做错,反而恰恰地做对啦。他曾办过大学,也曾当过校长,一切都过眼云烟,只有这件事做得有深远影响,那就是:遇到认为应赞扬的事,就不顾一切地赞扬。至于剧情发生变化,那是当事人的事,不是他的事。这种气质是酱缸蛆所缺少的也。
我们对于“是”“非”,似乎只应就是论是,就非论非,不能像冬烘烘夫子改小学生的作文一样,提起大笔,抹了个净光。秦桧先生固然王八蛋,但他阁下当初却是忠于宋王朝的,忠于宋王朝的那一段仍应该给予赞扬。文天祥先生《正气歌》上有一句曰“为颜将军头”,聪明人对这句话颇起疑心。想当初张飞先生把颜严先生生擒活捉,教他投降,颜先生大怒曰:“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张飞先生一瞧,英雄英雄,亲自为他解绑,请他上座。颜严先生受了感动,竟投降啦。呜呼,这个只有前半截而没有后半截的“头”,似乎不应该当作座右铭也。但文天祥先生却是把他们分开的,只取其抵抗权势、不畏死亡的那一段,而不取其盖棺论定的评论。吾友小说家王蓝先生(最近好像又成了画家啦)有次对我曰:“老头,你可别碰我,如果碰我,我可把你十年前恭维我的信抖出来,那信我还放着哩。”这个年轻人真是小精灵,不过这似乎并不能塞住我老人家的嘴。有那么一天,他发生变化,我碰了他两句,不要说把该信抖出没有用,就是把它刻成石碑放到十字街间,教人家都来看呀也没有用。十年前他努力创作时,我是佩他服他的,万一他中途断线,我就不佩不服矣。呜呼,连张半仙算命都不能保终身,对一件事、一种行为的赞扬,或对一本书、一篇文的赞扬,岂能当保险公司的保险单用哉。
再重复一句,赞扬不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单,也不是大同公司的电冰箱,保用十年,十年之内陆王心学空谈心性良知,反对坐而论道,主张博学多问与实,有啥地方坏啦,只要打个电话,就随传随到。酱缸蛆因为坚信他阁下的一句赞扬就是保险单,所以,嘴巴就硬得像猴屁股。而一些被赞扬的朋友,也往往咬住一句话,当保险单使用。写到这里,想起一桩往事:当陈果夫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有一位朋友,用尽心机,把陈先生的一位秘书老爷骗得团团转,就在陈先生跟前推荐他少年有为。到了后来,西洋镜露了底,秘书老爷不再理他,他就跟秘书老爷翻了脸。大家劝他不可如此,他狞笑曰:“没有关系,那小子在陈先生面前把我的好话说尽啦,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再说我的坏话吧?他如真的不识相,陈先生不认为他反复无常乎?”他阁下真是深通酱缸学,果然该秘书老爷只好干瞪眼。但也算该朋友运气,如果遇到的是柏杨先生,我可是个老天真,准会把前三皇后五帝说个清楚。该朋友现在仍在当他的校长,乃绝顶聪明之士也。
呜呼,天下没有完人,不但没有完人,连天上也沉有完神,玉皇大帝就是个没有原则的糊涂蛋,欺软怕硬,如果不是告洋状告到如来佛那里,请来如来佛洋法洋术,他的摊子恐怕早被孙悟空先生掀啦。耶稣先生更是厉害,他那三位一体的老爹,随时随地都把一个城交给犹太人,教他们杀个净光。希腊神话里那些神仙先生,更不像话,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你害我,我害你,好像一窝土匪。
完人是没有的,每一个完人都有数不尽的疮疤;而彻头彻尾的坏蛋也是没有的,每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都有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时候。一个人在活着的漫长岁月中,似乎有权利听听赞扬。赞扬是一种无形而有力的鼓励,不但可使好行为更为坚定,且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以柏杨先生为例吧,我本来有点手脚不太干净毛病的(这不能怪我,实在是有些人钱多得使我生气,所以遇到千载难逢的天赐良缘,我就忍不住俘他几文,教训教训他),可是自从有些朋友说我伟大不掉,我就老实得多啦,前天坐计程车,在坐垫上捡了一块钱,我就没下腰包。
有啥区别哉
在佛教徒来说,是有“轮回”这么一回事的,人死了之后,先到望乡台上,用望远镜向故乡瞧上一瞧,殡仪馆里的热闹情形,便尽收眼底。这是他阁下最后的一瞧,任凭英雄好汉,大圣大贤,都会柔肠寸断。瞧过之后,进到灵罗宝殿,阎王老爷高坐堂上,旁边站着判官,批开生死簿,看你活到了头没有,然后再查查你活着的时候干了些啥。遇到善事,好比柏杨先生坐计程车拾金不昧,就加上十分。遇到坏事,好比柏杨先生曾打过十个朋友的小报告,该十个朋友因我的小报告,坐牢的坐牢,跳井的跳井,一桩扣八十分,共计扣八百分。而在公共汽车上乱看女人,共乱看了三百零八次,一次扣十分。这么一加一减,结果还欠阎王老爷一万九千九百分。阎王老爷拿出分数对照表一查,凡存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就转生当皇帝;凡存一万分以下的,来世就转生当经理;凡存十分二十分,甚至一分也不存的,来世就转生为可怜的公教人员,在低薪政策下熬日子。至于不但没存,反而欠了他老人家的,欠一万分以上的,来世变牛变马,欠十万分以上的,来世只好变猪先生,以供各位读者老爷吃油大。
——谈起轮回,又想起同音字,有人说因为同音字太多,才无法实行拼音。我老人家的意见却恰恰相反,正因为同音字太多,才必须赶快实行拼音。盖图案画是中国文化之癌,而同音字又是图案画之癌,必须彻底改用拼音字,才能把它治好。从前有位朋友死啦,到了阎王老爷那里,左查右查,查出他在阳世既栽赃又飞帽,作恶多端,分数对照表上规定他要转生一条狗,他阁下哀求曰:“大人呀,转生狗也可以,但最好教我转生母狗。”阎王老爷大奇曰:“这是为啥?”他阁下曰:“圣人不云乎: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呜呼,原来他阁下把“毋苟”当成“母狗”啦。图案画一天不垮,这种母狗节目,就一天无法避免,要想避免,只有拼音的一条路,盖随着拼音文字而来的音节自然变化,才能把母狗肃清。
柏杨先生在阎王老爷那里是存款抑或欠账,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各酱缸蛆先生千万别太早拍巴掌。不过经过判官这么一查,死人只有甘心认罪,盖人间法庭有说不准学,有奉命不上诉学,银子权势进门,不起诉焉,无罪判决焉,就在公堂出现,而阴间法庭,却是一板一眼,都有根据的也。于是乎,被拉到阴山背后,阴山背后有个奈何桥,奈何桥头有个阿巴桑,在那里卖可口可乐,送你一杯解渴。该可口可乐就是有名的“迷魂汤”,一杯下肚之后,你就把过去的一切都忘啦,然后牛头马面,用钢叉一叉,往下界一扔,哎哟哎哟,睁眼一看,好一头漂亮的小毛驴。
轮回的过程大概如此,主要的用意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生没有报为真实存在的是“共相”,个别事物是虚假的。提出证明上帝,死也要报。你阁下明明欠柏杨先生一块钱,你偏嘴硬,说没有欠,而且为了赖这一块钱,还飞帽兼栽赃,把我老人家整得拉稀屎。好吧,等到那么一天,人死官灭,阎王老爷可能就教你变个小毛驴给我骑。
一切问题都集中在来世的报应上,柏杨先生虽然一再拜托酱缸蛆别太早拍巴掌,但我却真愿意知道下一辈子是个啥。即令变不成母狗分子,变个难得糊涂分子,无灾无难到公卿,也确可心旷神抬。如果判官先生暗中给我通个消息,说高阶层已经决定我来生非变个蟑螂不可,就悲从中来矣。有位朋友曾询问过一位高僧(他叫啥啦,偶忘之矣),问他前世如何,后世又如何。这真是大哉问也,纵阎王老爷,都得查查簿子才能回答,可是高僧到底是高僧,他不经过大脑就答啦,而且该答话成为千古不朽之句,他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呜呼。前世为善为恶,用不着左打听右打听,只看你今生是些啥遭遇,就可知之矣。今生老害砂眼,前世一定乱看女人。今生被隆重砍头,前世一定杀人如麻。今生怕老婆,前世一定踩死过一只小老鼠,贵太太就是该小老鼠变的,来报想当初一脚之分。至于下辈子当官当民,骑到别人头上或被别人骑到头上,则只要看看你现在干的是啥,就可下判决书矣。今生只打小报告,来世准屁眼长疗疮。今生是个酱缸蛆,来世铁定地要变成三家村的尿壶。
我们介绍轮回学说,可不是拜托读者老爷信佛教,而只是想介绍介绍这位高僧的四言名句。这名句使我们想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这文化是好是坏,用不着把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只要睁开御眼看看今天我们受的是啥洋罪,就应该明白矣。而我们子孙将来能不能复兴,也用不着到卦摊上找张铁嘴,只看看我们现在做的是啥事,也就应该明白矣。
然而,虽然“今生受者”是一个阴森森的大酱缸,虽然“今生作者”是大家纷纷在木板船上努力凿洞,可是仍有人自以为我们祖传这一套,放之四海皆为准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意识的作用”和“人们的思想”,,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就十分地妙不可言矣。呜呼,抗战之前,柏杨先生曾在报上看到过一位记者老爷的西北访问记,该记者大概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长大的,一旦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对女人的小脚,大为惊奇。该报道原文已记不得啦,只记得大意是,他访问了一位小脚老太婆,该老太婆谈起当初缠脚的英勇战斗时,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缠脚缠死的,也有女孩子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