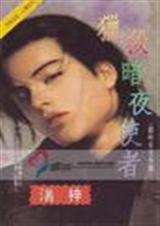��ҹ�۵�-��3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ۼ����Ҵ��壬�����е�����³�������Ժ�ȥ���������ӣ�ȴ�����й���������ͶЧ���ҿ�û�������������г�һ�գ�������³��������ܳԺ���������ٵ���̫��̫�꣬�ڳ¹����˰�Χ���������������ա�
����������������û���ֹ���ɫ���ţ���������ȴΪ��һ��Ư��Ů�˳Թ�������С��Ӽ����ӡ������ӣ�����Ҳ��������������������֪����������û�У��������������࣬��ɫ���졣����������������ͷ������һ���������ˣ����鶼�飬����������ʱ�����࣬��������Ի��������֮������֮��������֮�ߣ���ɰ������ǣ����������ú��������鼱���ˣ��ɼ���̬���ء����Ǻ�������ʥ��̸��������������Щ�˿�����ʥ�˶���һ��ľͷ��û�а�����û�����ɡ��ҿ����������к������������һ��ҧ��������ȵ����˾��ӣ����Զ������硣
����Ȼ�������������ԳԲ��㣬�ϼҵ��������ڸ���ͨС��û�зֱ����Dz��ò����飬ʥ��֮�����ഫ���Լ�ǿ����˰�˹���ʥ�˵�������ͳ��Ӧ��Ϊ�й��澰֮һ���Ա�����˹۹�������
��������ʥ�ˣ��γ���ϣ���������֮����������ƴ���ظɣ�ǰ����֮�����������ݡ�������û����������ߣ���Ⱥ�ڰ�Χ������������Ҳû�и�Ư��Ů�˾������壬�ֵ���ѧ�����䣬�����Ըϲ��Ͽ������������������������ǵ÷���֮�ȣ������¸������ڽ�ǿ������֮�ʣ�ֻ��������һ�˳��������䵱ʱ��ĿΪ���ӣ��ܶ�����ҲûŪ��һ�ٰ�ְ������ѧ�����������ۼ�¼����������Щʱ���ʵ���ү֮�࣬����������һ��ͳ�ν��а�������һ���������������������λʵ����������������ټң�����������֮�١��Ӵ˿���������������̨�̣�����������Ų�����
����������������һ���ӣ���������ʥ�ˣ������˸���˵�ӡ�����������������ǧ�꣬����һ������ʥ�������������˹���ʥ����ʲô�̶ȣ��ò���˵��ʮ������֮��������й��ˣ����¶��Թ����Ŀ�ͷ����������������ţ�����ȥ��һ��������ע��ġ�ʫ������������ū�Ժ����������������������Ҳ�ܰ������衣
���������������µ�һ��������¡���̨����Ů������Ůʿ���в�˼��ͨ�飬���һʱ����̨��̫��������˼�������������ƹ����ߣ�ʥ�������������ƹ�����Թ�������ڽܳ��ķ������ң��������ߡ�ԭ��Ψ��������ѧ�ҡ�������������Լ�������ģ���������Ƴ���ͷ����һ��С���������������˵��������Ю�����Ρ������Ű���Ůʿ���������̿��������ϡ���֪��һ��������������군�����ǡ����ʵ����ʥ�������۴��̫�ᣬ�����Զ��֣�����Ůʿ��ʵ�е�������Բ����й����칫����������Ѻ�������һ�����Σ�һ�����������
�����ۿ��Ŵ������ˣ��ҿ��������ʵ۲��������ǻ쵰�������������������£�ѯ�ʴ�ij�ˣ�ϧ���������ӣ����ɲ�ó�������Ի������œ���������ʵ۴�Ц����������������Ѳ�ط��٣����������������Ůʿ�����ͷš�����Ůʿ�Դ�л֮Ի�������ǰ��糾��ֻ��ǰԵ���仨������ʱ������������������ȥҲ����ȥ��סҲ���ס������ɽ������ͷ��Ī��ū�鴦����
�����غ������Ǿ���ι��£�Ϊ������һ���࣬�ô�ҿ���ʥ�˵��������й���ʥ���ƺ����κ�һ����ʥ�˵�Ѫ��������ǧ����ʷ�ϣ�û�в���Ȩ�ƽ�ϵ�ʥ�ˣ��������������ûʵ۷�ʲô����������ʲô��ʥ��ʦ֮���ܴ�������������������ȶ���֮�������ܲ������Ĺ�������һ����Ů������������������ˣ�����ǧǧ����ĵ�ò��Ȼ������ɶ��˵�ġ�
��������������ΰ��Ĺ����ƺ������������ˡ����ӡ�����С�ˡ������ʣ���ǧ�����������ַ���֮���������ݱ�������������������Ӱ���ߣ�����1894�꣩����������ɵ��������ѧ������Ψ��ʷ�ۡ����ڡ���ʦ�����ϣ���Ҫ�ʵ�ԶС�˶����ӡ��治֪������������������������ʱ���Ǻ�����״̬������һ�����ϵĸ㷨�������е�ë����������������Ҳ��������ַַ������������뼸���书��ǿ���˵���������æ�����й��˵�����֤�ϣ�����ע����ijҲ���ӣ�ijҲС�ˣ�Ȼ��֪ͨ�������ڴ���ϼ�飬������С�ˡ������ߣ�һ�ɸɵ�������ʣ������ȫ�ǡ����ӡ���������̫ƽ���գ�
����������ͳһ�ģ����˸���Ȼ����ʱʥ�ˣ���ʱ���ޣ���ʱ���ӣ���ʱС�ˡ���ijһ������ʥ�ˣ�����һ���������ޣ���ijһʱ���Ǿ��ӣ�����һʱ������С�ˡ����������Ĵ��Ķ��ַ�����Ȩ�����ã����й���̣����ǧ�ꡣ������϶���һ�룬���һ��Կ϶���һ������ѱ������ף��ҿ���ҳ��綼Ҫ��һ���ҹ�ϷҲ��
�����ҿ���������
����һ���¹���Ľ����Dz����ģ������ھ��ñ��ʵĸĽ�������ǷDZ��Ľ������Լ�˼�����������ɡ��Խ���������ˣ�����������Ҳ������ˣ�����Ů���⣬������ˡ�������Dz������¹������������һ��ǧ�����ɱ��е���ᣬ���ܰ��Լ��������غ�����ֻ�����Լ����亦����С����Ҳ���鷳���ǣ������鸯���˵Ĺ�ʺ��������̾�����ʶ֮ͽ����������ǡ��������������ɵ������ǾͲ��������Լ���Ҳ���˱��ˣ��Ʊس�Ϊһ���쳣�ɾ��İ���ʯ���谭�����ҵĽ�����
����һ�˾����꣬���ѷ������������Ĺ��������������֯��ѧ�ֻᣬ�ᳫ����Ȩ���͡�ƽ�ȡ������˽��죬�����Ƕ������ʶ֮ͽ������Ҳ����������ԡ�����һ���¹���һ������ɵ��Կǣ����¹�������ˡ�а˵�������桰�����������������ֵ��������磬ȫ�廩Ȼ��
�����ڵ�ʱ������ʶ֮ͽ�У����������ر��Ƽ�����������Ϊ���������ر���������µ����ۣ��Ա������ү���¹ʶ�֪�£��������ţ�йй�����������������ǡ�������֮������ģ�ӣ����Ժ�����Ϊ����֮���䡱����ģ���ӡ�
�����������ᳫ����Ȩ����ƽ�ȡ�����ѡΪ�᳤���涨�����׳���ⶣ�Υ�����ߣ�����ᡱ����ʶ֮�������������̶�����鲿���еĵ�һ���֣����������Ծ�����û���⻯Ϊ��Ȼ�磬ʹ��֮Ի������Ȼ����������������ᣬ��ƽ��а˵���Է���֮Ҳ����������Ҳ����������Ҳ���������к��ֵܷ�����֮�У��ǹʡ��ȡ�����ƽ������ƽ����һ�е�����ʩ����������֮�ɼӣ�����ν����ⶡ��ƺ���ʥ������֮�����Ժ�����׳����������С�Υ�����ߺ�������ߣ��ڻ������δ��Σ������ͣ��Է�ʥ�̣����桮���������գ��������Ϊ�᳤������ѧ���³̣��������������ʡ���ɡ���
������ʶ֮ͽ������ʡ���ɡ�����������˳���ڴ�ҲȰ������ʡ���ɡ���������ү������л�Ѫ��Ӳ���ģ���ò�Ҫ���������ٿ�������Ļ������ſ��ţ�����ƽ��ԭ����а˵����Ѫѹ���ߣ���֮�Գ���Ѫ����ʮ�ֱ�Ǹ����
����������������ƪ��һ�ģ�Ի��������֮��Ҳ���ӣ������������������ӣ�����������֮�����¸�������֮����ǧ������裬������ꡣ���������ڿຣ����֮�У��ݺ�۳�����������֮�أ���֮��֮����̤֮֮����ţ��Ȼ����ݮ̦Ȼ����
������ʶ֮ͽ��֮Ի�����ҳ��������������������������澡���Ϻγ���֮���ºγ����ޣ��Ҷ�ǧ���Ժ��������ʥ�������������������ġ����й��Ŵ���ѧ�����ָ�졢�ء��ˣ�����ѧ���壬������������ν��������꣬�������ã�������̤����ţ��ݮ̦��Ŀ�й���ǧ���ӡ���֪�����ڣ����ڶ�ǧ����Ҳ���������ڿ�ɣ�����ó���ɥ�IJ���֮�ۡ���
������ʶ֮ͽͷ���ǡ��ҳ��������ž��ǡ�ʥ�����ࡱ�����Ǹ�ʱ������Щ������ţħ���ĸֱޣ�С������мܡ�
��������������Ի�����ǹ�Ը��������֮�ܣ����֮ī���������ˣ���ı���ڣ���һֽگ�飬�϶ϱ���Ի�������������ˣ�Σ���ռ�������Ŀǰ��һ�����ã�����֫�ʽڽ⣬������ˣ�˰�ݺ������������ܣ��������δ�ã���֮���£��������ӡ�����
������һ����ʶ֮ͽץסС���ӣ�һ������ѧ����������������Ի��������گ������������Ϸ�⣬���˵ȴ�����֮�Ժ���������ڹ��ʻ������������֮һ��19����70����μ���������ˣ�������ݣ����Լ��̣�����δ����乼����
������ʶ֮ͽ�����������һͷ�Ե������Ȼ������������������������ν�����ӡ�Ҳ�ߣ�ָ���������������þͶ����������������ڻ���һ��δ���Ļ����Ӳ��������ڵ�ͼ��ݹ���Ա����ſ���һ��æ�����ݵ�������ͷ��������
�����������ᳫ������Ի�����ĺ�һ�ģ�һ��������������֮Ȩ�������Ծ���Ϊ�ǣ�����䣬�������ǡ���
������ʶ֮ͽ������Ҳ�ܲ��ˣ���ŭԻ�����������ߣ���Ȩ���������䣬�������������ֱͨ�ߣ�Ω����֮��������������������֮Ȩ���ξ��̱�������������Ӱӡ�ο̱����°���ӡ�����������˸�������Ϊ�ģ���ʹ����������ɢ��ͳ��Ҳ����ν����һ���ģ���νʵ��������Ҳ�������������٣������������֮��̩�����̶�������Ȼ������Ժ������Ϊ��������̩�����Ҳ������ӡ���������䣬�������ǣ�������ֱ��������ʥ����Ǭ�ٶ���֮���£���Ϊ̩������֮������˹��Ϊ��죣��溺��֮���գ���
����һ̸�����������Ϸ���������ż���������˵������Լ����������ڽ�����ݽ�����������������������������������ͷ�����ѽ������ѽ����С����ϥ�Ƕ�������ѽ������������Ͳ�ס�������顱���ڣ���͡�������е��࣬�Ƿ��������ɤ�ţ���ĭ�Ľ��������Ӯ����Ҳ��
����������Ի����ϴ��ϰ���ӹ�������һ�з���ϸ�ʣ����ɹ����������������ӷ�����ѡ���ᣬ�������£������跨�����ܾ��ɣ�����ѧУ���������ף�һ���ǰ��������ʣ��Ψ̩������Ч���ÿ��Ӽ��ꡣ��
������ʶ֮ͽ���洷��Ի�����𱰹������һ��֮�֡������������в���֮��������Ȼ����⫱ɶ�������������ڮ������ʥ�����ƶȣ����ɵ������ϣ����Sophistes�������ɣ�����һ���롣������ʵǧ��δ�С�������̩����Ч���α������ÿ��Ӽ��ֱ꣬Ի��Ү�ռ���ɶ�����
��������ʶ֮ͽϰ�����𱰹����ϰ����ū�����ġ���Ҫ˵����������ľ���ȣ������ϵ۶���Ҳľ���ȡ����ɡ����Ӽ�Ԫ�����ݳɡ�Ү�ռ��ꡱ��Ҳ����ʶ֮ͽ���е������ǡ���ʥ������Ū�����Ժ�����ż�����˲���������Ƥ�����ﶼ���µģ��������ܵ����գ��������ܵ����գ�
����ֻ��������
������ۺ����������ġ��ػ��밮�ġ����ء�����̨��˼�����У���������������ʱ��һ���¡�������һ��������ʮ�����գ������ռ���дԻ����һ�Ժ���ϵ���ڷ�����ʶ�ң��������ҷ��ӣ�����ȥ�Է������Ƶؽ��ҳԷ�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