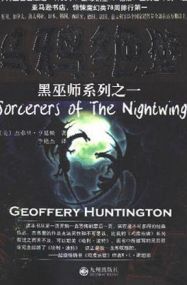乌鸦绝壁-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得汶说,“那个方尖石塔。”
“很奇怪,是吧?”她问,“只有穆尔家族的人葬在那儿……也许那是一个穆尔家值得依赖的朋友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仆人……”
“在乌鸦角的户口登记册上只有一个叫米兰达·得汶的,她死于1966年。”他告诉她,稍微有点儿失望。
她看着他露出一丝微笑。“喔,两天的时间里你已经做了一些调查了。”
“我已下定决心弄明白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
“你认为你父亲希望你这样做吗,得汶?毕竟是他把你养大的。他从未说起过你的亲生父母,也许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得汶想了想她的话,说:“我父亲希望我知道,我确信这一点。如果他临终前不告诉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告诉了我,格兰德欧夫人,并且他告诉我,我必须自己弄明白自己的命运。”
她紧闭着嘴,拿着茶杯走到壁炉前站住。
“不仅如此,格兰德欧夫人。他还把我打发到这里。他可以找其他的监护人,但他却把我打发到这里。”
“是的,”她更多的是对自己而不是对他说,“是他把你打发到这里的。”
他弄不清她的话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明白她对这件事的态度是痛苦,或是感激,还是怨恨。他接着说,“我肯定我父亲把我打发到这里的原因是在这里我可以弄清我的过去。”
她转过身面对着他,严肃地看着他,“你来的那天晚上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有许多秘密的房子。我也告诉过你,我们尊重这些秘密。我们不要探究它们。现在我给你提个建议,得汶,我希望你记住它。问题的答案不在过去,而在将来。如果你想在这里生活的幸福,要向前看,而不是寻找过去,不要去探究这所房子中的每个影子和进入关着的门。之所以关闭那些门,是有其原因的。”
然后,她说有事要做,需要离开,并告诉他如果有事,可让塞西莉到她的房间去找她。得汶看着壁炉里劈啪作响的火焰,投到大理石地板上的像敏捷的精灵一样跳舞的影子在点头。
“无疑,她知道的比说的多,”他想。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一定要对她加小心。”她是朋友还是敌人还不清楚,现在问她太多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再说,他认识到,他要寻找的信息需要他自己去发掘。
那天晚上,是自从他到这儿的第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他漫步走过屋外的空地,边走边听下面海浪咆哮的声音,在他沿着悬崖边向前走时,这声音使他的情绪平和了下来。
十月凉爽的风吹拂着他的脸,在明亮的月色下,他往下走了一段,来到一个能看到崖下海浪的地方,海面上像跳芭蕾一样摇曳的月光太让人着迷了。他在悬崖边上一块光滑平坦的岩石上坐下来,脚悬在空中。这里距下面的海岸垂直距离大约有一百英尺或更多。他认识到,这就是魔鬼岩,也许他坐的地方就是艾米丽完成她最后一跳的那个地方。突然,一种可怕的悲哀深沉地钻进他的体内。那一刻,他想了到爸爸,想到他躺在床上,寂静冰冷,似乎是害怕死亡,大瞪着双眼。
“不要再想了,得汶。”他暗自对自己说,但已经太晚了。在爸爸死后的几周里,爸爸的形象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失。爸爸躺在那儿,瞪着双眼陷入死前的空虚,青筋暴露的手放在他的胸前。他这样在床上持续了几周,并且得汶习惯了这一成不变的做法:坐在他旁边等他睡着后,然后他再回到自己的床上睡几小时,天刚一亮,他就回到爸爸的床边等他醒来。直到一个特别的早晨,当得汶摸他的时候,发现他冰冷僵硬。得汶吓得跪在床边抱着父亲的身体,哭了。
“乌鸦绝壁的幽灵可以回来,”夜色中得汶喃喃自语,“为什么你不能?”
“他能,一定能,”那个声音说。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得汶。”
他把手把伸到衣袋里,紧紧握住圣·安东尼像章。“如果你感到迷惑,圣·安东尼像章会帮助你。”爸爸临终前几天,告诉他,并把像章交给他。
“我从不知道你信教,爸爸。”得汶看着他手掌上的又小又圆的扁平银制像章说。
“所有的宗教都是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宗教来源于精神,精神的力量来源于正义。”爸爸微笑着看着他,“你要保证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得汶。”
“所有的力量都来源于正义?”
“是的,”他父亲告诉他。“如果你记住它,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比这里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强大。”
“我要努力记住,爸爸,”现在得汶对他父亲说,“但是这太难了,呆在一个我不了解的地方,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能不能相任,爸爸,我想你呀。我多么希望你在这里,我试图发现你为什么把我打发到这儿,但这里有太多神秘的事情,并且魔鬼也来到了这里,和以前相比,它们更厉害了,更难对付了。”
他双手紧贴着身体,垂到崖下悬空的腿不停地摆动着,同时身体也随着摆动。他想像,艾米丽带着一颗被她那个野蛮、自私的男巫丈夫伤透了的心站在这儿,耳中是自己急剧的心跳声,脸上满是泪水,过了一会儿就跳了下去,身体撞在下面的岩石上,鲜血染红了海水,撞裂的遗体被大海带走了……
想到这儿,他小心地站起来,看着远处的海浪,突然觉得腿有点发软,急忙后退几步来到了草地。他觉得有点晕,就离开悬崖往回走。穿过庄园时,修剪得很好的草坪和灌木显示出西蒙的技术,左边的网球场默默地呆在那儿,右边的花园懒洋洋地伸向大海,那里的花大部分都凋谢了,月光下几个大南瓜很显眼。他抬头看那大房子,阴冷的侧影映在夜空,他刚到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见过同样的侧影。
“塔楼已经锁了好多年了。”他说,似乎是让自己相信那忽明忽暗的黄光不是真的。
究竟为什么要锁住,他想,是为了控制什么呢?
有一天早餐的时候,得汶和塞西莉坐在一个可容纳二十六人的大桌子的角上,磨光的大橡木桌子使他俩显得很小,他们一边吃着米饭和新鲜水果,一边互相说着话,塞西莉逗得汶说:“我想,我告诉你我的幽灵的故事是多余的。”
“不,塞西莉,我想很有必要。我在塔楼上看到过一个影子。”
她做了个鬼脸,显得有点烦,似乎她不想深究这些事情。
“你从未在那里看到过什么?”得汶问她,“你不是也听到哭泣的声音吗?”
“也许吧。”她皱了皱眉,“你看,得汶,在这所房子里我想不明白得太多,我有另外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塞西莉,你能否认——”
“为什么?”她很烦躁地看着他,“因为不这样我就会发疯!想一想我从小就在这里,这么多年,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吗?!”
“你之所以有另外一种看法,是因为那是你母亲经常那样告诉你。”他很认真地看着她说,“我说得对吗?”
她撅着嘴,没吱声,她的沉默告诉得汶他说对了。
他大笑着说:“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按你母亲说的去做的?”
塞西莉不安地看着他,眼睛里闪着一种很难说清的光。“在这方面,我仅仅简单地按妈妈说的做,从未想过什么。得汶,我还是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我被可怕的、恐怖的噩梦惊醒时,我不得不相信妈妈对我说的,那哭声只是风在叫,走廊中的影子老房子中都有。当她说这里没有什么会伤害我时,我也相信。现在我不能不相信。”
说完,她推开她的碗,上楼去了。
他不知道哪里惹恼了她,但他需要有人进一步证实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早饭后,他在图书室碰到格兰德欧夫人,他奇+書*網决定直接问她。
“你是一个有决心的年轻人。”听完他的描述,她说。她今天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衣服,长长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手里拿着三本旧书:一本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其他两本看不清是什么书。图书室散发着霉味和尘土的气息,但是藏书却很多,往往都会使他轻松,但此时,他既感觉不到轻松,也感觉不到的它们的艺术魅力。这都是因为他的心思不在此,他已决心查明这里有什么瞒着他。
“我相信我看见了灯光,并且是两次。”他坚持说。
“好了,我会查一查的,”她懒洋洋地翻着书,用一种很厌烦的口气说,“也许是一些老的电器设备短暂地被接通,那里的线路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更新了。”她合上书,“我得谢谢你,得汶,你从另一方面提醒了我们,那里存在着潜在的火灾的危险。”
这就是她的回答,现在他只能接受。
“顺便问一句,得汶,”她冷漠地说,“我和亚历山大谈过,他说你袭击过他。”
“不,我——”
“你不必解释。我明白这孩子的想法。但我希望你和他能成为朋友。记住,我希望你给他做个好表率。”她把《海克·芬》递给他。
“给,你带给他好吗?我告诉他我要送他几本书看看。在决定他受什么学校教育以前,我希望能把他的注意力从电视上引开。”
她走出了图书室。他只能摇头叹息,又没什么收获,但他还是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楼上,也许他能从那孩子身上得到点儿什么。他又在游戏室找到了他,他正在用手托着下巴坐在电视前,看那个面容丑陋的小丑表演。“在这个节目中又看到了什么?”得汶问。
亚历山大没有理他,欠了欠身从他手里接过书,电视上马哲·缪吉克还在比较字母“M”和“N”:“听起来它们几乎一样。”那小丑用刺耳的声音说。
“是重播吗?”得汶问。
亚历山大微笑着关掉电视,“如果你想出去玩的话,我可以不看电视。”他说。
得汶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你想和我出去玩?”
“是的,为什么不呢?”
得汶咧开嘴笑了,“你似乎和昨天完全不一样了。”
“嘿,我需要一个哥哥,”他微笑着,“你不认为我们会成为朋友吗?”
得汶仔细地审视着他。
那孩子哈哈大笑。“我要改变我是个粗暴的孩子的形象。”他眼中有一些东西在闪,是挑战,是蔑视,还是有什么秘密?这些得汶在第一天曾看见过。
“我想你会喜欢那本书的,”得汶指着《海克·芬》说。“我像你这么大时就喜欢看。”
亚历山大又咧开嘴笑了,“我不能想像你这么大时是什么样子。”“唔,”得汶说,“我是。”
“你也像我这样陷入困境吗?”
得汶谨慎地回答:“唔,我也有些麻烦。”
“像什么?”
“我们那儿的教堂墓地旁边有个走廊,有时我和我的朋友们到那里去玩,因为走廊已经很旧了,并且砖都松动了,屋檐下还有蝙蝠,我们不应到那里去玩。但是,我们每个人又都喜欢去那儿。有一次一个牧师走出来看见我和我的朋友苏在那儿——”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样?”
“没干什么,”得汶为这孩子的猜测吃了一惊,“我们只是在聊天。”亚历山大带有深意地咧开嘴笑了,“我敢打赌你们只在聊天。”
“是的,”得汶感到声音比预想的要刺耳。“我们只在聊天,并且从一个管子里挤出吸血鬼的血。”
“吸血鬼的血?”
得汶哈哈大笑起来,“那只是红染料,但是我们把它涂在手和脸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