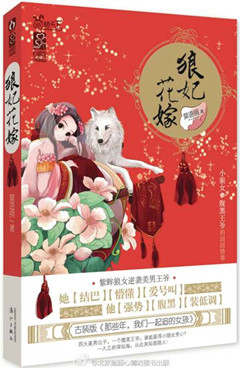江山不负-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父皇。”纳兰瑞伏在地上,语气悲凉,一旁的曹泉仿若老僧入定,“请父皇节哀。”
“老三啊,他是你皇兄!”皇帝叹了口气,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似的,“是朕小瞧了你。”
“父皇,儿臣亦不想走到这一步。”纳兰瑞这时已是直起身子,连如同缝在脸上的温雅笑意都隐去,神情上的悲凉凄楚却不是作伪,“皇兄在您饮食中下毒,指使江源勾结周人杀死李由,又豢养死士肆意绞杀与他不合的大臣,这般行径,父皇都能忍他,只是禁足了事,儿臣也是无话可说。儿臣不能由着父皇把祖宗基业,交到他手里。父皇您既然不给,儿臣就只得抢!至于今日的局面,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老皇帝转过头来,看着纳兰瑞,面色震惊似是全然不认识面前人,纳兰瑞亦是一脸平静地与他对视着。
“能叫玄汐给你做细作,老三,是朕,从来没有看清过你这个儿子。”皇帝的声音虚弱而又无力,“苏岚,你去,把朕的旨意记下来。”
“废太子,命赐死。皇三子着封为太子。”皇帝语意讽刺,说着竟是笑出声来,“左右你早就想好这圣旨的内容了,便自个写吧,玉玺,你也自己盖上。”
“诺。”苏岚恭谨地应了声,下笔极快,顷刻间便写好了旨意,由着曹泉加盖了玉玺,将那旨意拿给纳兰瑞。
纳兰瑞上下扫了一遍那圣旨,将它又交回苏岚手中,便笑着站起身来,对着皇帝道:“父皇身子虚弱,儿臣就不耽误您休养了,至于殿外兵马,如今朝堂局势不稳,就留下保护父皇吧。”
“朕身子不妥,老三,即日起你便监国吧。”皇帝瞧着纳兰瑞缓缓道,“不必报朕裁决,自个拿主意就是。”
“诺。”
寝殿又恢复了一室静寂,皇帝颓然地倒在床上,愣愣地看着明黄的床顶,眼角缓缓流下一颗泪来。
方才,他是真的怕了,怕了这个他原来从未看透的儿子。
然而,也直到此刻,他终于确定,纳兰瑞才是最适合这个位子的人。在这个残酷的大争之世,只有这个儿子,能带着这个帝国,登临天地。
“皇后啊,朕对不住你。”半晌他才叹了口气,擦掉了眼角的湿痕。
京郊护国寺第一声晨钟响起,这城中五十四间大寺的钟声,随之次第响起。京中九门在这钟声之间,亦再度被开启。
第二十六章 崇安宫变(五)()
二月初八的早晨,长平城又下起雨来。雨落如丝,冲刷着城里的石板路,将血迹也卷入两侧的水沟之中。
今日东市街官道上净街的,并非京兆尹衙门的衙役,黑甲蓝衣簪红缨,这乃是禁军第一卫羽林卫的装束,十步一岗,面无表情,在这细雨蒙蒙之中,显得尤为严肃。即使是住在京郊大兴县的官吏,此刻也已隐约知悉昨夜里这京城已是改换天地,更不要说,这消息灵通的京中官员。
所有官员的马车都被黑衣银甲的神策军,拦在了庆安门下,竟不容得再走,往日里官员皆是在宫中最后一道大门崇安门处才下马步行入内。约摸一盏茶过后,仍着甲衣的玄汐才打马从庆安门而出,直到了苏家的车马前,拱手行礼道:“劳国公爷久候,请入宫。”
下了马车,才瞧到,这庆安门直通到太和殿前,满眼看去,尽都是神策军帽上的赭红色簪缨,才过了庆安门,便隐隐闻见血腥之气,越往前,便越浓烈。
近得崇安门,有些官员已是颤抖起来,空气中还夹着几声压抑不住的惊呼和呕吐声。地上尚有未清理的尸首,整个崇安门广场上,血迹斑斑,初春时节,广场上一片空旷,刚刚长出的草,亦被染成暗红一片。
行在后面的几个文官,频频看向自己的衣角,只觉着,那血迹似乎仍在流着,染在自个的衣角上,心上。
前头的几个世家家主,亦是神色各异,虽都是一副神色平和,目不斜视又面无表情地走过崇安门。朝堂之上的波光诡谲,生死相搏,他们早已看惯。昨夜里,亦是顺应时势,各自维持着京城安稳。可待见到那被放置在太和殿前广场上的纳兰瑜的尸首,还是不由得心中一震。
这位新君的手段,太狠辣了些啊。十二年的温和外表,在这一夜之间便被撕裂。以如此残忍地方式,在获得胜利的第一个早晨,就震慑群臣。可就连苏晋都必须承认,这或许也是最仁慈的方式,以最少的血挽回最大的利益或是稳定。这不由得不称赞为高超的政治智慧,而苏家宁可抛弃流淌着世家血液的纳兰瑜也要选择纳兰瑞,看重正是这所谓的政治智慧。
后面的惊呼声中,有人终于承受不住,昏厥过去。但更多的人,只是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便恢复如常,低眉敛目,更加快速地行走。
李由瞧了那地上的尸首,一眼又一眼,终是低下头,却连叹息都不敢发出,只惨白着面色,踏入太和殿内。
太和殿的御阶之上,纳兰瑞早已负手而立。前夜里染了血的白袍换成了重紫的锦缎长袍,一百零八种龙纹盘旋其上,竟是显出从未有的尊贵。往日温和的面孔,此刻依旧带着温和笑意,只是,往昔叫人觉着如沐春风的模样,此刻只叫底下人隐隐惧怕。
御阶下此刻只站着一个人,苏岚亦脱了甲衣,只一件大红色袍子,静静而立。大红色锦袍上,黑色线条勾勒出繁复的苏氏图腾,被暗红色的血迹灼的斑斑点点,整个人身上似乎都散发着浓重的血腥之气,一身的肃杀之意,弥漫在这太和殿中。昔年的苏家公子,琴棋书画样样玩的风雅,楚京里的少年常挂在嘴边的那句“人不风流枉少年”,便是她醉时所说。可眼前这人,风华依旧,却再不是,他们眼中的一等富贵闲人。
如今她站在那里,展开明黄色的圣旨,一字一句地读出陛下的旨意。
“敕。储贰之重,式固宗祧,一有元良,以贞万国。皇长子瑜,矫诏行谋逆之举,罔顾人伦,不堪为君。废其太子位,命自尽。皇三子瑞,器质冲远,职兼内外,彝章载叙,遐迩属意,朝野具瞻,宜乘鼎业,允膺守器。可立为皇太子。所司具礼,以时册命。”
“敕。朕君临率土,劬劳庶政,昧旦求衣,思宏至道。而万机繁委,成务殷积,实疲听览。皇太子瑞,夙禀生知,识量明允。自今以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既溥天同庆,宜加惠泽。文武官人,节级颁赐,务存优洽,称朕意焉。”
纳兰瑞站在那里,只听着苏岚缓缓念出这两道圣旨,成为太子,监国摄政的喜悦,不过是崇安门下那一瞬,此刻也已消弭。他却依旧微微一笑,只觉着,苏岚果然文采斐然,不负大楚文坛宗主的风流之名。
苏岚已将诏书念完,转身呈于纳兰瑞,苏晋率领百官跪于地上,高呼:“殿下千岁千千岁。”
第二十七章 江山谁主(一)()
纳兰瑞依旧恭敬地站在玉阶上,离那空置的明黄色龙椅,不过是一级台阶,却半分也不曾靠近,只是站在原地,道:“诸位卿家平身。昨日,宫禁大乱,陛下痛心之余,病体愈重。本宫受命于君父,居储位,暂摄国政。望诸君克己奉公,勿受朝局所扰。若有意图扰乱视听,趁此时得利作乱者,本宫绝不姑息。”
众臣的脑海里都浮现出崇安门前太子的尸首,皆是一凛,哪敢起身,跪着到:“臣等定当肝脑涂地,为君分忧。”
“自然,兢兢业业者,本宫亦瞧在眼中,诸位,平身吧。”纳兰瑞笑了笑,又对着礼部尚书说,“赵尚书,本宫的太子册封典仪,就先省了,不必再议。”
“今日,朝会依旧,诸君有本,可启奏了。”纳兰瑞笑着叫人搬了张椅子,坐在了龙椅前方,脸上依旧挂着和煦笑容,哪里像是那个逼死亲兄长的人。
“殿下,臣有本奏。”纳兰瑞刚刚坐定,却见一人出列,跪在地上,竟然是张桓。
“延熹九年,瑞嫔娘娘卒于宫中。娘娘终身简朴,素有贤名,临终时尤言,无需丧礼,不事厚葬。今上怜其贤德,故允之。”张桓微微低头,跪于殿中,并不去瞧纳兰瑞的神色,“而瑞嫔为殿下生母,理应厚葬。臣知殿下至孝,不忍违母临终之遗愿,奈何朝廷早有礼制。臣请追封瑞嫔娘娘为皇后,迁葬皇陵,入宗庙,永飨后世之香火。”
大殿里,一片静寂,只听见张桓叩头的那一声响。
御阶之上,只有纳兰瑞一人站立,听了这话,他只是侧过身,缓缓摩挲着那把龙椅,神色仍旧是一片毫无裂痕的温和。
半晌,才听他道:“母妃乃是父皇后宫,张大人所请,本宫答允与否,都违了为人子的伦常。”
语罢,纳兰瑞的眼光却是落在了第二排的李由身上。李由低着头,却仿佛是一夜之间老了十数岁,单看背影,都觉他憔悴突然。
这道眼光平静而无锋芒,却叫人胆寒,御阶下的人,皆不能直视那一袭重紫锦袍的男子,明明是温润如玉的贤王,撕破外表后,这周身威仪,竟是连今上亦不能及。
无人瞧见纳兰瑞搭在龙椅上的手,暗暗使力,握成了拳。
“诸卿既然无事,那便散了吧。”
正在殿前兵马司班房里安排京中防务的苏岚,闻得太子传召,竟也愣了一瞬,才省过味来,如今东宫的位置,已经换了人坐。殿前兵马司的班房就在崇安宫墙之下,此时仍是血腥味未散,才出了屋子,苏岚便觉脸上一片湿意,竟是下起雨来,那血腥味被裹在泥土的气息之中,竟有几分难得的清新。
自己撑起天青色二十四骨油纸伞,苏岚沿着宫道缓步随着内侍往内宫而去,才过了太和殿西侧三省班房,就瞧见前头一个人。他一袭黑衣,在素色伞下,由着身后人撑伞,缓步而行,风姿卓越。
“京中大安了?”苏岚执伞向前,玄汐亦是难得笑着点了点头,素色伞下一袭黑衣,显得挺拔而冷清,禁欲之外却是惑人。
“嗯。”玄汐接过身后人手中的伞,与苏岚并肩而行,“你我如今也能在宫中自在地说句话了。”
苏岚在伞下侧身看他,他冷若冰霜的脸上难得挂起笑意,虽淡如烟尘,依旧惑人。
“余党如何处置?”
御书房就在眼前,玄汐止步不前,道,“骤变求稳,方是上策。”
“我只知,不论九世家内里被掏成了何等样子。这个九,都不可动摇。”
“张澎有个庶出的弟弟,年十九。幼时早慧,据说颇得他爹的喜爱。七岁那年,被只畜生吓到,从树上跌了下来,摔断了腿。从此,张家这个庶子,无人问津。”玄汐的声音夹杂着雨声落在苏岚耳畔,苏岚本是微垂着头,站立原地,却被逼着回头看他。
“张澎本就是你的替死鬼。”苏岚略有些无奈地笑了笑,“张家如何摆弄,我家老爷子是不管的。”
“可我不能不管,这人难道不是你选出来的?”
“难道,不合你心意?”
“恰恰相反,我颇为欢喜。”
第二十八章 江山谁主(二)()
苏岚踏进御书房里,纳兰瑞正低头翻着折子,见她欲行礼,只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待得坐定,苏岚微微一笑,道:“方才瞧着殿外还等着一溜的人,殿下还能想着我,真是受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