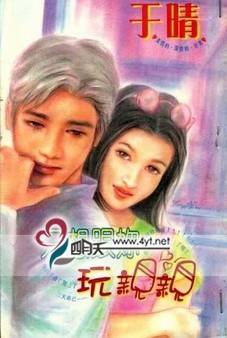光荣与梦想-第18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家庭正常供应的必需品而外,用在商品和劳务”的共达五百五十五元。
有很多行业全部改组来满足这些青年的需要。唱片业给他们准备了两种唱片:“单张唱片”(每分钟四十五转)是给未到一岁的小孩的。“唱片集”(每分钟三十三转半)是给青少年的。这两种凑在一起,就占全美国唱片销售量百分之四十三。青少年的消费额,占电影院票房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照相机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四,新收音机销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九,新汽车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岁至十九岁这部分的青年,每年在唇膏上花二千万元,在狐臭粉上花了二千五百万元,在家庭烫发上花了九百万元。男女青少年花在化装用品上几达三亿多元。
在严酷的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父母亲们,看见十二岁的女儿每周都去美容院,看见十四岁的孩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保险公司为他们那一代承保的退休保险的小册子,现在开始习惯起来了。这些年青的一代,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设一些赊帐户,它们用的是颇为诱人的名字,如“十四到廿一岁的俱乐部”,“校园帐户”,“新星帐户”等,都没有赊借两字的。他们还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打个公主牌电话要人送来商品,或者和男朋友或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每只十二元玖角伍分,“不用付现,每周付五角”)。加州有个公司建了一个造价二百五十万元的青少年商业中心,内有六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滑冰池和一所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沃尔特·狄斯奈在儿童们中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狂热,这对全国说明,对这些小消费者也是可以招徕生意的。“狄斯奈游乐场”本来是星期三晚电视的重要节目,有四千万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那周的节日,第一次连播关于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的人物。——译者】的故事。戴维由一个迄今还是寂寂无闻的二十九岁的演员费斯·帕克扮演,确是个风度迷人的主角。他那种随和态度很易使小朋友们陶醉,所以那些贩卖克罗克特纪念品的人很易使他们上钩。接着那年的春天,各个游乐场和超级市场似乎到处都是那些戴着浣熊皮帽的五岁小孩。浣熊皮的价钱一下子上升为每八元一磅。到了下年夏天,这个销售高潮才结束,但浣熊皮已销售了一亿元,而戴维·克罗克特式的汗衫、雪橇、毯子、风雪衣、牙刷、午饭盒、秋千、儿童游乐室、沙箱玩具、小凳子、玩具枪和自行车,还未计算在内。有个商人积存有二十万个学生帐篷,印上了戴维·克罗克特的名字,在两天内就把它卖光了。有些成年人实在忍无可忍。有个百货公司迸货员说,“再有人对我谈论戴维·克罗克特,我就用克罗克特的枪迎头给他一下。”在听了上千遍的费斯·帕克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以后,很少有哪个母亲不掩着自己耳朵的。这支歌独占歌坛六个月,一共销售了四百万张。
『生在田纳西的一个山顶上,
这个自由乐土的最葱绿之州,
在森林中长大,他熟知一草一木,
三岁上他就杀死了一只狗熊。
戴维·克罗克特呀,戴维
他是蛮荒世界之王!』
※※※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年们造成精神上的残害。在这方面,1954年开始有两种娱乐形式,确是使人不安。比尔·哈莱和彗星乐队的新音乐在广告上被宣传为“最优秀的摇滚舞流行音乐”。它使人担心在这新繁荣中长大的儿童,就象二十年代的儿童一样,可能被引向一味追寻欢乐,没有头脑。除此以外,斯坦利·克雷默的影片“凶暴的人”还加上了未来野蛮暴力流行的征兆。马龙·布兰多扮演主角约翰尼,是个毫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猩猩一般的“主席”。这些俱乐部成员都穿上紧身的蓝布裤,上身穿着黑皮茄克衫,背上漆上一个骷髅头和交叉着的大腿骨。按照电影的情节,布兰多这一伙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下午,冲进一个宁静的小城,由于没有事做,便把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显然,这电影是要揭露批判某些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是谴责那些青年吗?是谴责听之任之的态度吗?是谴责对法律和治安的不尊重吗?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克雷默要暴露的是战后富裕生活的阴暗的一面,是毫无节制的贪得无厌。有些人见到电影里的暴行有反感——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时代里,那是够粗暴的了——他们认为那样来进行社会批评未免太过分了。
有一小批年青的波希米派,他们认为对物质至上主义无论怎样指责,都不会是过分的。他们认为富裕生活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和它搏斗过,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承认被击垮了,或者说得更简洁一点,就是垮了。这个“疲塌”的一代在五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市下等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褪色的广告板和灰泥剥落的墙头后面的。这个运动在那里的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酝酿成长,然后往北一跳三百五十英里,在旧全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它的圣地。那就是那个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出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在巴黎出生的满面胡子的劳伦斯·弗林格蒂。他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杂志当过送信员,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得过学位。1953年他和彼得·马丁合办了这个书店,成为美国第一家全部供应平装本的书店。弗林格蒂用卓别林的电影名字给这个书店起了名。扩大以后,他又办了“城市之光丛书”,这是一家出版社。列在该店出版书目的诗人中,第一个就是他本人。他的诗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发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弹劾的宴会的初描》,这就可以使人大约知道他和五十年代的一般商人有多大的不同了。
“城市之光书店”还充作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讯地址。这些人不同寻常,即使是在本行中间也是如此。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科尔索的人曾在1946年披捕,因为他和同伙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把纽约市夺过来。逮捕他时,他还拿着步话机统一指挥这些抢劫。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哈佛大学的“扩大眼界图书馆”里自学,写了一些象《结婚》那样的诗。诗中他对一个要和他的未婚妻度过一个晚上的青年说:
『不要带她到电影场,要带她到坟场,
对她讲狼人的浴缸,和校正了的单簧管
然后向她下手,吻她,如此等等
我知道为什么她没发脾气,而她甚至会对你这样说:
你摸吧!摸着很舒服呢!』
“疲塌”派的作者的年龄属于摇曳舞的一代,但他们则认为己经不是了。作为社会预言家,他们主张自发表现、旅行、东方的神秘主义、唱民歌、弹吉他、跳勃鲁斯舞、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和他们所谓美国的梦想。有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在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克鲁瓦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一些评论员认为他和其他新复兴时代的作家是消极的,他驳斥这种说法。他肯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极其积极的。本·赫克特在电视里问他,为什么不多写一点“这个国家有什么毛病”呢?克鲁瓦克后来写道:
『他要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我说反对人民的心里话。他轻蔑地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和所有这一类的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东西说话,为了十字架,我会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会说话……为了可爱的穆罕默德,我会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会说话,为了支持D。T。铃木,我会说话。为什么我要攻击我在生命里所热爱的东西昵。这就是“疲塌”派。活下去活到死的一天么?不,是爱生活爱到我们死的一天。到了他们要来象处死耶稣那样用石头把你扔死的时候,至少你没有温室,你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身躯而己。』
他的《在路上》只写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完全不是写作,而是简单地把字打出来罢了!”但是他把人们想听到的东西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买了五十万册。这本书谈情说爱的情节是索然无味的,书中人物的眼界是浅薄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东来西去到处探索,他们似乎总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似乎什么都探索不到,甚至自己是什么也弄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他要说的吧。起码克鲁瓦克眼中的人们总是张开眼睛,而不是被家里的物质世界把他们围着。“疲塌”派的人是真诚的,他们对他们那一代的毫无生气的生活不满。比克鲁瓦克写得更为有力的艾伦·金斯伯格对冷战问题,是用摧枯拉朽的气慨写的。
『美国呀你并不是真想打仗。
美国呀,就是那些坏俄国人、
那些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
俄国人要把我们活活地吞下去。他们是权力狂。他们要
把我们车库里的车拿走。
他们要把芝加哥夺去,他们要搞一份《红色读者文摘》。他
们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放在西伯利亚。要由他们庞大的
官僚主义机构管理我们的加油站。
这不好。唔!他要使印第安人读书,要使黑鬼出名。啊,
他要我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救命啊!
美国呀,这是严重的。
美国呀,这就是我从电视机里看到的印象。
美国呀,我说的象不象?
我还是立即动手工作吧,
是的,我不想参军,或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车床,反正我
是近视的,是精神病患者,
美国,但我也要担负一份不寻常的责任。』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正神经错乱,但在进行了一年精神治疗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那是在1954年和1955年早期。它使他结束了初露头角的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病床以后,一口气写出了《吼叫》一书。旧金山警察认为内容淫秽,把它充公。但是法官认为这篇长诗还有“重要社会意义”,于是金斯伯格和克鲁瓦克,科索,弗林格蒂都成了这个“疲塌”派的宇宙里的红星了。
这些人一出现,那些一本正经的祟拜他们的人就想把他们圣洁化。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爱和克鲁瓦克的不道德,都视若无睹。他们说,beat(疲塌)就是“beatitude”(耶稣“登山训诲”【圣经中重要一段,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十二节。——译者】的福音)的缩写,所以这些诗人都是受到上帝赐福的。这些“疲塌”派被惹得大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们的工作有无内在价值(其实多半也是价值不多的),但他们使人们对那种不加思索地随俗从流的习气有所怀疑,这样,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社会目的。不承认他们这一成就,就使他们成了文坛的阉人。但当时不大可能。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们还继续引起热烈的反应。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运动唯一的奇怪之点,就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