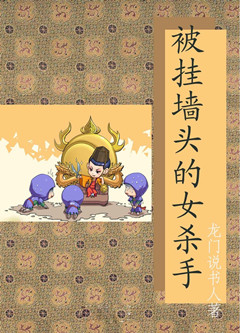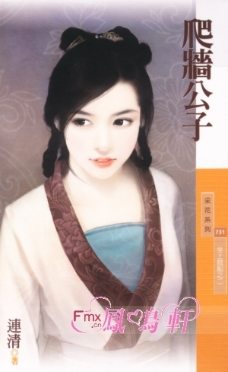烂泥糊上墙-第7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阅敲挥邪楹罂孔徘浊樽呦氯サ钠降睢!�
见张扬不吭声,林小雨肯定他是没有想过的,有些头疼还是耐着性子解释,像是开导一个无理取闹的小朋友,“你的事业呢?你想过没有?多少人对你的位置虎视眈眈呢,巴不得你立刻爆出任何新闻好把你踩在脚底。我知道你这一路走得虽然算是顺畅,可说没有付出努力是肯定不会的,在最好的上升期又跌入谷底,你甘心吗?”
“我不在乎。”张扬梗着口气说。
林小雨把他的手拿开,“你的不在乎能有几年呢?如果以后你说你在乎了,我要怎么办呢?”林小雨说,“张扬,我是个女人,我能力有限能保证住女儿和我的生活已经很辛苦,我不能保证也承担不起,你有朝一日的后悔。”
“郑驰文就可以?”张扬幼稚的问,像个赌气的孩子。
“不是他也可能是别人。”林小雨说,“我累了,已经过了非谁不可的年龄,生活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许细温的嘴巴张了张,没有把那个答案说出口。
她看着郝添颂,静了静,“张扬说你走了,怎么没走?”
郝添颂说,“我明天早上离开,张扬可能向你们转述错误。”
他的意思是,他不是故意等在这里的?
郝添颂的解释,让许细温如鲠在喉,其实他不用说那么多的。
“我们后天离开,明天还有个杂志要拍。”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网上。”郝添颂解释,“因为节目,你和张扬人气十分高,关于你的行程安排有很多报道。”
“工作谈完了?”许细温环视房间一周,“怎么没见你其他的同事?”
“工作是在另外一个城市谈的,经过这里我顺便来看看,他们已经回去。”
“郝添颂。”许细温突然叫他的名字。
郝添颂抬头看她,“嗯?”
“你累不累?”
“”郝添颂想了想,“不累,我晚上睡得一向晚,你累了吗?”
“这么说话,你不累吗?”
“”
许细温说,“每句话都要解释,让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聊天,而是在汇报工作。”
郝添颂说,“如果你不想听,我就不解释了。”
“你真的是路过吗?”
“是。”
“你们是从哪个城市过来的,怎么会刚好路过这里?”许细温又问,“又是在我来的这几天。”
“巧合而已。”郝添颂蹙眉,他坐直身体。
“你对网上传的关于我的行程都那么了解,会不知道我要来这里拍节目吗?”
面对许细温的连续追问,郝添颂如临大敌一般正襟危坐,“我没有其他的意图,也并没有打扰和纠缠你的意思。”他停了停,保证,“我以后都不会再给你造成困扰了。”
“其实,你说专门来看我的,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许细温嘀嘀咕咕抱怨。
郝添颂有些吃惊地看着她,又认真想了想她的话,理解错了,苦笑着说,“以前是我做的不对,自己陷在过去里走不出来还非要拉着你一起,想必给你造成不少的麻烦,以后,不会了。”
许细温有些无语,他们的沟通障碍是有多么严重,才会让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都能产生歧义,让郝添颂以为是她不满又无奈的吐槽。
“我不是那个意思”
“”郝添颂看着许细温,等着她说。
许细温又摆了摆手,“算了。”
42 许细温()
平时,是郝添慨给郝添颂擦拭身体。
今天,是许细温给郝添颂擦拭手掌。
郝添颂情绪低落,懒洋洋地靠在枕头上,眼睛不知道看在哪里,看得十分认真。
“明天是晴天,你想不想出去走走?”许细温低头,没看他的脸。
郝添颂摇头,“不去,累。”
“总在房间里躺着不好,出去走走好不好,我推着你。”许细温继续鼓动他。
郝添颂还是摇头,“人多,不去。”
“不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去远点的地方,一日游。”
郝添颂动了动手指头,“手不脏,不用擦了。”
“明天去吧?”许细温再接再厉,劝说。
郝添颂还是两个字,“不去。”
第二天,是大晴天,郝添颂睡了将近一整天,或许他清醒过,可他没睁开眼睛。
相比较骨折的四肢和腰椎,郝添颂表现得都很淡定,以为只是忍受疼痛而已就能好起来,可腰椎脱位带来的其他功能影响,彻底摧毁了他的自信心和希望,他不可能好起来了。
接下来几天,郝添颂不怎么吃饭,水很少喝,整个人迅速的瘦下去。
而郝添慨,归期未定期,许细温不知道该找谁商量,急得团团转。
许细温找过医生,医生却表示爱莫能助,“这样下去,郝先生会患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郝添颂,两个词语联系在一起,让许细温久久的手脚麻木冰凉。
如果那天,郝添颂不管她,一定会比现在好。
一个星期,郝添慨没有回来,郝添颂却是不得不洗澡的。
郝添颂胳膊和腿上绑着石膏,不能用花洒洗澡,平时都是用盆子接了热水,擦拭全身。
许细温在热水里掺了些凉水,她试过水温,只是稍微热一些,可毛巾落在郝添颂的腿上时候,他瑟缩了一下,可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摊手摊脚,任由人摆布。
石膏已经绑了将近一个月,虽然现在天气不算热,可里面还是闷得厉害,泛红。
许细温溜着石膏边缘,仔细擦拭,从小腿到大腿,再往上。
他有几天没洗澡,身上有些脏,许细温只是轻轻擦,还是搓起来一层污垢。她把毛巾湿了些,想把污垢擦拭下来,水却顺着流,她手忙脚乱去擦,就碰到不该触碰的。
“我去拿干毛巾。”许细温急着说。
她以为郝添颂是闭着眼睛的,不会回应她的话。
可她抬头,对上他的眼睛。
她的心脏突地一疼。
郝添颂低头看着软踏踏的一团,目光沉静,毫无波澜,可就是这份安静让人心惊,他的声音轻飘飘的,“你碰它都没反应了,我是真的废了。”
“我去拿毛巾。”不敢再看,许细温立刻转身出门。
许细温毛巾拿了三五分钟,回到房间,郝添颂正抬手解手臂上的石膏。
“还要几天才能拆。”许细温丢下毛巾,去阻止他。
左边比右边严重,郝添颂就用包着纱布的右手,拽左边手臂上的石膏,太长时间没有活动,动起来格外的疼痛,他咬牙忍住,撕开纱布拿下石膏夹板,扔在地上,又去拿腿上的。
“郝添颂你别这样,会落后遗症的。”许细温捡了石膏,往他手臂上安装。
郝添颂忍着疼痛,推开她,没什么力气只是轻轻的,“我他妈的都这样了,多这一点后遗症又有什么。”
许细温站着不说话,看着他像只困兽一样咆哮着,看着他拖着半掉着的石膏,在房间里把桌上的东西一挥而下。从受伤,郝添颂一直在忍,可今晚上,他的尊严和自信心,彻底碎成了渣渣,他还要什么理智。
放在凳子上的水盆,因为碍事,被他扬手推开。
水珠漫天撒开,一半落在许细温身上。
郝添颂双手捧头,他埋在手掌里呜咽出声,“我废了我废了。”
许细温第一次见他这样,平时里多么嚣张跋扈的人,无助的时候,越发显得可怜。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郝添颂一个人的声音,他的哭声和自言自语的声音。
比较下,许细温的呼吸声都变得轻起来。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郝添颂毁了,毁在她手里了。
因为她,从前那个自信张扬好面子的郝添颂,像个孩子一样,在她面前失声痛哭。
他的一辈子毁了,她该怎么偿还他。
如果他落入地狱,她是不是该陪着承受同样的煎熬。
许细温的手背上落过水珠,已经掉在地上,留下一条痕迹。
白皙、匀称的手指,颤抖着,抬起,捏着衣领处的透明扣子,穿过去,解开。
动作反复,一直到最后一颗。
许细温光脚,踩在满是水的地板上,她走得小心翼翼,却坚定地走到郝添颂面前。
她张开双臂,拥抱住他。
怀抱里的人浑身僵硬,剧烈地推她。
她虽是女人,却是健康的,郝添颂是男人,可他受伤了。他用受伤的手臂根本阻挡不住许执着的许细温,只能被她像个孩子一样抱着,亲吻他的脖颈和后背。
郝添颂承认,他对许细温还存有特殊的感情,不然不会,在大脑判断出来她有危险的时候,奋不顾身去救她,而忘记会给自己招惹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他还有特殊感情的许细温,抱着他,亲着他。
“细细,看着我。”郝添颂挣扎着站起来,捏住许细温的手腕,控着一个劲往他身上凑的许细温。
许细温低着头,偏不看他,身体却在努力靠近。
他不肯,她急得浑身是湿漉漉的,不知道是刚才的水,还是出的汗。
“细细,不要同情我。”郝添颂痛苦地说,扯起床上的床单,包着她。
许细温四处闪躲着,趁着郝添颂站不稳,把他往后一推,她压上来,吻上他的唇。仓促的、忙碌的、不得章法的。
“就算是同情,我也要。”
这场耗时耗力的活动,很久后才结束,许细温捂着嘴巴从床上跳下来,跑进洗手间,呕吐不止。
不想让郝添颂听到,把水龙头打开,终于遮盖住呕吐声。
鼻涕、眼泪活着口水,糊了一脸,许细温坐在花洒下面,咬着手背,哭得压抑和委屈。
很久后,许细温才从洗手间出来,衣服还在地上,她捡起来要回自己的房间。
以为睡着的郝添颂却说,“细细,不要走。”
许细温捏着衣服的手发白,还是丢在地上,走到另外一侧,躺下。
可她浑身发抖,躺下很久还是在抖。
躺在一张床上的郝添颂,肯定能感觉到,可他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在天空泛着鱼肚白时,郝添颂困难地挪过来,用受伤的手臂搭在许细温的肩膀上,准确地摸到她的眼睛,用暖热的手心,轻轻盖住她的眼睛。
“细细,对不起。”
在别人要么叫她全名,要么叫她“温温”的时候,只有他固执地叫她“细细”,而且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叫过。
那天晚上,对两个人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许细温没有再回自己的房间,她住在郝添颂的房间。
郝添慨回来后,看到大吃一惊,可看那两个人还是过去的相处方式,他就把好奇心放回了肚子里,因为郝添颂的状态好转很多。
的确,郝添颂配合治疗,医生说的他完全做到,坚持康复训练,整个人又恢复了过去的光彩。
像被乌云笼罩住的太阳,再次光芒万丈。
八个月,过得也没那么慢。
所有人都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察觉出来哪里不正常。
郝添慨望望在厨房里做早饭的许细温,搬着凳子悄悄往郝添颂旁边挪,“你和许细温吵架了?”
郝添颂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