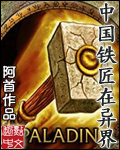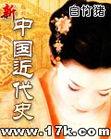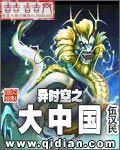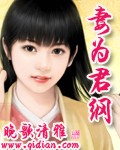中国人史纲-第10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磕甏合闹唬迨斓牧革鳎搅降劳背龇ⅲ蚝犹咨ǖ矗偕漳敛莺兔晒湃嘶娴牧甘场C磕耆绱耍曛螅腥吮患⒍鏊龋挥型顺龊犹祝缓缶驮谝跎礁坪又洌拗碌姆老撸梢砸焕陀酪荩⑶沂雇聊夭坑泻蠊酥牵桓叶�
朱厚囗被这个雄壮的建议大大地感动,立即交给国防部作进一步的研究,当国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见时,朱厚囗大发雷霆,下谕旨说:“敌人盘据河套,为中国边患已久,连年破关入侵,使我日夜不安,而边疆将领中从没有一个人为我分忧。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规模壮伟,国防部为什么迟疑不决,拿不出主意?”下令先发给曾铣白银二十万两调度使用。曾铣深庆他遇到盖世英主,积极准备。
但是,没有人对疯狗能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忽然发作咬人,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暴君亦然。事情突然变化,首席宰相(中极殿大学士)夏吉,全力赞助曾铣。而次席宰相(建极殿大学士)严嵩,则正积极排除夏言,河套战略正供给他攻击夏吉的工具。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理由,只知道严嵩和宦官勾结,在宫廷中秘密下手,终于使朱厚囗作一百八十度改变。一五四八年,当国防部把实施攻击的详细作业拟妥,而且刚刚呈请批准时,朱厚囗忽然下了一道谕旨说:“驱逐河套的敌人,出兵是不是有名?粮秣是不是够用?胜利是不是有把握?曾铣一个人不可惜,而人民受到荼毒,谁负责任?”这是一种当权人物翻脸时特有的口吻——中国人称之为“官腔”,官腔一出,已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了,全体官员大为惊愕,严嵩立即公开反对擅开边衅。于是,曾铣、夏言全被处斩。
土默特部酋长俺答,不因朱厚囗的昏聩而心肠软化,明年(一五四九),俺答直抵大同、永宁(北京延庆)一带,大掠而去。又明年(一五五○),攻陷古北口(北京密云东北),破长城而入,包围北京。这是上世纪(十五)也先可汗围城后,北京再次被围,两次相距恰恰一百年。朱厚囗惊恐过度,把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丁汝夔杀掉泄愤。但他不承认杀错了曾铣,反而坚称这正是曾铣妄图开边,激起敌人的报复。
北京好容易解围,俺答杀够了中国人,抢够了中国人的财产之后,满载而归。但北中国全部暴露在这个蒙古部落的铁蹄之下,万里长城在腐败的边防军手中,已不发生作用。俺答几乎每年都要攻破长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边防军将领们无可奈何,唯有把逃难的一些难民,提来杀掉,当作杀敌报功——其中有多少使人伤心落泪的事迹。然而,俺答年纪渐老,而且他和他的部落人民,都信奉了从西藏传过来的喇嘛教。开始厌倦战斗。七十年代时,又发生了一件桃色事件。遂使他们永无休止的侵略,蓦然结束。
桃色事件的男主角就是俺答,女主角是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三娘子美丽绝伦,身为外祖父的老混蛋俺答却把她纳为姬妾。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应,跟俺答理论,俺答没有办法,只好把孙儿把汉那古的未婚妻,改嫁给三娘子的未婚夫。现在轮到把汉那吉恼火了,他说:“这算什么话,外祖父娶外孙女,祖父把孙儿媳妇送给别人。”就率领他的家人,逃到中国。边将们痛恨俺答,一致要求杀掉把汉那吉,幸而大同总督王崇古有政治头脑,坚持予以保护,又请中央政府委派把汉那吉一个中级军官(指挥使)的职位。
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孙儿被中国杀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闹咒骂,这个老混蛋在头脑清醒时还是有理性的,他既懊悔又惭愧,于是率领十万人的强大兵团,越过边界二直指大同,准备在发现中国杀了他的孙儿后,即发动攻击。王崇古知道他的用意,派人前去谈判和解,保证他的孙儿还结结实实地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亲信到大同窥探,看见把汉那吉穿着中国军官的制服,正在那儿骑马取乐。俺答惊喜说:“中国竟没有杀我孙儿,我从此也不再攻打中国。”
中国北方的外患,就这样戏剧性的停止。
俺答死后,三娘子掌握大权。她不但美丽,而且极有才干和见识,她发现跟中国和解,接受中国的封号所得到的赏赐,要比劫掠得到的还要多,所以她始终臣服中国,作为中国的屏藩。本世纪(十六)最后三十年,以及下世纪(十七)初叶,三娘子在世期间,两国边界保持一段长期的和平。
七 张居正的改革与惨败
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带给中国半个世纪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国人照例松一口气,由他的儿子朱载垕继任。朱载垕在位七年,于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岁儿子朱诩钧继任。
当朱载垕刚死,朱诩钧还没有登极时,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张居正,争斗激烈。张居正跟宦官巨头——司礼太监冯保勾结,利用主少国疑,千载难逢的机会,由冯保设下网罗,向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告密说:“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扬言:十岁的孩子,怎么能担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个白痴,也不敢公开讲这种杀身灭族的话,但在官场倾轧中,问题不在他讲不讲,只要有人坚持他讲就够了,李太后颜色大变,立即把高拱免职,擢升张居正为首席宰相。
张居正使用的显然是一种不尊严的手段,但不能责备他,明王朝三百年间,所有高级官员都必须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数人敢跟宦官对抗,但不是死于诏狱,便是死于穷困。
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更没有触及到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过像一个只锯箭杆的外科医生一样,只对外在的已废弛了的纪律,加以整饬。
主要的措施在于加强行政效率,下级官员必须对中央命令彻底执行,不能敷衍了事。张居正屡次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赋税,使负担过多的穷人减少负担,使逃税的“乡绅”纳税。又大举裁减不必要的官员,缩小若干机关的编制。最有成绩的是,张居正任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守御北方边疆。
当戚继光调任蓟辽兵团司令官(蓟辽总兵)时,准许他率领一手训练的击败倭寇的浙江部队。到任后的某一天,举行阅兵,忽然大雨倾盆,边防军竟一哄而散,只有浙江部队因没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动,边防军大吃一惊,从此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令。这件事说明边防军的腐败(现在我们可以了解万里长城所以抵挡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张居正所以进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们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是反对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纪(十六),正是大黑暗时代,对改革的反对当然更加强烈。张居正所作的这种外科医生的手术,严格地说还谈不到改革(更谈不到高一级的变法了),只不过稍为认真办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对,却同样可怕。一是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如被裁减的人员,被增加田赋的“乡绅”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习惯性的反对,儒书上“利不十,不变法”,已成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张居正又因为父亲亡故的守丧问题,触犯了儒家的礼教。
张居正的父亲于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礼教的规定,作儿子的必须辞去官职,回到故乡守丧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权下令征召守丧中的儿子继续供职。皇帝朱翊钧倒是下令征召张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员的喧哗,一种是卫道之士,他们认为纵然有皇帝的征召,但儒家正统思想不能违犯,不守父母三年之丧,跟禽兽没有两样。另一种是锐进之士,希望张居正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这场争执虽没有大礼议事件那么死伤狼藉,但也热闹了一阵。使张居正的仇人布满天下。
张居正当权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钧已二十岁,蛇蝎性格随着他年龄的成长而大量显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时对他生活管教过严的宦官冯保和在他幼年时对他读书要求过严的张居正。
朱诩钧十岁时,就经常拷打身边的宦官和宫女,把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拷打到死。冯保向李太后报告,李太后就责骂朱翊钧,有时候还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罢黜的后果。至于张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师,往往在朱翊钧早睡正甜时,强迫他起床读书。在他读错字时,又声色俱厉地纠正他。
朱翊钧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立即向他们采取报复行动,任命冯保的死敌张减当司礼太监,把冯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布张居正的罪状,下令抄没他的家产。张居正是荆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员在谄媚奉承宰相之家十余年后,为了表示对新当权派的忠贞和对“罪犯”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得到正式命令,一听到风声,就派兵把张居正家团团围住,门户加锁,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员张诚到达时,已有十余人活活饿死。
张居正的失败是注定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绝不允许他成功。他失败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渐化为乌有。一切恢复原状,黄河照旧泛滥,戚继光被逐,边防军腐败如故,守旧的士大夫、乡绅、宦官,一个个额手称庆。
八 第一次保卫朝鲜
张居正死后不久,日本大举侵略朝鲜王国,中国第一次武装援助朝鲜。
朝鲜王国和安南王国,是中国南北两个最忠实的藩属,他们除了有一位国王和使用一种跟中国大同小异的文字外,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省。中国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宗主国,但从不过问他们的内政。
日本帝国在本世纪(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
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对于文化落后的蕞尔小国,竟敢动高度文化大国的脑筋,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团于翌年(一五九一)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日公)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九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
——判断,是人类最高智慧的表现。判断如果错误,就必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小焉者是个人的失败,大焉者是国家受到伤害,甚至灭亡。对同一现象,竟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事实上有时候还产生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断),跟当事人的智慧见解,生活体验,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