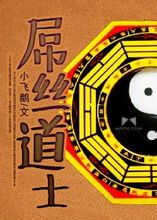南山道士诡谈-第27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发出了微弱的银光,熠熠生辉。这是他第一次在接这种小单时主动运用巫力,也是第一次没怎么使用腥盘的手段,实打实的做这一局。
有了“亲身体验”,桑于桥对于两位大师更是毕恭毕敬,恨不得请对方把自家整个看一遍,最好能把风水全部调整一下才好。然而魏阳的指点却相当有限,只是在几个屋里大致看过,让他把之前那位同行搞出来的幺蛾子统统撤掉,其他别说是法器了,就连家具位置都没改动。
这简直都跟空入宝山一样了,难不成是两位大师还生着气?心里忐忑难安,桑于桥小心翼翼的赔笑道:“魏大师,实在是我太怠慢了,招待不周啊。只是家里人心惶惶,又受了这么多罪,您看能不能再帮忙看看,咨询费什么的绝对不会少……”
魏阳却风轻云淡的摆了摆手手:“已经有了墨玉佛,还是你亲手供养的,放其他东西反而会冲突。只要好好供奉佛像,绝对要强过寻常法器。”
这话桑于桥是真心**听,本来那博古架还让他心中惴惴,但是能得个法器绝对是大大得补偿了,他立刻追问道:“那供养法器有没什么讲究?需要上香吗?”
魏阳一笑:“佛像嘛,自然还是要诵经供奉的,正好这尊是除秽金刚法相,不如就从除秽金刚咒入手,不过跟其他佛教经典一样,还是需心诚方能有效。其实这次也是机缘巧合,如果雕刻的不是除秽金刚,说不好还无法这么立竿见影的克制百家佛。”
这也是除秽金刚的特性之一,任何地方都可以施展,除秽为净,无所禁忌。虽然不太了解佛法,但是桑于桥好歹也是个文化人,自然也查过一些关于除秽金刚的资料,听到这话不由大点其头。魏阳却像是对这里没了兴趣,随意又敷衍了两句,就对黑皮说道:“明哥,晚上定的是几点的火车呢?”
黑皮可是一直看着呢,当然知道魏阳耍的是什么花招,硬货已经摆出来了,没有再上赶着做买卖的,退后一步、欲擒故纵才是真正行家的手法。配合的笑了笑,他立刻对桑于桥说道:“桑先生,这边已经处理完了,我们晚上是真有事,就先告辞了。”
其实这话是有点失礼的,但是落在桑于桥耳朵里,又觉得格外有分量,看看人家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当天的,这得对自己多有把握才行啊?为难了自己这么多天的遭祸,不过是对方顺手施为的事情,这样的大师不结交才叫真的傻了。虽然不敢真的拦人,桑于桥还是说了一堆的好话,连带对黑皮的态度也更谦恭了几分,还专门开车把人送到了高铁站,虽然一路上没敢谈钱,但是这报酬,想也不会少了去。
(本章完)
第334章 过路阴阳()
? 直到火车驶出了车站,黑皮才啧了一声:“还真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搞,天衣无缝啊,只是那玉佛给他实在太可惜了……”
现在黑皮还以为刚刚是两人在演双簧呢,别说,小天师让魏阳上那一步简直堪称绝妙,小神棍的演技也可圈可点,几句话说的他寒毛都竖起来了,这么一配合,叠加效果也就成倍了,比一个光说一个光练的档次可就上去不少。
魏阳笑了笑,也没解释,反而略带调侃的说道:“玉佛给了才更好啊,打广告不也要花钱?只要桑先生的事情传出去了,还怕阿曲接不到单吗?”
黑皮哪会不懂,只是嘴皮子上过过干瘾罢了,不过眼珠转了一圈,他又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事你们也先别跟小曲儿透底啊,否则这货尾巴又不知翘的有多高。难得老实几天,也让咱这一家子好好安生一段才是。不过说回来,他雕的东西真的有用?有气运之类的东西?”
“万物有灵嘛,这种凝聚了心血的东西的确更容易带上创作者的生机,所以法器多是大师才能做出,这点明哥你可以放心,阿曲以后绝对会成为真正的名家。”虽然听起来像是吹捧,但是魏阳说的也未尝不是实话,毕竟能让齐哥说出“有气运”的东西可没几件,而柳曲的玉雕绝对算是其中之一,同时玉本身就能通灵,如此叠加,当然不同凡响。
马屁拍得恰到好处,黑皮心里顿时就乐开了花,面上还勉强维持着矜持,呵呵谦虚道:“也算家里没白养这个小混蛋,阿阳你也放心,这次姓桑的不会少给钱的,到时候我都给转你帐上,只是以后要是在遇到了什么事,你们界水斋可不能推啊。”
“那是自然。”魏阳笑着答道,但是笑容里多了一点心不在焉。从刚刚开始,他的心思就已经落在了身边人身上,虽然黑皮和桑于桥都没看出来,但是他却不可能不知道今天事情的蹊跷,是什么让他家齐哥突然转了口风,他还真好奇的紧呢。
有一阵没一阵的又闲聊了会儿,黑皮看了眼已经闭上眼一句话不吭的张修齐,和目光频频往那边飘的魏阳,干咳了一声,借口尿遁去了。本来的三人座立刻就只剩下两人,魏阳笑了笑,头一歪就凑到了邻座,在张修齐耳边轻轻说道:“齐哥,你是不是又瞒我什么了?”
张修齐睁开了双眼,看了过来,虽然一直没有说话,但是他非常清楚魏阳盯了他有多长时间,也知道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只是有些事情,他现在依旧还没有下定决心。沉默了有那么一会儿,张修齐开口了:“今早舅舅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些事情。”
魏阳可有点没有想到这个,但是他的反应不慢,立刻就皱起了眉头:“你又要擅自决定什么了事情吗?舅舅到底说了什么?”
没有人比魏阳更加清楚身边人的本质。虽然看上去面无表情又少言寡语,但是张修齐骨子里是个善良且温柔的人,幼年的经历让他失去了大半人生,也让他更在乎如今拥有的一切,只是拙于言行,他更倾向于把所有心事都闷在肚里,独自承担,就像上次的不告而别。如果换个人,恐怕早就被这别扭的锯嘴葫芦气死了,或者撒手放人离开,但是魏阳不是那些人。
看着身旁人一脸的紧张,张修齐摇了摇头:“不是你想的那样,舅舅只是跟我说,想把母亲当年用过的东西给你。”
魏阳不由一怔,嘴上立刻结巴起来:“你,你母亲的东西?”
“嗯,一个她自用的罗盘,还有阴阳锁和卦书,从母亲去世后,舅舅就把这些收起来了,没让别人碰过。”张修齐轻轻拉住了魏阳的手腕,低声说道,“他想把这些都交给你。”
魏阳张了张嘴,没能说出话来,这跟他想的的确不太一样,曾先生怎么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呢?那可是上代过路阴阳留下的宝贝,别说是曾家了,就算是三僚六姓也不会放手吧?他只是个神棍,又哪里配用这些。然而抓着他的手温热有力,并没有让他逃脱的意思,魏阳突然就明白了过来,也许并没有答应下来,但是张修齐已经意动了,才会在桑家让他看那个博古架,才会退开一步,让他掌握更多的巫血使用方法。不再紧守着曾经的执拗,他家齐哥确实开始放松了手指,开始尝试着想要克制自己的控制欲,想要与他商量,说出自己内心隐藏的东西。
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事情。
心脏砰砰跳的厉害,魏阳沉默了那么一小会,突然开口说道:“那可是你母亲留下来的东西,就算你走了龙虎山路线,肯定还是能用那些的……”
张修齐却打断了他:“我母亲去世的很早,据他们说,是因为窥破了天机,我其实并不太喜欢这些……”
“那现在你想让我用这些?”魏阳紧追不放,一双黑亮的眼眸直直的锁在那人身上。
张修齐嘴唇动了一下,最终还是说道:“那是我母亲用过的东西。”
就算他不会用,或者不希望他用,张修齐依旧也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他。魏阳听懂了那些言下之意,喉结轻轻一滚,把额头靠在了对方肩上:“齐哥,有时候你真让我发疯。答应舅舅吧,告诉他,我想用那些东西,想让上代过路阴阳的法器在我手中重现光彩,齐哥,我想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一个强到也能保护你的人。”
反手握住了那只骨节优美的手,魏阳摩挲着恋人的指尖,每一个字都力若千钧,他其实并没有想过那么远的事情,找回齐哥的天魂,除掉那个老怪物就让他十分满足了。但是现在,新的冲动代替了那些,他是真的想好好运用这些天赋了,当一个能够配得上那些法器的人,一个新的……过路阴阳?
张修齐的手指僵了那么一秒,旋即更紧的攥住了魏阳的手。有些话他拙于表达,但是同样有些话,不用语言也能传递。魏阳轻笑了一声:“当然,平时还是你来保护我好了,就像当年你的父母,或者什么时候,再送我一块龙虎山符玉?”
“我不清楚符玉是否跟你的巫血冲突……”张修齐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点犹豫。
魏阳马上就明白了过来,笑着挠了挠对方的掌心:“你还真想过我把封回去啊?不过应该不会了,如果龙虎山能克制巫血,恐怕早就没了巫族一脉。齐哥,不论是符玉还是那些法器,我都想要,一个都不能少。”
听着对方带笑的声音,张修齐最终也露出了点笑容,轻轻答了一个字:“好。”
随着话语,两人的唇再次贴到了一处。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公共场合,身边就是无数的旅客,可是两人并没有克制,那个吻既深且浓,悠长缠绵。从厕所回来的黑皮僵在了两步之外,心底冒出一串“卧槽”的咆哮,这两人神马时候搞到一起了?然而他还是识趣的停下了脚步,尴尬的摸了摸鼻子,转头又朝厕所走去。
车窗外,无数景色以300公里/小时的速度飞速后退,然而车里,两只手掌却紧紧相扣,犹如黏在了一起。阳春三月,花树繁茂,遍山浅翠,正是踏春野游的好时节。半山腰的凉亭里此刻也有几个人,或坐或站,然而神色却没有游玩的惬意。
“曾先生,这次实在是事关家父的毕生心愿,能否看在老人的份上,再出山一次?不论多少……”
话音未落,一旁留着山羊胡的老者已经按住了说话人的胳膊,摇了摇头,让他住嘴别提钱的事情。被这么一阻,那男人也想起对方上山前的交代了,不由暗自懊悔,只想扇自己的嘴巴子。这是什么地方?他那点臭钱能有什么用处。
然而还没等凉亭里的气氛僵住,坐在对面石椅上的人就轻笑了一声,缓缓答道:“杨叔,我已经封卦了,你也知道我的情况,这种事真的是帮不了。”
虽然被称作“先生”,但是那的确是个女人,长发披肩,一身浅蓝色的扎染布裙,面上毫无脂粉,肤色却白的惊人,只是已经没有了莹润的光泽,白有些发透,再加上瘦可见骨的单薄身材,似乎碰上一碰就会让她香消玉殒。
老人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静芸啊,小樊的父亲的确对三僚有恩,这事我们也考虑过了,能不能破例一次呢?”
“不能。”那女人回答的很轻,却干脆得很。
听到这话,一直站在一旁得西装男眉毛都怂了起来,冲那中年人叫道:“爸,三僚就没别人了吗?干嘛非要求这女人,反正她也……”
“你给我闭嘴!”男人大声呵斥道,打断了对方的无礼叫喊,额头上的油汗出了密密一层。
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