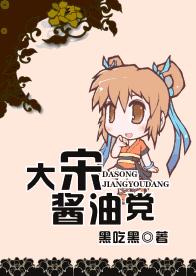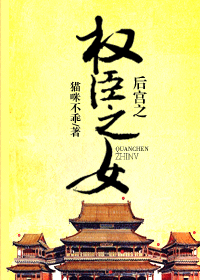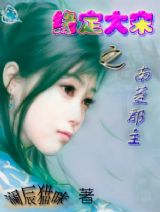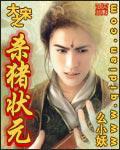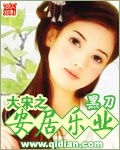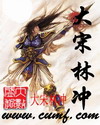大宋权臣-第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怜悯的心思淡了几分,忍不住说道:“伯父、世伯,小侄刚刚出宫,院子那边还没有照料,在此先行告退。”
眼看侄子有躲的意思,王旦老大不高兴,他是知道王璇对婚事的推脱,但景慕作为长者在座,他没有让王璇退下,王璇竟然开口要走,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下,当即冷然道:“今日,你世伯就在府中吃酒,你也在旁相陪。”
王璇听出王旦的不满,也觉得自己刚才有些过分,未来的泰山刚刚见面,就借口出去,实在让人臆想翩翩。
好在他反应快,立即说道:“小侄自要作陪,只是刚刚回来,想回去换一身衣服,总不能穿这身绯衣吧!”
“呵呵。”景慕见王璇的窘态,忍不住笑了笑,说道:“子明相公,就让贤契先回去,你看,在下来搅扰一番,还让子明相公麻烦,实在过意不去。”
王璇好不容易出来了,脑子里很乱,本来又能拖延婚期,应该松口气才是,但刚才纷乱忐忑的心情,不仅没有平静,反而越加沉重,终觉得好像要发生些事情。
当他又回到府邸,对王保说道:“明秀和上来了吗?”
王保脸色怪怪的,用很古怪的强调说道:“大师正在东院给孩子们讲德道经。”
“德道经?”王璇翻个白眼,不怀好意地一笑。在这些日子的接触中,他知道明秀的佛学造诣,远远低于道家甚至儒学,这和尚是标准的遁世士人。
“那我就不过去了,你去给和上说。午后,我过来给孩子们讲课。”
如果说明秀给孩子们灌输儒道之学,那他绝对是按自己的设想,去影响这些孩子。
第110章 郁闷()
王璇陪王旦、景慕二人吃酒,这才对景慕有所了解,自己未来的老泰山风骨硬朗,比王旦还要早两科的赐进士出身第一,谈吐间才华横溢,却一点也不迂腐。
更难能可贵的是,竟然还有一丝理想化的大同思想。
这个年代,士人言不离尧舜,口必说仙佛。实际上,他们压根就不抱任何大同思想,仅仅小康而已,至于神佛在他们眼中,也就是敬而远之,不能不让他感叹景慕的执着。
他们之间并没有谈论景影,景慕表现的也很洒脱,半醉之后飘然而去,完全不像一个六旬老人。
在送走了景慕之后,王璇难得与王旦在一起,他利用陪着王旦回书房的机会,边走便说道:“伯父,王太尉的大军,忽然勒兵不前,不知是何用意?”
他知道王旦的性子,并没有浪费时间拐弯抹角。
王旦的步履慢了下来,转首若有所思地瞥了王璇一眼,继而平淡地说道:“圣意,也是你等小辈能够揣摩的?”
王璇心中咯噔一下,立即听出王旦言外之意,看样子西北大军勒兵不前,果然有道道,而且限制在极小的圈子内,自己的身份是无法参与其中的。
王旦之言不过是对他的警告,不要多管闲事。
犹豫间,他轻轻叹了口气,大好的局面真的就放弃了?如果能一举消灭党项势力,自己所担忧的战马、侧翼安全问题将迎刃而解。
朝廷最高层显然形成共识,他无法理解,难道仅仅是为了陕西的民力,为了一时的重负?
如果那样的话,纵然他引起的蝶变,在不久的将来会付出百倍的代价,才能重塑今日的优势。
是不是再次抗上坚持?王璇已经没有底气了,完全是两码事。再说西北变局,他又不知道里面的猫腻,贸然介入,肯定逃不了好,一个不小心或许会满盘皆输。
“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和上,再过十年,不——十五年之内,我定要把党项给灭族。”王璇发狠了,他回到府邸面对明秀,几乎是发下了重誓。
“子正,杀心太重,难免坠入阿修罗道,天下本就一家,兼而统之,何必灭人后嗣。”明秀并不赞成王璇在恼怒中的誓言,他发出沉重的告诫语气。
王璇无可奈何地一笑,说道:“和上,难道你不明白?如今要是平定党项,或许让陕西生民苦上几年,朝廷税赋困难几年,对契丹迁就几年,一劳谋百年大计。哎,算了,不管了、不问了,也问不了,不如给孩子们讲讲课。”
明秀并没有被王璇的豪言所左右,反而兴趣十足地说道:“你倒是教的好啊!,数字、负数。。”
王璇一听,倒是把心中的郁闷压了下去,如今他的目标已经一分为二,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变,用知识去影响,权衡之下,他逐渐倾向于去影响。
用实力去争夺,铁与血的沸腾中,他很自信自己能够胜利,但又能怎样?不过是改变一个朝代,百年后又会怎样?培养一颗种子,开花结果,不断地去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思想,一切要从零开始才会有意义。
王璇碾弃了不悦的杂念,独自来到东院,把十几个孩子聚集起来,带着平和的心情说道:“今天我要给你们讲力学原理,拿一个小铁球、一个大铁球来。。”
对于王璇给孩子们的讲课,明秀虽然不解,却每次都从中得到了启发,一些固有的观念逐渐松动,万有引力、负数、负负得正、几何图形,大小不一的铁球,竟然可以同时落地,最离谱的是,人呼吸的就然是氧气。
真是太淡了,哦、南无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越来越骇人听闻,但细细思量,又无法去辩驳。
时间就这样,一点又一分的过去,欧阳颖携带柳非烟去上任了,到了四月份下旬,赵恒突然用殿前副都指挥使、保静军节度使王汉忠接替王超,却传来灵州治城失守,知州兼灵州都部署裴济战死的消息。
王汉忠成了替罪羊,王超却因祸得福,没有受到处罚。也该王汉忠倒霉,刚刚上任就丢了灵州,却要承担责任,被御史弹劾‘坐违诏无功’。
在几个月后被罢免邠宁、环庆都部署,责为左屯卫上将军、出知襄州,因气愤而死。
他的长子阁门祗候王从吉不服,新科进士杨峰亦是血气方刚,为王从吉写下诉状,让他大胆上书为父鸣冤,结果王从吉被除名发配随州,杨峰也倒了大霉,被发配春州。
咸平五年,简直成了赵恒的噩梦,王璇的预言似乎又灵验了。
在六月,王超、周莹分别赴定州、高阳关上任之际,李继迁在拿下灵州后,忽然对麟州发动袭击,好在麟州知州卫居也不是善茬,麟州地处四战之地,民风剽悍,竟然把两万党项大军死死拖住。
宋军第一次救援失败后,朝廷几乎绝望了,认为麟州缺水,丢失只是时间问题。
历史往往就是那么可笑,在赵恒气急败坏地传旨,麟州军民合力守城,有功者重赏,环、庆都部署以下的高官任选,但卫居只能望诏苦笑。
要不是侍卫步军都虞候,并州、代州副部署张进在没有诏旨调遣下,亲自率军一万广锐军骑兵过河,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精锐的广锐军骑兵,党项人战死上万人后,不得不乖乖撤退。
由于张进并没有奉旨,属于私自调兵,触犯了文官们的忌讳。
御史们立即像打了鸡血,弹劾的奏折如雪片一样,好在赵恒算是清醒了,要不是张进及时救援,恐怕麟州这块战略要地要完了,陕西中部将门户大开,特意下诏奖励张进。
西北烂摊子还没有利索,北方契丹忽然发动一次对保州的忽然袭击,情报很准确,由刚刚成立的机速司北面房使臣送回,甚至精确到契丹几位高层将领,还有详细的兵力配置。这份情报精确的让人不敢相信,连王旦也疑虑万分,就在大宋朝廷君臣疑虑时,契丹人发动了进攻,杨延昭、杨嗣两人仓促应战,还没有列好军阵,就被契丹马队冲乱,结果是一场惨败,阵亡五六千人。
赵恒在接到战报后,顿时目瞪口呆,才明白机速司北面房情报的准确,西北、北方简直一篇乱麻。
正当烦恼不堪之际,朝廷再次出现一件头痛的大事。
此时,王璇如同消失一样,默默地做好自己本职工作,闲暇时在宅院给孩子讲课,他在等待,等待咸平六年的到来。
第111章 咸平五年总结之 狗血()
赵恒似乎对王璇又重视几分,甚至某些重臣,看王璇的目光也端正许多。
正如当初,王璇与冯拯力争的一样,放弃灵州的弊端开始显现,少了灵州牵制之后,陕西彻底暴露在党项兵锋之下。
就在边事失利的形势下,朝廷竟又出两件丢人的大事。
礼部贡举,爆出震撼性的丑闻。
门下给事中、参知政事王钦若主持贡举,竟有僧人勾结他夫人李氏舞弊。
如臭鸡蛋,刚裂一道小缝,御史们如同闻到臭味苍蝇,一个个眼冒绿光,终于有弹劾执政的机会了。
一旦王钦若倒了,御史中丞赵昌言就会上位,御史们也会跟着尝甜头,结果是棒打落水狗。
赵昌言何许人也!当朝重臣,冉冉升起之星王旦的泰山大人,太宗时代便做过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甚至被任命为川陕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是镇压王小波、李顺名义上最高统帅,连名相李沆是他举荐的。
时下,本官已是工部尚书,担任御史中丞兼知审官院,标准的硬茬子。
但王钦若对赵恒有恩,结果处理了一批人,王钦若终究保住了脑袋。
要知道朝廷虽不杀士人,但贡举舞弊是读书人的大忌,若非王钦若与赵恒的关系,十有八九要掉脑袋的,躲是躲了,但名声彻底臭了,夹着尾巴做人好长时间。
集英殿唱名,王璇作为直秘阁,有幸侍驾,目睹风光一时的进士及第第一王曾。
他当年的断言果然言中,王曾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直接回乡发奋攻读,于咸平四年夺青州解试头名,以贡举人身份参加礼部试,他以有教无类赋名冠群士,一举夺魁,成为会元第一。
在三月份得殿试上,一气呵成有物混成赋,文章气势恢宏,志趣不凡,担任阅卷考官的杨亿大为赞赏,称之为:“真乃王佐之器也!”
赵恒大喜之下,御笔钦点为魁首。
整个过程,王璇和王曾没有说话,但王曾却透出感激的目光,让他心下有几分惭愧。
在闻喜宴上,王曾在开席之前来到王璇身边,深深作揖道:“多谢大人当年提点,才有王曾今日。”
王璇却笑道:“状元公不必客气,下官随意一言,不想状元公竟连中三元,一朝成为栋梁之才,可喜可贺。”
王曾实在汗颜,苦笑道:“大人说笑了,当年年少孟浪,若非大人一言,在下或许便是同进士了。”
“何必在乎虚名,志在苍生。”王璇在王曾面前不敢托大,态度温文尔雅。
此时,翰林学士刘子仪走过来,玩笑道:“状元公试三场头名,一生吃穿不尽。”
王曾脸色肃然,正声道:“王大人所言有理,在下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刘子仪一怔,老脸微红,不太友好地瞥了眼王璇,尴尬地笑道:“状元公好志向,好志向。”说完后,借故离开。
“总归是衣锦还乡。”王璇见刘子仪脸色不对,暗叹自己躺着也中枪,被王曾一句话,小小得罪一名翰林学士,当真有些哭笑不得。
王曾却道:“此乃先世积德。”
王璇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