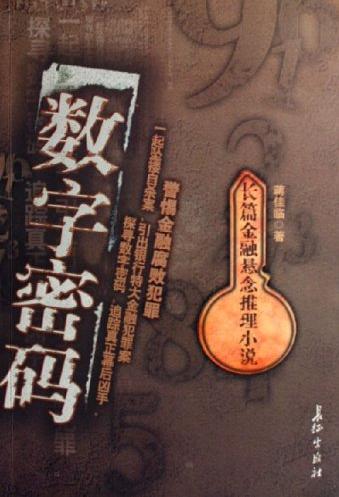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接过来,说:“应该能。”
她拍拍屁股站起身说:“下去睡觉吧,不早了。”
关掉阁楼里的电灯才发现,原来天早就亮了,苍凉的光线从天窗照进来,把这个低矮的空间照出一种老照片上才会有的陈旧感觉,有点诡异,多看几眼汗毛都竖起来,赶紧关上门离开。
下了楼,我叫她去睡觉,自己回到书房,将十二张报纸铺开,研究上面被剪掉的部分,其中有三个洞在中缝,很小的一块,另外都分布在各个版面,大小也不一。
因为是好几个城市的报纸,年头又比较早,靠搜索引擎恐怕没办法,估计得跑图书馆、资料馆或者打电话到当地报社,工作量还是有点大的,幸好只有十二张,要是一百二十张,我非得死在这上头不可。
查到七点半,我随便弄了点面包牛奶填肚子,给小海留张纸条,就开车出去了,跑市政资料馆,跑图书馆,忙了一整天,收获还好,找到两张内容齐全的原报纸,用手机把苏墨森剪过的那几部分拍了照片,其中一张是寻人启事,找一个叫蔡中的人,另外一则是新闻,乾州市下面一个叫横田的村庄后面的墓地里突然发现很大一片“死亡之花”。
所谓“死亡之花”其实就是水晶兰,鹿蹄草科植物,因为自身没法进行光合作用,靠着腐烂的植物来获取养份,加上长得有点诡异,所以被人叫作“死人之花”。
不知道这些跟苏墨森有什么关系。
回家时小海已经做好晚饭等在那里,一大桌子好吃的,热气腾腾。
之后的几天我也都在查剪报的事,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几乎把局里那起要命的“上帝之手”连环案给抛到脑后,直到老懒打电话来,问我突然连面都不露了到底是几个意思。
我看看时间,晚上十点多了,想他们也真够可怜的,连着加班,还经常吃不上饭。
老懒又喂了一声,问我不回答问题又是几个意思。
我笑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吧,你这个人,疑心病太重,说话老是阴一句阳一句,太不好打交道,所以干脆避着点,惹不起你,我总躲得起嘛你说是不是。”
这话是挺认真的,但因为我说话的语气不太认真,所以在他听来大概也是玩笑话,只“哦”了一声,然后叫我明天有空的话过去一趟,讨论讨论案情。
我问他是不是有进展了。
他说:“如果发现案情越来越复杂也能算进展,那就是有进展了。”
别的没说什么,就挂了电话。
小海正好进来,问我今天要不要睡觉。
我想了想说:“还是睡一觉吧,虽然好像还能再撑一撑,但万一接下去要连轴转的话还是补充点能量比较好。”
我说着话就把电脑关了,又把这几天查到的东西整理好,关灯锁门上楼,小海走着楼梯突然哼了一声,像是在笑,说:“你有点像机器人,睡眠和能量都可以储存。”
我点头:“嗯,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查了很多材料,也没弄懂到底是什么原理,网上看到新闻说加拿大也有个人的身体情况和我差不多,没事的时候可以长时间睡觉,有事的时候又能长时间不睡,丝毫不影响身体健康,被列为医学界的难解之谜,也有人说是一种病,搞不清楚。”
到了三楼,她突然刹住脚步,凝着表情看我,静静地、不带一丝感情甚至看不出好奇地问我:“除了不变老、力气大、感觉听觉嗅觉这些特别灵敏和能自动调节身体的能量这些以外,你还有没有其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把身体往她那边凑过去,真凑到她眼皮子底下,然后抬起一根手指指自己的脸:“看,看我这张脸。”
她不习惯挨我这么近,皱着眉头往后仰,仔细看我几眼以后用一种嫌弃的口吻问:“怎么,你是想跟我说你特别漂亮吗?”
我噗地笑,反问她:“难道不是吗?”
她翻个白眼,不想理我了。
我收起脸上的玩笑,认真地跟她说:“我一直觉得我身体这种处处超出常人的优势是有问题的,甚至可能是巨大的问题,但一时又说不清楚问题的关键会在哪儿,总归是觉得太多好事情落到同一个人的头上肯定不对劲,会出事。”
她垂下眼睛沉默,大概在心里觉得我也挺不容易的吧。
69、冰凉的噩梦()
然后彼此都沉默下去,过了好一会,小海才开口,问:“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我慢慢点头:“想过,也查过很多资料,觉得可能是在我很小还不记事的时候,吃过某种很特别的药或者动过特别的手术,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她问:“什么人会对你做那样的事?”
我摇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不知道,也许是苏墨森,他失踪以前,基本每个月都要量我的身高,称我的体重,抽取我的血样,检查我的心跳和皮肤状况等等,跟体检差不多吧。我觉得如果我的身体真被人做过什么可怕的事情,就应该是他干的,可又觉得不可能,哪个爷爷能对自己的孙女做出这种奇怪又疯狂的事情呢你说对吧?”
说到这里,又苦笑着补上一句:“不过也许他并不是我的亲生爷爷,我可能是他捡来养的。”
说最后这句话时,我感觉眼睛里有汹涌的泪水,死咬着嘴唇忍住,不想当场哭出来。
然后有一瞬间,我好像在小海脸上看见一抹奇怪的神色,眼睛里有亮亮的光,但是稍纵即逝,我就没有太留心,几个月以后再回想起这一刻她眼睛里面那点奇怪的光,才恍悟,原来她早知道啊。
我不太愿意回想起以前苏墨森给我体检的种种,恶心得头皮发麻脊背冒冷汗,所以赶紧甩甩脑袋把那些画面甩掉,说:“时间不早了,先睡吧,别的事情明天再说。”
小海没说什么,兀自回了她的房间。
这天睡着以后,我做了以前常做的那个难堪的噩梦,被绑在一张冰凉的像解剖台一样的床上,全身赤裸,嘴里发不出声音,苏墨森像个幽灵样笔直笔直站在旁边俯视我,眼神冷得像冰,没有一点人间温暖。
我一下就吓醒了,抚着胸口喘气,眼泪不知不觉淌了一脸,差不多到天快亮时才又睡着。
第二天上午我跟小海赶到公安局时很不凑巧,几个主要负责人出勤的出勤开会的开会,要我们在三楼办案用的那间会议室里面等。
我心里有事坐不住,让小海等着,自己去计算机部门找小张,之前我让他帮我查北排沟,他回过一个“查无此地”的消息之后说会再帮我继续查,但之后就再没消息回馈给我,所以还是亲自找一趟比较好。
小张看见我很激动,一个劲说抱歉的话,说:“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事情太多一忙一忙就给忙忘了。”
我原本是稍微有那么点不开心的,觉得不管有没有结果好歹都该再跟我说一声,可见他这么客气,又想到这阵子全局上上下下都被那只“上帝之手”搞得头昏脑胀,反而觉得自己太给别人添麻烦了。
小张告诉我说查不到任何叫“北排沟”的地方,乾州市内不管是村名镇名还是街名路名河名,都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相近的名字倒有两个:六排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在山坞里;还有个叫北非路,就在城东二手家具市场附近,是条很小的老路。
他问:“你从哪弄来的这个地名?会不会是弄错字了?应该是六排沟或者北非路?”
我摇头,表示不会弄错。
确实不会弄错,我看过小海找到的那张写了两个地名的纸条,明明白白就是北排沟。
小张见我这么笃定,便说了他认为的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是很早的时候比较偏僻的地方人们对某条不起眼的路或者水沟随便起的叫法,从来没有登记入册过。
可能是这样吧。
想了想,还是很不甘心,又问他会不会还有别的可能性,比如是早些年的地名,后来城建中修改掉了之类的。
他很确定地摇头说不会,因为他遍查所有能查的资料,包括城建和园林建设等各个相关部门,凡建国后的乾州地名全都用软件精确检索过,真的没有这个“北排沟”。
我真没想到他会为了我的请求,做这么多的工作,一时之间突然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只怔怔地看他。
小张脸上却有因为没能帮到我忙而产生的愧疚,挠挠头从抽屉里面取出几页纸递过来给我:“之前原想可能是你弄错字了,所以把看上去有点相近的两个地点的资料给你打印出来,不过”
我赶紧接过来,说一遍谢谢,又说一遍谢谢。
他犹豫了一下,问我这个地名是从哪里听来的,为什么要查它。
我笑笑,说:“我也不清楚,帮朋友查的。”
他也笑起来,问:“你说的朋友,该不会就是那个经常跟在你后面的胖胖的女孩儿吧?”
我说:“嗯,是她。”
然后我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送我到楼梯口。
我下楼走到外面以后突然有点回味过来,觉得他刚才提到小海时候脸上的笑容有点奇怪,仿佛很高兴。
想来肯定是这些日子白亚丰老是巴着小海给她献殷勤闹出绯闻来了,小张才会笑成那样。
想想白亚丰和小海两个人,我也不由自主就笑了。
我回到一号楼,他们的会还没开完,小海坐在窗边玩贪吃蛇游戏,我去茶水间泡茶却意外撞见付宇新,他端着杯茶背靠着墙在那里发呆,我喊了他一声才回过神来冲我笑笑,说:“开会开得头痛,出来偷个闲透口气。”
我一边取茶叶一边问他:“案情有没有进展?”
他叹口气说:“情况越来越复杂。”
问他:“怎么个复杂法?”
他又叹出口气,说:“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等开完会了抽出空来大家一起再讨论讨论。”
我点头。
然后突然沉默下去,只剩下饮水机烧水时的一点声音,那声音在寂静的空间里居然有一种轰鸣的感觉。
付宇新突然又没话找话问我这几天是不是带小海去哪玩了,怎么没见来局里。
我不想跟他说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便顺势回答说是。他又问我小海跟着我会不会给我添麻烦,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只管跟他讲,他会做另外的安排。我说我们相处得很好,不用考虑别的安排。他便放心地点点头,疲惫地笑笑,说还得回楼上开会。
付宇新的脚步即将跨出茶水间的门时,我用很平静的语气喊住他,问他知不知道发生在江城那起“人皮x案”的细节,如果知道,能不能跟我说说。
我看见他的身体很明显地抽搐了一下,茶杯都差点拿不稳,而且脸色刹时难看,好像我往他的软肋上使劲捏了一把似的。
但毕竟是多年的刑警,再受震憾也能迅速调整好姿态和表情,马上作出一副严肃镇定的样子问我:“这案子,你从哪里听来的?”
我说:“无意中听几个警察聊天聊起。”
他皱着眉头问:“你突然打听那起案子做什么?”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回答:“因为听说那也是件连环案,好像还有固定的模式在,所以想多了解点细节,也许能在比较中拓宽些思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