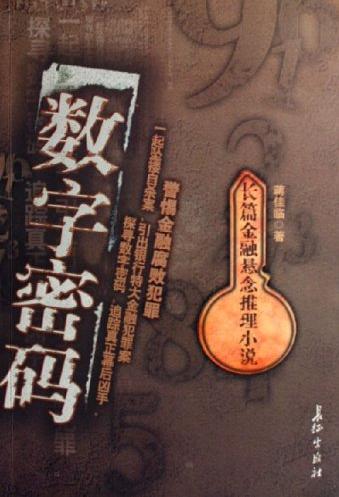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下去会是什么?
感觉再出几桩案子的话,我们大概就能凭现场遗留物件和线索拼凑出一个女人的全貌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铁了心认定,复仇联盟里面的那个领头人物,那个主谋,那个担当着“上帝之手”四个字的角色,应该是个男人。
我能感觉到一个聪明绝顶的男人的气息,聪明,冷静,沉着,细心,讲究原则,有超出常人的掌控力和自制力,还有一种奇异的金属质感的漠然。我想起美剧里面那个吃人的汉尼拔,觉得这件连环案的凶手,就差不多应该是那样一个厉害的角色,但是,他没有汉尼拔那份优雅。
优雅,对,是这个词,之前老懒在对凶手做侧写的时候,提到过这个词,并且把它跟我联系在一起。
想到这里我歪了下头,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老懒把我当成凶手嫌疑人这件事,觉得未必全都是坏处,至少是对我很多方面优点的一种直接称赞,比如我很优雅。
但是,我不觉得这只“上帝之手”优雅,优雅这种东西,不管是内在的气质还是外在的作秀,都有某种享受的东西在里面,譬如汉尼拔吃人,他是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上帝之手”在设计这一系列案件时,并没有享受。
他只不过像个厉害的匠人,先出图纸,而后照图纸打造作品,精准到每个细节,不出差错。
老懒就站在我后面,也发现了尸体胸口处的那两道黑色。他走到我侧面将眼睛凑到很近的地方看了一会,然后往旁边移一步,再看一会。接着看看我,突然伸起手比划了一下高度,再接着,猛又扭过脸来看我,原本淡漠的表情里多了一缕若有所思的味道。
我被他死人样的目光凛冽扫到,本能就有点慌张,同时也立刻明白了其中缘故,赶紧再去看尸体皮肤上那两条黑色睫毛膏的痕迹,果然,几乎跟我的眼睛在差不多的高度。
几处现场留下的线索都显示凶手是个女人,“七刀案”现场的披风正好是我的尺码,现在又出现差不多正好合我身高的睫毛膏痕迹。
这些线索,好像真的都在指向我。
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自己都恍惚了,这一切的一切,加上老懒紧盯不放的怀疑,再加上我的很多特质确实符合侧写,所以我想,会不会是我有精神分裂症,一半时间是凶手,到处犯案,另一半时间又是侦探,拼命破案?
我打了个寒战,觉得自从认识老懒以后,我的脑洞越来越大,有点接近丧心病狂。
老懒还在看着我。
我不动声色地稳住情绪。
这些日子过招过下来,我也渐渐没先前那么恼火了,居然还没心没肺朝老懒笑了一下,凑啊凑啊凑啊凑过去,直把自己的睫毛戳到他的眼睛上去,说:“怎么,要不要拔两根我的睫毛去化验一下是不是同款睫毛膏?”
他把身体往后仰,一脸嫌弃的表情,说:“谁能保证你每天都用同一款睫毛膏?化验结果不同,也不能证明不是你的啊。”
我说:“那东西又不能吃,就刷个质感,我有必要买很多款搁家里?”
他说:“你们有钱人的世界不是我们这种凡人能理解的,我以前抓到个女嫌疑犯,搜证的时候在她家里搜出两千多双高跟鞋。你也是个白富美,家里有几千支睫毛膏估计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
我说:“哟,听这口气,你不把我判成凶手不罢休了是吗?
他说:“哦,那倒不是,我并不真的认为你是这几桩命案的幕后主谋,我只是觉得你气恼窘迫的样子很有趣,忍不住经常要逗逗你。”
说到这里他突然笑起来,真摆出一副我只是逗逗你的表情来,我真是无语到了极点,翻个白眼,不搭理这茬,还是专注于案件。
我把我对现场很熟悉但怎么都想不起来到底在哪见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情讲给他听,希望他能提供点思路,让我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他听完以后说:“要死了,你不说还好,你一说,我又要真的怀疑一下你到底是不是凶手了,搞得不好你有梦游症,或者精神分裂之类的,你有上医院检查过吗?”
我心里又恼,白眼翻得更大,直不愣登问他:“就算我真有病,你有药吗?你能治吗?!”
他觉得这个话题再说下去就没意思了,赶紧识趣地转回到当下,给我讲解他们之前初步堪查现场的情况:“窗户上的是红色是丙烯颜料,不是血;尸身上大部分也都是颜料;这间厂房废弃有六年之久了,凶手是强行打破大门上的锁进来的,据原先的主人讲,这里除了角落里堆的那几麻袋过期不知道多久的饲料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颜料、刚才你问起的篮球、还有凶手离开时用来打扫的水和拖把等工具,全都是凶手自己带来的。这个现场没有脚印、凶器,也没有凶手遗落的随身物件,整个干干净净,除了刚刚被你发现的这两道睫毛膏印子。”
他一边说,一边又开始对照睫毛膏的位置和我的身高。
53、代芙蓉!()
我再次环视现场,深吸口气,仔细考虑这里面的古怪之处,凶手不嫌费事自带颜料和篮球,用这样残忍的方式将受害人杀死,又把现场弄成这个样子,看上去匪夷所思,但有前面几桩案子做铺垫,就不那么难理解了——他们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复仇的意思。
必须把现场弄得跟曾经发生过某桩命案一样。
即使不能一模一样也至少要差不多,要在最大程度上复原。
跟“开膛案”一样,都是必须,对执行者来说再困难再下不去手也得硬着头皮干。
因为“必须”。
我对复仇的判断越来越坚定,再看老懒的目光,就有点不屑了,他肯定还在坚持他的反社会人格论。
老懒问我以前到底在哪里见过这个现场。
问这话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大门的方向,说:“就算你没蒙我,以前真的发生过同样的案件,也肯定不是在乾州,你想,刘毅民是土生土长的乾州人,又当了三十年的警察,他没觉得这个现场很面熟。而且,也肯定不会是在江城,付宇新来乾州之前是在江城,听说是从底层爬起的,年头也应该不少,他也没觉得眼熟。所以,你只要想你在别的城市接触过命案,就很好回忆了。”
他这是在帮我做记忆启发,可是没用。
我跟他说:“我记忆里是有这个画面,但我肯定没有亲自在现场过,所以那个画面只可能来自画、照片,或者文字一类的材料。”
说到这里,我心里突一下跳,对,文字,我刚才没考虑过文字的情况,也许我在哪里读过一段描述这个现场的文字。
对,文字描述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我对眼前这画面的熟悉感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既然间接获取又能达到如此强烈的画面感,最有可能就是文字。有人曾经详细描述过这样一个命案现场,环境是怎样的,光线是怎样的,尸体是怎样的,诸如此类。优秀的文字能激发人的想象力,激发出潜在的构图能力,所以我脑子里就有一幅和眼前这幕十分十分像的画。
那会是哪里呢?报纸?杂志?还是悬疑?太混乱,真的太混乱,我活得太久了,看过的书和材料又多,脑子里塞满有用没用的东西,估计跟个硬盘很大文件夹分类又不明晰的电脑差不多,一时要从中精准找出点什么东西来真的很困难,特抓狂。
老懒还想启发启发我,我嫌他吵,扰乱思路,就叫他闭嘴。
他这次居然很听话,让闭嘴就闭嘴,还乖乖往后退了几步,不吵我。
我又绕着尸体走两圈,仔细查看每个细节,光、姿态、颜色、死人泣血的空眼睛。
尸体嘴角那滩黑红色的是血,因为不想她出声,凶手把她舌头割掉,血从嘴角淌出来,淌得有点夸张,反倒不真实了,乍看像颜料。
我扭过头问老懒第一次尸检的时候有没有查过死者的舌头。
他答:“查过,舌头不见了,这里没有,厂房周围也都没有找到。”
于是我感觉肚子里面轰隆隆一阵乱响,紧接着胃里翻江倒海一阵恶心,眼睛不由往尸体的肚子看去。我对眼前的血腥画面没多大感觉,但难以忍受想象中受害人死前遭遇的残酷折磨。
我不确定那条割下来的舌头到哪里去了,但是,我终于想起,有个人曾经很认真地对此做过猜测,她猜测那条消失的舌头,被凶手强行喂受害人自己咽进肚子里去了。
作这个猜测的人,说起来,还真的不能算不熟。
代芙蓉!
我终于想起为什么对眼前的画面有如此强烈的熟悉感了,代芙蓉的名字在脑袋里炸响,我的脸色就有点发白,颤着嘴唇往后退几步,扭脸看外面,拉扯喉咙大声喊刘毅民。
喊了一声,他没听见。再喊一声,还是没听见。他正站在警戒带外面跟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说话。我拔高音量再喊,站在门口的付宇新和胡海莲都觉出我的喊声古怪,近乎尖锐,所以胡海莲狂奔几步去拍刘毅民的肩膀。刘毅民受了惊吓般跑过来,差点把警戒带给扯翻掉。
他跑进来,呆呆地看我,右手按在腰间,随时要拔枪的样子,这是当惯警察的人的应急本能。
我咽口唾沫,狠狠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给他。
代芙蓉。
这三个字好像根本不是从喉咙里滚出来的,而是从骨头里面窜出来的,冒着嘶嘶的冷气,透着股特别骇人的劲道。
刘毅民完全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指着尸体一字一顿跟他说:“去把代芙蓉找来,问她,仔细问她。她以前见过这种现场,见过,还报道过,差不多一样,但有几处细节不同。你去把她找来问,那件原版的案子,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我用了“原版”这个词,而且咬字很重,一字一个坑。
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曾经有人用这样的方式杀害了某个人,然后现在,当初那桩命案的受害者遗族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复仇,也就是复制出了眼前这桩血案。
老懒说得对,既然刘毅民和付宇新都没觉得这桩命案眼熟,说明原版案件不是发生在乾州也不是在江城,而是在别的什么城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天胡海莲查来查去都查不到类似旧案的原因。
那只“上帝之手”选择在乾州实施这一连串复仇谋杀,恐怕有部分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警察太快追踪到原版案件。
刘毅民话没听完就已经掏出手机来拨号码了。局里面应对媒体那块工作基本由他在负责,所以找代芙蓉是分分钟的事情,加上那女人跟我一样又是个哪里有血腥味有犯罪现场就往哪里奔的死变态,我敢保证,不出一个钟头,久闻其名不见其人的代芙蓉就会赶到这里。
代大记者!
刘毅民出去以后,我重新走到尸体前面,感觉全身心都渐渐放松了下来,神经不像之前那么紧绷了。
然后,记忆反而从容地清晰起来。
代芙蓉曾经报道过的原版案件里面更多内容和细节都泉水样从记忆深处冒出来,那桩案子的死者也是女性,三十六岁,小学教师,为人温善,丈夫是冶炼厂工人,夫妻关系很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