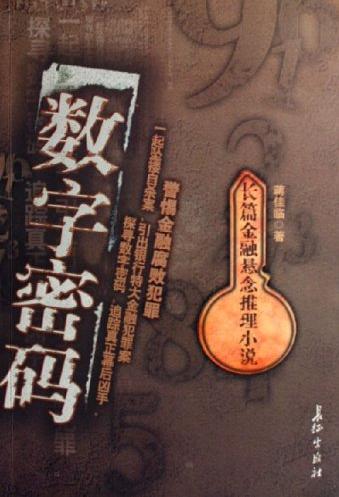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还说越是超出常规的例子,越有其超出常规的狡猾处,美国fbi统计出来的数字说百分之九十八的连环凶手都是男性,女性只占百分之二,甚至还不到。但偏就是这少数的部分,会犯下让人膛目结舌难以下手侦查的案件,比如那个著名的黑寡妇冈尼斯。
我发现我说不过他。
他不仅用宽泛的理论知识和例子打压我,还把眼前案件的疑点拎出来作了有利于他论断的补充,比如“砸头案”的简单粗暴和“七刀案”的细致完全属于两种气质的凶手,这里面没有任何证据或线索支持我的“复仇论”。
这时白亚丰突然跟个小学生似的举手,表示有问题要问。
我因为还是很坚定自己的看法,但又说不过谭仲夏,所以心里有点窝火,看见白亚丰那副猥猥琐琐有话不敢说的样就来气,很不耐烦地叫他有什么就赶紧问。
他嘴一张牙一碰,一本正经吐出个无聊到爆的问题:“为什么女性连环凶手那么少?”
我被这问题噎了一下,翻两个白眼,懒得理他。
谭仲夏倒是认真,喝口茶,转过脸,正正经经回答白亚丰说:“你想,女人天生嘴碎,心里藏不住事,平常随便做点什么都非得跟人家说才高兴,何况杀人这么大的事!她杀了第一个,扭头告诉别人,一传十十传百,还没来得及杀第二个呢,警察就把她逮了,怎么可能犯得了连环案嘛!”
他回答完,立刻又扭过脸来继续跟我讨论案情,把白亚丰不尴不尬不温不热晾在那里,晾出一脸白痴表情。
谭仲夏认为被害人死前的那三天,是凶手定下的“审判日”。凶手用三天的时间来审判他们认为有罪行的死者,卖淫、偷盗贩卖婴儿的女人;坑蒙拐骗草菅人命的包工头;露阴癖和试图猥亵自己亲生女儿甚至很可能已经得偿所愿的变态狂。这些行径在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凶手眼里,条条都是死罪。他们用三天时间用来审判然后才执行死刑。
然而我也有可以反驳的说法。
一般来说,反社会人格的连环凶手,他,或者她,或者他们,在犯案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模式,比如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或者特别的凶器,再不然就是从死者身上取走点什么或者在命案现场留下些什么以便让人知道这些案子是同一个人所为,比如“榔头杀人魔”是指那个凶手在犯他每一桩案件时使用的凶器都是榔头,而“海湾变态”是用弃尸地来指代,凶手把他杀的每个人都肢解成碎片用旅行箱装了扔在固定的海湾,再还有“扑克小丑”是指凶手在每个杀人现场都留下一张扑克牌。
而我们手里的三桩案子并没有一样可以用来给它们下定义的典型特质。
这三个受害人虽然都死得极惨,但死法各不相同。虽然死前都被捆绑,但捆绑用的材料也都不同,绳结也没什么特殊的。现场虽然留下很多七零八碎的线索,但并没有与案件无关可以用来作标识的记号。
这是一部分原因。
再者,我认为,反社会人格的连环凶手,智商一般都是比较高的,想想看就知道了,智商低的犯一两桩案子就被逮住了,哪有机会继续犯案。只有那些智商高、情商高、心思密、耐性好的人,才能屡屡犯案甚至还能逃脱法网,他们行动利落、高效、干净,在某些方面有变态和病态的讲究。但眼下的三桩案子,除“七刀案”扎七刀全部避开主动脉这点看上去稍微有点技术含量以外,其余几桩都野蛮粗暴到极致了。
这些是我的看法。
谭仲夏突然摇头,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强迫症的。”
我噎了一下,突然觉得,他这话,意味好深长。几分钟前,我才说过我没有强迫症的话,马上,他把这话当颗球样踢回来了。
他是说,不是每个连环凶手都像我以为的那样,对命案特别讲究,会有固定的模式,也许就有那么些人没这种贱毛病,他们随心所欲,乱七八糟,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呢?就像我往墙上钉照片的行为一样,完全不按顺序。
他这话,该不会有别的意思在里头吧?
他该不会有怀疑我是凶手的意思吧?
真要这样想的话,他疯了不成?
我朝他看过去,他却没看我,神情很简单,似乎没我想的那层意思。
然后我们唇来齿往你一言我一语又争论了好些时间,白亚丰站在旁边像个傻瓜一样看来看去,谁说话看谁,脑袋扭来扭去,就像在看乒乓球比赛一样。
等我们终于停下不吵你瞪我我瞪你时,他又再次弱弱地举起一只手表示要发言,这回谁也不理睬他,还是你瞪我我瞪你,各自心里都拧着股子劲。
白亚丰觉察不出空气里面有古怪的味道,自顾自发问,问我们这么争来争去的意义在哪里,反社会人格团伙作案也好复仇者联盟作案也好,争明白了又怎么样,想破案还是得看现场证据不是吗。
我坐下,暂时撇开谭仲夏不理,回答白亚丰说:“很有必要。复仇杀人的话,杀害对象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跟谁有仇就杀谁,与别人无关。我们也就能从死者的人际关系中进行排查。但如果像谭副队长说的是反社会人格将自己扮演成上帝角色进行的系列性连环凶杀,目标就不确定了,任何一个品行不端的、在凶手眼里有罪的人都有可能被杀,我们也无法从死者本身来进行排查,除非凶手自己露出马脚,否则很难抓得住,得从外部去查,邪教组织啊,特别嗜好俱乐部啊,之类的。”
白亚丰一脸似懂非懂的表情。
我不要他懂,我只是借跟他说话的空档缓一缓,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谭仲夏在有意无意地给我施加压力。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他说的话,他似乎轻描淡写地提出的问题,他明里或者暗里打量我的目光,全都带着迷惑、探询和叫人很不爽的质疑。
恐怕他真的是把我当成凶手嫌疑人了呵,仔细想想,故意接近警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勘查惨不忍睹的“开膛案”凶杀现场,符合反社会人格对警察的挑衅性行为特征,还有遗留在“七刀案”现场那件女士披风,仔细想想,好像正好是我的尺码。
我的三叉神经又开始痛了。
这时,小海突然走进来,用托盘端了四杯茶,每人一杯,白亚丰也有份。
白亚丰接过茶的时候,恭敬得像个太监,就差给小海下跪谢恩了。他想讨她的好,以弥补之前嘴贱说的那些得罪人的话,可小海不领情。
她是个对什么都不感觉到意外,发生什么都能接受,没有恐惧也没有多少好奇心的姑娘,活得无喜无悲无感觉,像是清水煮的大白菜,看着鲜嫩可口,实际上一点味道都没有。然后你吃着,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它会没有味道,为什么煮它的时候不放点盐。
谭仲夏接过茶,低垂着眼睛细细吹着水面上的浮叶,轻声慢语说:“你好像对艺术这件事有偏爱,比如构图、色彩这些。”
他这话又是突然之间出口的,而且眼睛没有看着谁,搞得小海以为是在跟她说话。
我知道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开膛案”的现场不管是凶手无意选择的还是有意选择的,它都有一种艺术的美感在里面,这无法否认,只是有的人能看到有的人看不到而己。
他不怨自己没看出来,反而以我看出来为疑点来怀疑我?
我深吸一口气,把刚刚捧起来的茶杯放下,把两只手撑在桌面上,倾着脸特别特别认真地盯住他:“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大学里学的是平面设计。”
他漫不经心地点头:哦。
只这半分钟时间,小海已经感觉到气氛里剑拔驽张的味道了,目光不由利害起来,直直望向谭仲夏。
谭仲夏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我可能会产生的敌对情绪,仍旧一脸漫不经心的表情,悠闲地喝着茶说:“来,苏姑娘,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你想杀人,你会怎么操作。比如,从什么角度选择目标人物。怎么动手。怎么弃尸体。你会把犯罪现场弄得非常艺术化吗?会留下作为身份标记的符号或者物品吗?还是从死者身上拿走什么当纪念品?”
他声音很低,但是面色平静。
36、还是针尖对麦芒()
谭仲夏提出的这个“假设”实在有点露骨了,小海听着,目光发沉,转过脸来看我一眼。
我微微笑了笑,在心里跟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本来我的原则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对付蠢货有对付蠢货的办法,同样,对付聪明人也有对付聪明人的办法。
不用说,谭仲夏肯定是个聪明人。
现在我有点后悔没多打听打听他的底细和来路,只知道从上海调过来,不知道别的。搞得不好他精通犯罪心理学,能从任何一个不受意识控制的微表情或者微动作里读出名堂,所以,在他面前撒谎肯定不明智。
唯有把真话当假话说,再把假话当真话说,真话假话炒成一锅,才是眼下对付他最好的办法,亦真亦假,真真假假,你自己分析去。
我慢悠悠喝几口茶,才似笑非笑看谭仲夏几秒钟,正色回答他的问题:“如果我想杀人,嗯。我肯定会选择我恨的,并且是我认为该死的人下手。我会做得滴水不漏,不留一丝痕迹。而且,我还会想办法说服自己相信,我不曾做过那些事情。”
我想这个回答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会主动去杀谁,但谭仲夏给了我个认真想想的机会。我想一定就是这样,做得干净利落然后迅速忘记,挺好。
谭仲夏死定定地看着我。
我脸上浮起笑,笑得有点得意,然后从桌上抓起一支红色马克笔,转过身把墙上照片上那些凶手留下的线索一一圈起来,脚印、凶器、大衣、标有厂名和地址的弃尸桶,种种种种。
我告诉他说留下这么多乱七八糟故意扰乱警方办案的线索,绝对不是我的风格。而且我是个简单明了的人,绝不干哗众取宠的事,在命案现场取走什么或者留下什么来做身份标识这种,算了吧。还有艺术感仪式感什么的,呵呵,杀人就杀人,搞那么多花样,费时费力,真是有病。我这个人连强迫症都没有,怎么可能有那种神经病。
他还是死定定地看着我。
我撇撇嘴,表示说完了。
然后我听见白亚丰在那里犯迷糊,喃喃地说:“我还是想不明白凶手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复杂,明摆着都是预谋杀人嘛,可预谋杀人这种事,不是越少人知情,对自己来说越安全的吗?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刀把对方捅死,除了天知地知再就只有凶手自己知道,为什么非要几个人联手?就不怕哪个喝醉酒说漏嘴?或者哪天闹翻了,大家谁也别有好日子过?”
他这一发问,虽说是把我跟谭仲夏从眼前的尴尬境地里解救了出来,但又把案情推回到最开始我们争论的地方了。
谭仲夏仍旧认为是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反社会人格的危险分子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体,他们把自己当成上帝,随机挑选他们认为有罪但是没有被人间法律制裁的人来审判、定罪、执行死刑。这样的犯罪团体除非主谋落网,否则绝不会收手。
他说他已经让下面的人分头打听,看最近有没有可疑的团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