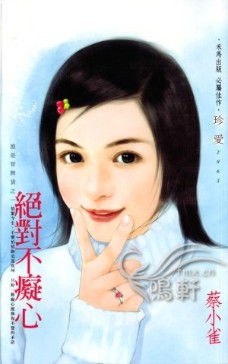绝对权力:仕途成长记-第126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吕华说:“桑塔纳车宽,要是别的车就真挤了。”
温庆轩也说:“小舒教授跟我们同车,我们情愿挤着。”
就这样,舒晴上了车,彭长宜和温庆轩、吕华坐在后排座位上。
上车后,彭长宜说:“老吕,给家里打了电话,通知所有班子成员,今天连夜召开常委会。另外,通知所有的市领导包括一些相关部门的领导,明天上班召开常委扩大会。”
“好的,我马上通知。”
吕华往回打了一个电话,重复了一遍彭长宜的指示。
彭长宜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国庆家属没来医院吗?”
吕华说:“出国了,好长时间了,陪读去了。”
彭长宜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感到,这次事件,比牛官屯要复杂得多,也棘手得的多,之所以复杂和棘手,并不是事件的本身,也不是老百姓,彭长宜从来都不觉得处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是问题,固然,他们针对征地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他从不认为他们不好对付。他们本质是不坏的,他们无非就是想多得到一点补偿,甚至把这些补偿任意夸大。
:
275。第275章 根源所在()
彭长宜他不再关心事件的详细过程,而是问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温庆轩:“温部长,您怎么看这次事件?”
哪知,一路上都很少说话的市宣传部部长温庆轩,此时听彭长宜问他,却出乎意料地说:“彭市长,我不瞒您说,我昨天就写好辞职信了,本来我今天上午已经交给国庆记了,但是国庆记说我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如果非要辞职,也要等完成这次强拆任务后再提出辞职,常委会上定的事,不容更改,更不许有人当逃兵就这样,我就没交这封辞职信,果不其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的声音跟大,而且很激动。
彭长宜一听,就是一愣:“哦?您,真的想辞职?”
“当然了,您看,辞职信就在口袋里揣着呢,他不收,我就又揣了回来。”温庆轩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封辞职信,递给彭长宜。
彭长宜没有接过来看,他说:“我不看,也不管,那是上一篇的事,今天晚上我回来了,就从今天晚上往后翻篇,我在一天,您就别想辞职,除非上级来调令,调您到别处高就,那我就拦不住了,否则,您就是说出大天这职也辞不了。”
温庆轩叹了一口气,口气有些缓和下来,说道:“彭市长啊,我还真不是见着您说好话,在来医院的路上,我就跟老吕说,我说,我要是昨天晚上知道长宜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都不会写辞职信。”
彭长宜笑了,说:“这就对了。”
温庆轩说:“我不是抬举您,我说,彭市长在亢州当记的时候,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能跟他交流,也能把问题谈开,但是跟国庆记就不一样了,我不是背着国庆记说他的不是,我对事不对人,你一旦有不同的意见,就很难跟他沟通,他在征求你意见的时候,也是非常虚心、非常真诚的,但是你只要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有时不等你把话说完,他就打断了你,说:这事已经定了,就那么地吧。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态度,老吕应该也有体会。他根本听不得不同意见,那种行事作风,特别像当年的钟鸣义。一次两次行,次数多了,他就是再怎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提了,你提了也没用,提等于不提,还惹他不高兴。但这次强拆可是例外,我昨天晚上在会上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以前我也都是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这个您不信的话问老吕,市委办都是有会议记录的,您可以去查。”
彭长宜笑了,他说:“您的话我没有理由不相信。”
温庆轩说:“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已经在类似的问题上栽过一次大跟头了,在全省都出了名,为什么就不能吸取血的教训?非要跟老百姓硬碰硬当然了,硬碰的最终结果肯定是政府胜利,因为谁惹得起你政府啊?但是有句老话怎么说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哪,你把他逼急了,逼到了死胡同,他能不采取极端手段吗?”
温庆轩停顿了一下,在看彭长宜的反应。
听到这里,彭长宜说道:“您说下去。”
温庆轩继续说:“我在会上就说过,而且私下也跟国庆记和刘星市长交换过意见,但是没用,没人听你的”
他显得情绪很激动。
一直以来,彭长宜对樊文良选拔上来的这个宣传部长很尊重,温庆轩这个人也的确让人尊重,为官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投机钻营过,更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取过什么利益,人本分老实,是亢州上上下下公认的学者型的干部,才华出众,也是省里有名的基层理论工作者。
他继续说道:“我今天说的这话,真的不是事后诸葛,我的的确确在私下里做过工作,但是没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的话,不但没有人肯听,而且还被认为是危言耸听我早上去找国庆递交辞职报告的时候,你们猜刘星市长说我什么?”
车里的人都不说话,在认真听他。
“他居然说,说我在会上的言论是妖言惑众,是动摇军心,还说之所以那些乡民这么强横,是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跟政府作对,一言以蔽之,我就是罪魁祸首就是坏拐子,就是扇阴风点鬼火的人”
说到这里,温庆轩情绪更加激动起来,声音都有些颤抖了,看着这个昔日的老实人生这么大的气,彭长宜感到了欣慰,最起码在亢州班子中,还有敢于说真话的人。
吕华这时说道:“这个我可以证明,庆轩部长说的的确是实情,他几次在班子会上提出过自己不同的建议,也私下跟我交流过。”
“唉——”温庆轩叹了一口气,说到:“这是今天长宜市长回来了,如果他不回来,我这一肚子话准备烂在肚里,不管怎么样,你并没有阻止流血事件发生,说出大天来你从前说的话也是放屁我也可能是生气太足,我记得关于这个问题,以前小舒在这里挂职的时候,我们一同去牛官屯搞调研,就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舒晴在挂职期间,跟温庆轩有过接触,她很佩服他的理论天赋和对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解读,听温庆轩这样说,就问道:“温局长,我冒昧地问一下,这项工作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一年的时间内,始终就没跟老百姓谈妥这事吗?”
“谈什么?怎么谈?我不是向着老百姓说话,怎么谈他也是不平等条约甚至是欺辱条约,欺骗条约跟老百姓玩文字游戏,支支吾吾、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大凡有这类事件的发生,都是不透明、不清白,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表现。”
“不清白?”舒晴有什么不明白。
温庆轩更加激动,他说道:“就是不清白这边跟老百姓签的协议明明是租地,一亩多少钱,租期有的是三十年,有的是二十年,说是建农贸市场,建生态养殖场,建各种各样的厂房,还能安排村民就业,等等甜话,给老百姓画了一个大大的馅饼,老百姓同意了、签字了。那边呢,又和四面八方来的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开发征地协议。结果怎么样?纸永远都包不住火的,那些房地产大鳄们,他们可不是吃素的,跟你签了合同,把征地款交给你后,他们就开始规划,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设计图纸,图纸刚出来,就立刻开始大卖楼花,按说这都是不允许的,拿到业主预交的买房款后,才开始搞建设,挖槽,挖很深的槽,立水泥柱,很密很多的水泥柱。老百姓再一看,傻眼了,这哪是盖工厂呀,就是再没见识的人,他也能看出你建的不是厂房,而是高楼,是要搞商住宅楼别说租期是二十年、三十年,就是五十年一百年,建起了高楼也没法恢复地貌啊这么点钱就把全家的口粮田卖了出去,他们能答应吗?所以就开始告状,四处告,各家各户没有不参与的,锦安、省城、首都,来回来去地告。但是你怎么告,也阻止不了开发商建设的步伐,眼睁睁口粮田都被戳上了水泥柱,那些还没有建设施工的土地的主人们,开始了一场耕地保卫战,他们撕毁了之前签订的合同,提出提高补偿款的要求,要求土地按正式招拍挂走程序,按照征地的标准要钱,他们一方面跟政府谈价钱,一方面借着开春的时机,开始在地里种树,什么树贵种什么树,能栽多密就栽多密,为的是多得补偿款,当然,他们告状的脚步始终都没停歇过。后半年到先现在,市里就光去首都接这些告状人的钱就是一大笔开支。”
舒晴问道:“既然老百姓提出按征地程序进行补偿,给他们补齐应有的价钱不就没事了吗?”
吕华说:“拿什么补,开发商给的征地款是有数的,是按照标准赔偿的的,这笔钱早就盖不上盖儿了,拿什么给老百姓?”
温庆轩说:“所以,矛盾就来了,开发商自称手续全部合乎法律程序,土地是他的,他就要进场施工,误了工期就告你政府;老百姓告政府以租代征不合法,抗着不让施工方进场作业,大小冲突不断。这一年来,市里几乎没干别的工作,我们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项工作上了。”
舒晴皱着眉头,又问道:“从理论层面讲,您认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温庆轩说:“我认为问题就出在执政方。”说道这里,温庆轩看了一下彭长宜,说道:“彭市长,我在和小舒教授探讨理论层面的事,完全站在学术角度看问题,不涉及其它方面,也不带我个人的主观偏见,我们是纯粹的探讨,您不介意吧?”
彭长宜有一半时间在听温庆轩发牢骚,有一半时间在考虑怎么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波,这一半的时间,他想的最多的是怎么应对亢州地面上各路的开发商们。听温庆轩这样问自己,就说道:“我不掺和,你们尽情讨论。”
舒晴这时回头说道:“您认为执政方的问题出在哪儿?”
温庆轩说道:“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意思,既然你这么刨根问底,那我就直接跟你说吧,问题出在我们的流盲行政上。”
“流盲行政?”舒晴有些吃惊。
“是的,就是流盲行政,这是我个人下的定义,也是我的理论。有的学者早就提过这个问题,但不是这样的说法,意思基本一致。你在高层搞政研,肯定是没有听过这个词,是不是吓你一跳?”温庆轩的口气很坚决。
舒晴说:“是啊,是有点惊人,我的确头一次听到,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
彭长宜注意到,舒晴用了“说法”,而不是顺着温庆轩说成“理论”,在这一点上,彭长宜觉察出舒晴政治是成熟的,当然也是过硬的。
温庆轩解释着说道:“我还是那句话,只限于探讨理论层面的问题,这个观点我从来都没跟别人说过,不说还被扣上妖言惑众的帽子,说了的话,指不定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呢?为什么叫流盲行政,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为了在短时间达到一定的见效,带头破坏秩序,野蛮行政,而且这种作风在各地都有表现,就拿近来各地发生的征地风波来看,已经有形成趋势的苗头。这不是危言耸听,是事实。”
车里的人都屏住呼吸认真听着。
温庆轩继续说:“我为什么下这样的定义,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本

![女子无殇1,2完结,番外晋江新完结高分文[1].绝对好看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