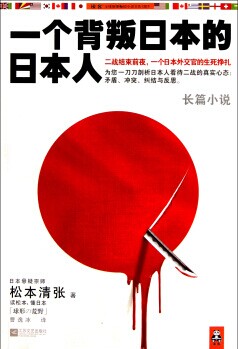背叛-第5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伯诗人称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后部重”。我的目光和柳如叶的“后部”一告别,急忙移到客商的腰间来。我以为客商别着的真是一包香烟。当时我见过的最高级的香烟就是那种铁盒装的中华烟(可惜我只是见过,没有抽过),我以为客商别着的就是这样一包铁盒装的中华烟。铁盒中华烟是红盒的,还没见过黑盒的。转念又一想:也许有黑盒的,只是自己没见过罢了。我有点鄙夷这个人:太摆谱儿了!将一盒中华烟挂在裤带上干啥?证明自己是老板?因为只有老板才抽这种高级烟。这与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有什么两样:递给他一支好一点的香烟,看看牌子,放到鼻底嗅一嗅,舍不得抽,别到耳朵上。也许这人只有这一包烟,为了显派,天天出门时挂在裤带上。或者只是挂着一个空铁盒。就像我们《紫雪日报》那些记者,省长来了,忙着跑前跑后照相。给省长拍完再给市长、县长拍,再给随从的干事拍。回去后洗好、选出、放大,屁颠屁颠拎着送给县长市长:给县长送去的,一定是和市长的合影;给市长送去的,一定是和省长的合影。可却从不见给干事送——送什么呢?给干事拍照时,相机里就没装胶卷!
我当时正在心里这样“损”着客商,客商已从我身边经过。那包香烟突然像鸟儿一样叫起来,吓我一跳。然后便见那人拔出来一边走一边看。后来我才知这种“鸟儿”叫传呼机,简称“呼机”。也称“BP机”、“屁屁机”。我后来也有了这样一台“BP机”,为了表示对其轻贱,将它称作“土豆”:因为土豆也有四种称谓:土豆、洋芋、山药蛋、马铃薯。
人们对于现代文明,往往持这种态度:一边鄙夷它,一边接受它,就像嫖客之于妓女的态度。
那天我和小牛从车行出来,找一家宾馆住下。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们这宾馆是两星级。进房间后小牛左瞅瞅右看看,然后有点神往地说:“咱们啥时能住一次‘一星级’宾馆呢!”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是装傻,我忍不住笑了:还有比我鱼在河更“刘姥姥”的呢!我鄙夷地瞟了他一眼说:“不是一星级,是五星级!”
我刚换上拖鞋进卫生间洗了个澡,出来时小牛已将我的皮鞋擦得锃亮,并在我自带的水杯里泡上了一杯热茶。我惬意地坐在圈椅上,端起茶杯将嘴唇凑上去,刚吹了口热气,还没来得及喝第一口,腰间那个“屁屁机”吱儿吱儿叫起来。我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拔出呼机,屏幕上显示的一行字是:“陶小北女士请你回电话”,然后留了一个省城的电话号码。这妮子也在省里?我的眸子里像蹿出火苗一样蹿出惊喜之色,下意识地放下茶杯,去抓电话。可一看小牛正伸着一个十分愚蠢的脑袋在看电视,并发出一些比他的脑袋更愚蠢的笑声,我又将手缩回来,扑出去就在服务台给陶小北回电话。
第二十九章
直到和陶小北见面,我俩那种意外的惊喜还依恋在脸上。
陶小北呼我前并不知道我在省里。我接到传呼前,也并不知道她在省里。直到通了电话,我俩才证实对方近在咫尺。
我俩约定在我们共同的母校北方大学见面。
扔下电话,我仿佛已看见陶小北笑吟吟的脸和高唐神女一般婀娜多姿、光灿照人的身姿。下楼时,我高兴得一蹦一跳,就像脚心里装置了弹簧。快乐从心里溢出,到脸上;脸上容纳不下,掉到宾馆大厅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我又俯身将这种快乐拾起来,捏在手中,出来站在街道上,将快乐高高举起——我打个车,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小北飞奔而去。
陶小北是到省里来参加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的。聚会结束,和同学一一告别,心中升起诸多人生感慨,想找个朋友倾吐一番。小北后来调皮地对我讲,起初并没有想起我,后来她限定了一个又一个条件,我这个“幸运的家伙”才凸现出来。她当时限定的条件是:非老公;非同学;非女性朋友;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这四个条件一限定,我这个“幸运的家伙”的面容就从她脑海里浮现出来,于是呼我。她原以为我在紫雪,准备和我煲电话,没想到一下竟将我呼到眼前来了,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所以小北称我们的见面是“上天的安排”;我则称其为“历史性的会晤”。我开玩笑地问小北:是不是那种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多少个小时?
小北“排除法”里有一条:男性朋友排除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我问她:“莫非你有年龄大出十岁以上的男性朋友?”这句问话里竟含有那种“醋意”。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小北对我说,市政府至少有两个局长,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给她打电话。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挂零。两个局长都是市政府开会时认识的。我们紫雪市是北方一个干旱少雨的地区,市县召开的会议比下雨的次数多得多。有些会阎局长亲自去参加,有些会派副职去参加,有些会随便指定一个科长去参加。小北每次去开会,都能照亮整个会场,就像二百瓦以上的大灯泡,出现在哪儿都刺人眼。小北开会时,不是低着头看书,就是画漫画。她很少抬头。只要抬起头来,一准能发现多束目光正从各个角度向她搜索而来。好比是晚上开会,大会议室突然电灯熄了,那么至少有十束手电筒的光束从各个角度照到小北这儿来。那些目光才有趣呢!有的贼溜溜的,有的像怕生的小孩子一样带点害羞的味道,有的火辣辣的,有的赤裸裸的。有一次一个局长模样的人与她隔五六个座位坐在一排,一手拿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另一只手端着茶杯正准备仰脖喝水。在“仰”这一下前,眼珠子一斜,放出一束目光,向正低头画画的小北偷觑过来。此时恰巧小北抬起头来,敏锐地“逮”住了这束目光。她像武林高手放出一件暗器一般,调皮地放出一个媚眼迎局长的目光而去。两束目光在空中“咔嚓”碰撞,局长哪是小北的对手,当下一慌神,脖子一仰,妄图以喝水姿势掩饰对小北偷觑带来的尴尬。可他在放出目光之后,因走神,本已端到唇边的水杯与嘴巴游离开一点小小的距离,此时慌急间一倾杯,水没有倒进嘴里,却倒进了敞着衣领的颈项里,烫得局长眉头都皱了起来,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
那两个大出小北十多岁的局长,与小北认识,一个是因开会时恰好坐在小北身旁。小北正画漫画,邻座递来一个小纸条:“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还有芳名?”小北心想:还想勾引姑奶奶呢!那就和你玩玩吧!当即扭头风情万种地瞥了那位有点紧张的局长一眼,在纸条背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这位局长从此像万里长征的红军刚刚背着背包离开井冈山一样,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给小北打电话。他将小北的电话号码写在一个精心收藏的笔记本上,号码下面还写了一位伟人两句十分平常的话:“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用以砥砺自己。另一位则是有一天突然给她打来电话,那个电话恰好是我接的。对方用温和中带有一丝讨好意味的口气说:“请找陶小北听电话。”小北狐疑地从我手里接过听筒,与对方通了话都不知是何方神仙,哪路诸侯。对方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之后,小北才知是市政府一个很重要局的局长。可小北与这位局长并不认识。以后这两个局长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有一搭没一搭地打电话来。小北说,在他们的百般相邀下,她和他们分别单独吃过一次饭。两人一个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从外包装看,有一股大义凛然的劲儿,又仿佛是坚持抗清的顾炎武。另一个形容委琐,脑袋不大,肚子却不小。坐在那儿,腹间就像搁着一个篮球。从腰腹之间看这个人,有点像纪晓岚。而从形容举止看,则有点像刁德一或者栾平,要么就是引清兵入关的明末辽东总兵吴三桂。小北说,“顾炎武”她不太讨厌,因为这人还算风趣。不过也仅此而已,谈不上喜欢。“吴三桂”她心里其实很讨厌。小北说,这人无趣得很,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保准是问她“最近好不好?”她故意说:“不好!”对方一听她带点孩子气的顽皮,竟兀自幸福的呵呵笑起来。挂电话时又总是说:“有什么办的事情没有?”乍听这话,仿佛天下没有他办不了的事。有一次他忍不住了,引导小北说:“出租车票,吃饭票,总之什么票据都可以拿来,我都可以报销的!”原来他能办的,也就这么些事。小北有点气恼,心想:这不是诱惑姑奶奶上林彪的贼船嘛!那样姑奶奶有一天和你做爱时,身下都仿佛铺着一层出租车票,最大面额才是十元——不是找着“犯贱”嘛!这些想法小北当然不会表现出来,有一次还逗对方:“买皮鞋的票可以报销吗?”对方马上说:“当然可以啊!”话语中有一种喜出望外的味道,仿佛小北真要在他那儿报销一双皮鞋。可接着又说:“不过最好开作烟酒,或者笼统写为纪念品、办公用品。”
小北最后又说,况且若她和“吴三桂”有什么瓜葛,那她自己不成明末苏州名妓陈圆圆了吗?虽然陈圆圆曾“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但她还是不想成为这个晚景凄凉的玉庵道士。
那天我和小北坐在北方大学校园外一条小街一个雅静的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漫无边际地说着话儿。小北说她上大学时常钻进这条小巷吃零食,这条小巷的小吃让她吃遍了。她说:“有一家的擀面皮特别好吃。本来蛇钻窟窿蛇知道,可我今天给你打传呼前,在街上走来走去找了很久,口水都流出来了,却没有找到!”小北说,她当时差点儿就要急哭了。
小北说这些话时,像个娇憨的孩子。我都仿佛能“看”到她当时找不着那家卖擀面皮的小饭馆时,那副惘然和着急的模样。
“我上学时也常在这条小街吃饭,怎么没有碰见你?”我这样说时,心生幻觉,仿佛小北正偎在我肩头,挽着我胳膊,在这条小街上走,在北方大学校园里微风中沙沙作响的梧桐树下走。小北向我撒娇,用纤细的手指头悄悄抠我手掌心……
小北说:“碰见才怪呢!你比我大六岁、高四级呢!”
我说:“大六岁有什么不好?据我广泛调研,夫妻之间最佳年龄构成就是男大出女六至八岁。这种年龄组合有三大好处:一是呵护感。男人总觉得拥在怀里的是个小妹妹,时时事事呵护着她。二是反差小。男人四十岁左右事业有成时,女人刚三十出头。男人最具魅力在四十岁左右,女人最解风情在三十岁左右。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成功人士挽着一个三十岁出头风情万种的妻子,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男人为啥四十岁左右离婚率高,就是因为妻子大都成黄脸婆了。三是爱情生活和谐。男人四十岁时,因事业有成,身体焕发出第二次青春,战斗力极强。女人三十出头,既不像二十多岁时在爱情生活中显出羞涩和抑制,不又像四十岁以后减弱和衰退,既放得开又收得拢,这叫强强联合。两人在一起,能不如胶似漆?”
小北已被我撩拨得秋波含情,春心荡漾,脸颊泛红。可她不甘束手就擒,瞥我一眼说:“鱼氏谬论!”这话明着在反驳我,却似在鼓励我,因此话语像夏日和煦的风儿一样,显得软绵绵的。在我听来,反有那种“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的感觉。
“不是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