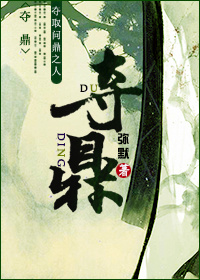纵兵夺鼎-第5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伤病将会给围城军队战力带来巨大的折损。
这雨来得又快又急,虽然是好事,却也令夏侯惇忙昏了头。
成父县不算大城,却临近着汝南东北部北通梁国最宽阔的官道,扼守乾溪谷,是汝南东北面的门户。汝南这地界,对大江之南是易守难攻,但对北面而言却并非地利之地。因为地势,汝南全郡仅有一条沟通东西的路,还是先秦时修的驰道,余下道路皆为南北纵贯,均为山谷水文所阻。倘若以陈国、梁国南下的道路来分,可将汝南分为东西两面,西面北方正对着陈国、东面北方则正对着梁国,东西中间以颍水为界。
单单梁国,可纵兵南下直取汝南东部的官道便有三条,分别为自北向南偏东的城父一线;靠近中间的思善一线;自北向南偏西的新阳、宋国、细阳、汝阴一线。其中新阳、思善、城父三县也正是扼守要道的前沿,是如今曹氏在汝南东部布防的重中之重。
三条路均有近二百里互不相通,要一路向南行至汝阴东西一线才能相互沟通,中间隔着绵延山脉,只有猎手出身的老练斥候才能在两个时辰之内将信息送达,这还是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速度。如果哪条要道遭遇敌情,等待援军至少要三日之后,因为曲折回转的官道,三县之中最近两县的路程都足足五百里,最远的新阳与城父甚至隔着一千一百里路!
不过也因为地势,三条要道均为山谷,虽说援军不利,却也勉强算是善守之地,雨季之前曹氏便在乾溪谷让张辽试探还击的兵马吃到不少苦头。
如今到了雨季,汝南东部便更不必担心燕氏的进攻了,那些山谷在平时尚不易通行,如今天降暴雨,没准不需守军山体下滑便能将整支军队封死在山谷里,谁敢冒这样的险,哪怕是张辽。
但夏侯惇发愁的事情确实很多,比方说因为雨季而带来的运筹辎重困难。因为三条山道的驰援困难,曹氏的大队兵马都布防在位于颍水就近也是汝南正中间道路四通八达的汝阴城,曹操的大营也在那里。从汝阴驰援东面任意城池,都要比三城相互支援近的多。
哪怕再因天时带来的道路难行而感到放心,夏侯惇也必须派人将粮草辎重从汝阴送到他所镇守的三城之中,这本身就是为了防备暴雨而提前要做的准备,但这场雨来得太急太快,最后三队押运辎重的粮队被困在路上,没有准备多余的草席,粮食无法上路,否则运到城池也被泡烂了。
让军士食泡烂的谷子?那样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可想而知。
夏侯惇肩上的担子不可谓不重,过去他主责各郡屯田,历任太守,放在燕氏那边即便算不上沮授那样,也算是司马朗一样的郡中主官,可现在却成了镇守一方的大将……这其实并非是他受到重用,在曹氏这样的正统诸侯眼中,州郡官员才是重用;这是曹氏内部人才不足的体现。
袁氏在燕氏的攻伐下足足撑了十年,直至最后两年才出现这种情况;但曹氏的底子不如袁氏,却接连遭受吕布、陈宫在兖州的反叛,燕氏大举南下的压力,曹仁、夏侯渊等宗族重将接连殒命疆场,虽然有能征善战的战将,却缺了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令人压力极大。
对夏侯惇而言,镇守汝南东北,便是赶鸭子上架,不得已而为之。
夏侯惇非常清楚,因为汝南东北部的地势,燕军如果要打,便一定会进攻这里。眼看过了秋天就进冬月,曹氏有多期望得到年末的修养之机,燕氏想扼住他们的喉咙不给丝毫喘息之机的心情便有多急迫!
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冒险,也不奇怪。
事实不出夏侯惇所料,就在夏侯惇雨季到来之后第三次派人催促运转粮草的辎重队尽快赶路派出骑手时,循着暴雨中传来的马蹄声,思善城外的大营远处官道奔来一骑,尽管眼前串联的雨幕与山雾遮住夏侯惇的视线,单单马蹄声却已足够令他感到不安……那是北方,梁国的方向。
骑手一身庶民装束的短衣已被雨水浸湿满是泥泞,面色苍白显然被雨中长时间疾驰冻坏了,翻身下马通报之后快速入营,这是一名曹氏派往北方的探子。间使快步奔到夏侯惇身前,方才矮身行礼却已不自觉地两腿一软拜了下去,两手撑着泥泞不堪的土地抬头对夏侯惇艰难道:“将军,十七日前张辽在陈国集结兵马开坛祭天,随后北上梁国,由陆梁南下经过谯县,直逼成父!”
张辽的兵兜了个大圈子,从西面的陈国绕到东北的梁国,才经由官道一路悄无声息地南下。夏侯惇微微咬牙,心中盘算着燕氏兵马的行进速度,任凭雨水打击在肩甲后溅在脸上,道:“现在燕氏军到哪了,谯县?”
“回将军,属下出发时未至谯县,现今应已过谯县,克日便至成父!”
夏侯惇紧紧攥着拳头,明日抵达成父,现在阻击已来不及,只能尽快传信汝阴的曹操,再派人向成父守将李典示警!
第二百三十四章 汝南之战()
张辽不在谯县,带兵经过谯县的是高顺。从梁国经由沛国谯县南下成父,路还勉强称得上好走,尽管大雨磅礴,行军稍慢,但实际上这场战争开始的本质是燕氏军对曹氏守军的突袭……高顺半月曲折行军千里,为的就是袭敌不备。双方距离太过接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豫州战场上随处可见的都是探子,要想瞒住曹氏耳目让他们将作战行军当作常规调动,这可不容易。
暴雨是最好的掩护,尽管高顺为保全实力仅让军卒以缓慢的速度行进在官道上,每天都要花上半日让部下就地扎下可遮风挡雨的营地避免军卒感染风寒,但这样的天气对谁都是困扰。对燕氏军、对高顺部如此,对曹军、汝南守军、遍布豫州的曹氏间使亦如此。
所有人都被搁浅在这场暴雨里,怀揣非常之意的高顺便能从中得利,这便是张辽对汝南作战的第一个思量。
雨季作战是铤而走险,但既然是冒险,便必然有得到巨大利益的可能,张辽在东部战场所要的利益,便是尽数占领汝南东部三条南北纵贯的要道,以取得直接逼迫汝阴曹操大营的威慑力。
只要高顺在汝南东部钉死万余兵马,这场仗便毫无悬念。
进入汝南境中的燕军足有三万,皆受高顺节制,除其部下三个精锐陷阵三千营,余下兵马为春季从兖州募到的新卒与先前中原战场上退下去整编的司、冀老卒,兵员成分杂乱,战力于燕军当中亦算不得上乘,均不过中下之资,与兵甲上也讨不到好。
绝大多数人仅有皮甲、皮弁,短剑、矛戈,远程力量同样多数装备硬弓、轻弩,都属于燕氏主力军队弃置不用的武备。
但这也是天下诸侯军队的中坚力量。
所幸,高顺还有三十架石砲,依靠三十架石砲,攻关陷阵。
转眼之间,兵行道间,扼住山谷的城寨遥遥在望。
高顺集中兵力,派遣两个校尉部的军士扼守住中、西两处进入汝南境内的道口,接着挥师大部攻击乾溪谷,直逼成父。成父守将李典在半日前收到来自山那边夏侯惇的消息,但时间显然已来不及派兵扼守山谷……这样的天时,山谷上没有人尚且有滑坡坠石的危险,守军难以攀登,与其出城营地被半路截击,还不如扼守城郭等待援军。
援军,成父必须需要援军。曹军的兵力在长久的战争中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全郡仅剩两万余兵马分散于各地,李典部下不过仅有军卒四千,出城便毫无还手之力,但凭借城池,尚可一战。
暴雨会代替刀剑给敌军带来无与伦比的打击,守备城池至多七日,成父若还未陷落,敌军便会因寒冷病痛而退军。哪怕不退,守军也会拥有一拼之力。
但面对接近十倍的敌军,守备七日又谈何容易?
援军,至少还要再派三千援军。
成父城北,李典早先立下三座城磐,以高耸的山壁为基,厚实木垒原先不过是作为前沿哨站,毕竟木垒最惧火攻,可偏偏这天降暴雨对李典反而成了优势,当即在收到张辽发兵南下进攻的消息后引军北上,接连越过两座城砦,将兵马陈于当先。
后方两座城砦一座城池,仅仅驻留了几百人,征募民夫分配矛戈加急操练。
李典深知,单凭三座简陋的木垒城砦是挡不住张辽的,如今这般困兽犹斗也不过是拖延时间罢了,就连李典自己也不知道三座木垒究竟能拖住张辽大军多久,但他终归是知道,以小兵抵御燕军大部成父城的攻守……已是无可避免。
曹军进驻三寨后的一个时辰,两支以奔驰驴车、驮驴为前锋的千人队进入山谷,冒着雨季滑山的风险攀上山壁,分散伍什扼守各处险要,以车架所携木具快速于山谷平坦处扎下简易望楼,形成星罗密布的防守网。接着不过半个时辰,两个兖州郡国兵校尉部进驻山谷,在距离曹氏三寨最近不过十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旁若无人地大兴土木。
他们像过去袁氏的匠作营一般,以早前扎好的望楼为角,快速夹木垒土,区区一个时辰便建起一面寨墙。一个时辰,是高顺小心翼翼估测出的时间。
曹氏从三寨出兵至此,骑兵急袭仅需一刻,步卒疾行则要半个时辰,而前后探马回报则又要一刻时间,再有一刻犹豫。倘若曹氏守军趁燕军未能扎寨急袭至此,这个时间刚刚好让高顺的前线军队扎下一面并不牢固的寨墙用以防守……只需再拖上半个时辰,便有源源不断的援军赶到。
事实也和高顺的考虑相同,守备城砦的李典并非没想过趁燕军远到轻袭一阵好鼓舞军心,但第二次派出探马回报时燕军前阵便已扎下望楼,少兵不足以取利,大兵则难以回防,这着实令李典犹豫片刻。就这犹豫的片刻中,第三轮回报的探马便已将燕军两个校尉部进驻山谷开始扎营的消息传回城砦。
错失良机。
暴雨中往来探马不断,燕军一道道消息传回城砦,扎下半面寨墙、又进驻一个校尉部,极快的时间里,燕军便已向山谷中扎下上万兵马,李典袭击营寨的心也散了,当即传令军士同时在城砦之外布放陷阱以拖延敌军即将到来的攻势。
李典想的就是尽量拖延燕军的攻势,他有三座城磐可以去拿去丢给燕军,只要能在数日中且战且退,最终在援军抵达之前守住成父城就足够了。待到援军赶到,成父城驻军上万,便有能够驱走燕军的底气。
一万守军凭借城池守住三万敌军的攻势,并不困难。即使燕军有每逢攻城必有石砲出战,李典也不为此感到担忧。成父城外绵延的山势能够最大程度上抵消燕军石砲的优势。何况……他手里也有十几架石砲架设在北面瓮城上,毁了敌军石砲,把战事拖进冬季,打不死敌军也能冻死他们!
左右燕军,一定比他们急!
第二百三十五章 汝南之战【三】()
高顺真的不急,他心里比李典要轻松多了,哪怕在行事上他一定要做出迫切需要攻下成父城的样子,但他心里一点都不着急。成武城攻下自然很好、攻不下,也没关系,那并非他的使命。
倘若被曹军看见中军帐里常坐之人一定会感到奇怪乃至心惊胆战,营寨分明悬挂张辽的大纛,可大纛之下的中军帐却属于高顺……张辽根本没参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