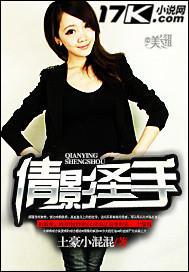孤灯倩影-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客栈掌柜惊醒过来,一紧手中剑,身随念动,一剑划向杨惜芳,剑势凌厉,劲风飒然。她早觉出他身手不凡,所以不求伤敌,先谋脱身,却也没想到厉害至斯,说到便到。
她经过先前的负伤逃逸,早已疲惫不堪,不敢直撄其锋,只得再退七尺,避开来剑。客栈掌柜早料到她有此反应,剑尖一挑,又斜划而至。杨惜芳退无可退,贝齿一咬,双手握剑,硬挡他一招。嗤,哐啷。客栈掌柜的剑断为两截,而她的剑也被震飞,斜插在床前,兀自晃荡不止。她被震得摔在壁上。
客栈掌柜拿着半截剑,小心翼翼地走向她,阴阴地说:“江湖传言杨小姐风华绝代,武功盖世。姿色,嘿嘿,倒确是极品,这武功嘛,嘿嘿,不过如此,我说的对吗,杨小姐?”
她只觉喉头一甜,哇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挣扎着想站起来,却浑身疼痛无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恶人走向自己。她知道这无耻之徒想要做什么,她的心却没有一丝惶急,她在想:“容与,你在那里?我就要死了,我们只好来生再见了。”心下伤痛,又呕出些血来。她闭上眼,感觉到客栈掌柜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拼命地凝聚功力,运于左手食中二指,二指慢慢地逼向膻中穴。客栈掌柜每走近一步,她的功力便增加一点,距离膻中穴更近一点,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永别了,容与!”
二指凝结了足够的力量,正要戳下去,吱一声响,自窗外钻进来一人,急扑向床前的剑。客栈掌柜一惊,手中断剑掷向来人,同时,纵身向床边掠去。杨惜芳停住了二指,却没有想过今天还有活路,她依然凝聚着功力,等待死亡。黑暗中,客栈掌柜和来人交上了手,双方都毫无保留的痛下辣手,希望尽快置对方于死地,瞬息间,以快打快的对拼了十几招,从床边直打到门边,俱为对方的强悍震惊。久斗不下,双方的攻势不约而同的稍缓,都有意的向潮退靠去。二人都存了这样心思,当然竭力使对方不能靠近,如此一来,二人谁也不能得逞。便在这时,窗棱响处,又一个身影扑了进来。此人顺下扑之势,在地上连滚几滚,已然到了床前,正欲拔剑,打斗中的二人陡然一起攻向了他。他不及拔剑,跳到床上,掀起被子抛向二人。二人躲避不及,被罩在被下,一阵瞎抓乱扯,没有弄开。后来那人拔出床前的剑,运力一挥,惨白的剑气闪耀而出,被下二人没了声息。
那人也不睬地上的杨惜芳,挟剑奔向窗户。正行间,突觉面前空气有异,百忙中,提气上跃,堪堪避过那无声飞来的暗器。那暗器好似长了眼睛一般灵动,眼见得去势将尽,却又呼地旋了回来。那人心中一凛,听声辨位,挥剑砸向暗器,眼看要砸上,那暗器又绕了个弯,才主动撞在剑上。那人剑势未尽,暗器又顺势推了剑一下,巨力传来,那人只觉虎口剧震,潮退脱手而飞,又斜插在床前。
那人顾不得再要剑,身体腾挪,撞破屋顶,仓皇而去。
杨惜芳潜聚着力,平静地等着有人进来,拾剑而去,却久久不见有人来。她终于放下二指,挣扎起来,点灯,收剑,收拾行李,弄醒人小,连夜离开了姚记客栈。
人小为她另找了家客栈。开门的伙计嘟嘟嚷嚷的,说什么天寒地冻、三更半夜的鬼话,人小递给他一锭纹银,他立刻换了张笑脸,招呼二人。
第一卷 第四章暗波隐隐
心似双丝网,
中有千千结。
——张先《千秋岁》
终于有了片刻的安宁,杨惜芳只觉肩上疼痛难当,先前在逃避中还不觉得怎样,此刻痛楚传来竟是一阵胜比一阵。她撕破伤处衣衫,只因伤在肩背上,自己勉强能看到,说到处理却是无可奈何的。她紧咬牙关,因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的脸更加的苍白了。她觉着好烦,暗恨自己往昔练武时疏懒,心不在焉。平素师父只传她功夫,却从不督促她习练,由得她心意。现今想来,她没有恨师父的意思,只是责怪自己。她想叫人小进来为她处理伤口,心底又不大愿意,先不说男女授受不亲,她实在不能接受除那个他外的男人碰到她的身体,但不叫人小吧,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什么人来帮忙。她好矛盾!她好烦恼!她好恨伤她的人,好恨觊觎潮退的人。她左手紧紧扯住右肩,指甲深陷肉里。犹豫再三,她到底开口叫了人小。
人小推门走进来,没有惊讶自己的主人受了伤,也不问她怎么受的伤,只低垂着头,听她吩咐他该怎么做。她看了他一眼,强作镇静的告诉他先想办法取出暗器,然后敷上些金创药,包扎一下就可以了。他唯唯诺诺地答应了。她没有说怎么取暗器,他也不问。他走到她身后,颤抖地从怀中取出一只精致的白色瓷瓶,拔开塞子,将里面的液体滴了几滴在她的创口处。她觉得一股清凉的感觉自伤口传来,直沁心脾,便没了痛楚。她问人小滴的是什么,他不言语。收好瓷瓶,摸出一只锦盒,掀开盖子,只见里面放着十几根长短粗细不一的银针。他捻出两根较粗的,使筷子般夹在拇指、食指和中指间,试探着把针伸进伤口,夹住暗器,微微用力,快捷地将之挑出。虽然,有他滴的液体消除痛感,可暗器出来的刹那,她还是痛地哼了一声,那自是暗器的缘故了。他被她的哼叫吓了一跳,针及暗器一起掉在了地上。
原来那是枚拇指般大小的铁锥,铁锥做的十分精细,锥尖细小锋利而有四方倒刺,倒刺同样的锋利,倒刺有分叉和侧刃,分叉增加伤害,侧刃防止倒刺影响铁锥刺入肉里。倒刺上还挂着她的血肉,更显得异常的恐怖骇人。见着此暗器,她的心不由自主的狂跳了几下,喃喃道:“附骨锥?天下竟有如此可怕的暗器。”
人小在心里叹息。他知道,尽管自己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六七年,经历了无数的江湖风云,他还是有着太多的幼稚,太多的一厢情愿了。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江湖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逃不掉的。他知道他的计划不得不改动了,他决定该做点什么了。他一时想得出神,忘了给她包扎伤口。
她问道:“人小,你在想什么?”他回过神来,说道没什么。看着她雪白的肌肤,又不自觉紧张起来,双手颤抖却又熟练地为她洗去伤口四周血污,敷上金创药,包扎好伤口。
人小出去了,她兀自发呆。她不奇怪人小有那些疗伤的物事,不奇怪人小会那么的熟练,她只奇怪人小的手碰到她肩上的肌肤时,心里竟会泛起些一样的感觉,那样的心醉而又那么的熟悉,仿佛她的容与第一次用手抚摸她脸庞时的感觉。唉,容与。她的心一痛,随即责怪自己,为什么责怪,却也说不上来。
唉!她叹了口气。她把潮退放在桌面上,看着这柄看上去与普通的剑没什么两样,却已让自己到鬼门关走了几遭的所谓宝剑,耳中似乎响起了师父垂危的嘱咐:
“芳儿,潮退一出,必惹风波。那人当初送给为师潮退,便即引起江湖的腥风血雨,无穷祸患,为师也因此与他落得劳燕分飞,鸳鸯难谐。你要记住,为师去后,你代为师将它还与那人吧。你本已遭遇太多的不幸,为师不希望你的人生像为师一样沾满血腥。唉!”
师父的叹息犹在耳边,经过这些日子的打打杀杀,她终于明白师父的良苦用心,她想:“师父是希望我好好的活着。”唉!神兵利器有什么好,自古以来就是不祥之物,可叹无数江湖豪客执迷不悟,枉自丢了性命。她又想:“师父与那人分手,可以说是因为一把剑的缘故,然则容与他离开我是为什么呢?”胡思乱想一会,倦意来袭,她熄灯就寝。一宿无话。
因着有伤在身,况且要事未了,她也便在这家客栈住下。人小自然不会违拗于她。
这一日,人小待杨惜芳用过晚饭,像前几日般到酒店喝酒。
桌上放着一大坛酒,一只小酒杯,——他不习惯用大碗。他垂着头,坐在靠窗一隅。酒杯里倒满了酒,他却迟迟不举杯,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又好像在凝听什么。
只听一个脸皮焦黄的汉子说:“听说足迹从不到北疆的‘东海午夜剑’宗少名已经到了风镇,好像为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一个瘦削的汉子接道:“前些日子,我倒瞧见了。宗少名穿一身珍贵的雪白貂裘,披一件玄色披风。跟在他后面的有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夺魂玉面’汪言,据说是宗少名的关门弟子,极得宗少名宠爱,武功在同门师兄弟中无人是其敌手,而那女的是宗少名的幼女;叫宗毓秀,是宗少名小妾所生。”
“那叫什么秀的,水灵灵的,长的真他妈的俊啊。”一个长着两撇八字胡,神情猥琐的汉子突然道,“那细腰儿,水蛇似的,那脸蛋儿,真他妈想捏上一捏。江湖上说那姓杨的貌美如花,却未必便赶得上这妞儿。他妈的,要是能弄到手玩上两天,那可才真叫爽。嘿嘿。”
先前二人陪着笑道:“尤兄,你不要命了。”二人随如此说,却也没见着担心的意思,倒是不把宗少名放在眼中了。
姓尤的嘿嘿干笑一声,喝下一杯酒,道:“别人怕他宗少名,老子可不怕他。妈的,这里是我尤二的地盘,不跟他为难算是看得起他了,还怕他怎的。”
人小举杯,小呷了一口。
脸皮焦黄的汉子说:“这个当然,再怎么说,天给他宗少名一百个胆,他还不敢开罪沈老。”嘴上这么说,心中却道:“‘塞外孤星’固然厉害,‘东海午夜剑’却也未必好惹。”
瘦削汉子和尤二不言。又喝了会子酒,瘦削汉子道:“依我推测,姓宗的也必听说了那把剑的讯息。他姓宗的也是使剑的人,岂有不动心之理,再者说了,凭他姓宗的一句话,随便遣几个弟子走一趟,怕还没多少办不了的事,何必寒冬腊月的亲自跑来。”
脸皮焦黄的汉子和道:“刘兄言之有理。这些天风镇的气氛可有点不大对,不单姓宗的,还来了不少有头有脸的江湖人物,其中不乏像‘蓝衣毒神’、‘多情附骨’等蛰伏多年的老怪物,恐怕或多或少都是为剑而来的吧。”
尤二沉吟半晌,道:“别人不好说,宗少名倒未必为剑而来。”
二人问道:“尤兄,这话怎么说?”
尤二道:“十年前,家师远赴江南,遇宗少名在扬州相遇。姓宗的和家师客套几句,就邀家师过招。当时家师有要事在身,耽误不得,便与姓宗的订下十年后在酉城一决高下的约会。宗少名这次来北疆,应该的赴家师的约会来了。”稍顿,又说:“这事家师极少提起,原是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二位务必保守秘密,否则家师怪罪下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二人忙说:“兄弟理会得。”
尤二嘻嘻一笑,又道:“哈哈,他奶奶的,好久不曾听得如今那妞儿的箫声了。刘兄,萧兄,等这里的事半完后,一起去酉城听他娘的个痛快,如何?”
脸皮焦黄的汉子道:“坊间传闻这个如今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容,果然当真吗?”
瘦削汉子道:“萧兄,你才从中原回来,所以有所不知,那如今既然入得尤兄的法眼,姿色自然不在话下。”接着对尤二说:“尤兄,兄弟有说错吗?”
尤二满脸淫笑,对姓刘的话不置可否,却道:“可惜啊,可惜,他奶奶的,动不得。”
二人愕然问道:“为什么?”
尤二也不解释,只招呼二人喝酒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