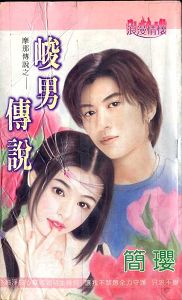战族传说-第6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牧野栖赶紧翻身坐起,心中暗自嘀咕:“为何只见一人?”
那汉子一见卜贡子,脸上立时有了惊喜之色,张了张口,似乎要说什么,话未开口,脸
却已更显紫红!他突然“扑通”一声跪下,声音嘶哑地道:“师父,你一去十年,又无人能
知师父行踪,弟子还道……还道…”
他这么一跪,牧野栖立见在衣四方的身后还站着一个人,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女孩,扎
着一对冲天小辫,正将自己的一只手指放在口中吮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飞快地转动,一会
儿落在卜贡子身上,一会儿又落在牧野栖身上。原来与衣四方同来的竟是一个小女孩!
卜贡子脸上的笑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接过衣四方的话语,道:
“你还道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师父了,对吗?”
牧野栖初时还以为卜贡子真的恼怒了,但细加留意,立即发现卜贡子的脸上虽然再无笑
意,但他的眼神中却仍有难以掩饰的喜悦!
衣四方忙道:“弟子不敢!”
卜贡子语气平淡地道:“为师不在身边,你岂非清闲自在多了?我传给你的刀法多半也
忘了吧?”
衣四方不安地道:“这十年来弟子从不敢懈怠,只是弟子天资钝愚,恐怕有负师父厚
望!”
卜贡子道:“你也不必大过自谦,方才我听你的脚步声,快而不乱,就知你的内力已增
进不少,况且你有资格面见主人,说明这些年来武功定然精进不少,你起来吧。”
衣四方依言起身,牵过身后的小女孩,道:“这是婧儿。婧儿,还不拜见太师父?”
那小女孩倒也乖巧,双膝一曲,便要跪下,卜贡子当即双手微扬,一道柔和的劲道飘然
而出,正好将小女孩的身子托住,口中喝斥衣四方道:“这是你收的徒弟吗?不好好教她武
功,却让她磕拜,拜得全没了骨气!”
婧儿忽然开口道:“婧儿从不胡乱跪拜的,婧儿只拜爹爹与主公老爷爷。”言罢,她噘
着嘴,似乎对卜贡子的话甚为不满。
卜贡子一怔,随之哈哈一笑,颇有些惊讶地道:“四方,原来你竟成家了。”
高大雄魁的衣四方神色显得有些不自然,他磕磕巴巴地道:“弟子不曾成家,婧儿她……
她……是弟子的义女……”
卜贡子恍然而悟,点了点头,道:“这孩子倒也机灵。”
言罢,他下了床,整整衣衫,这才对衣四方道:“四方,这是主人新收的弟子,将来照
应少主人的重担,多半会落在你的身上了。”
衣四方一惊,飞快地看了牧野栖一眼,迅速垂首,恭声道:“白道端木总领麾下高字堂
天级弟子统领衣四方参见少主人!”
牧野栖赶紧起身还礼,急声道:“晚辈怎敢担此大礼?”
对衣四方的一长串头衔,他一时也未能弄明白。正当此时,忽听得天儒的声音清晰地传
入众人耳中:“贡子,黑白二总领及八大堂主皆在若愚轩,你将小栖领来吧。”
牧野栖神情一肃,低声道:“师父也来了。”就要开门迎接,卜贡子却哈哈一笑,道:
“主人还在若愚轩呢!”牧野栖顿时瞪大了眼睛。
卜贡子脸带崇敬之色地道:“主人神功盖世,能凝声成形,又有何奇?黑白总领及八大
堂主齐聚若愚轩,定是主人要将新收弟子之事告之众人。黑白道上有两大总领,一是北侧白
道的端木总领,另一位则是南侧黑道的敖总领,两大总领麾下各有四大堂,端木总领麾下为
‘高、山、流、水’四字堂,而敖总领麾下则是‘阴、睛、圆、缺’四字堂。齐聚两大总领
及八堂主,是极为罕见之事。”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四方,你虽得主人恩准涉足此间,
也不应久留,还是速返自己所在之地吧。为师返回之事,是‘生死二司仪’告诉你的吧?见
了他们,代为师向他们问候一声,他们的修为可是越来越出神入化了,为师经过‘归去亭’
的时候,可没发现他们的行踪!”大概他与所谓的“生死二司仪”颇为投缘,言及他们时,
嘴角处又有了笑意。
牧野栖一边随着卜贡子往外走,一边思忖着:“赶赴‘若愚轩’的途中,的确曾经过一
处凉亭,似乎就在七里之外吧,至于是否就叫‘归去亭’却没有留意,更不知那儿有什么生
死二司仪!这一路过来,一直风平浪静,除了路途两侧屋子颜色奇特外,再无异常,没想到
事实上这十里路中却是包罗万象,玄秘莫测!”此时他才忽然发现江湖中极少有一眼便可以
看透的事。
※※※
戴无谓颓然顿坐于地时,恰好响起一位女子的喝问声。
喝声甫落,众人眼前一花,楼上已多出两位美貌女子!其中一人略为年长,身着红衣,
秀美无伦,眉如青山,鼻若凝脂,头上束着堕马髻,高耸而侧堕,身材美妙,蛮腰纤细,玉
颜修长。最让人心动的是那双有种意态慵闲的风情眸子,让人一见,顿生爱怜之心,为她的
娇慵之风韵所倾倒!这是一个让人很难判断年龄的女子!
另一女子甚为年轻,容貌却反而略逊一筹,但她的身躯却成熟得让人惊心动魄,让人一
见,便想到她的年轻与活力!
两女子见眼前一片狼籍,地上更有人倒于血泊中,不由齐齐一惊!
她们的目光落在了戴无谓身上,略为年长的红衣女子道:“你就是戴无谓?”语气甚不
友好,对戴无谓这样年长她许多的前辈,竟直呼其名!
关东三义之徐达怒喝道:“好刁蛮无礼的妇人!戴老先生乃武林前辈,岂是可以直呼名
讳的?”若说他先前称戴无谓为前辈多少有些敷衍,然而在见识了戴无谓的惊世身手后,徐
达的这一称谓,端的是发自内心肺腑了!
那红衣女子冷哼一声,道:“世间最不可原谅的就是那些以高人前辈自居之人,他们以
为公道正义在手,恨不得判定世间一切是非善恶!”
戴无谓缓缓睁开眼来,缓声道:“姑娘就是残害阎公子的人吧?”他说得很慢,显见其
伤势极重!
红衣女子冷笑道:“可惜那贪色可恶的阎公子是冒犯了我的小师妹,若撞在我手中,只
怕他早已没了性命!戴无谓,据说你处处为人士持公道,为人正直,今日方知你是混淆黑白,
欺名盗世之武林宵小!为老而不尊,可笑可叹!”
戴无谓微阖的双眼倏然睁开!红衣女子但觉戴无谓目光如电,锋芒逼人!分明是唯有绝
世高手才会有的气势,不由大惊!定神再看,戴无谓已回复了他的谦和平凡!一时间,红衣
女子转念无数!
幽求忽然冷冷地道:“能够击伤我的人,怎会是武林宵小?你不但辱及了戴先生,也辱
及了我!”在幽求看来,戴无谓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辱及了他的对手,刘他而言,也是
一种污辱!
红衣女子侧目一看,目光正好与幽求的眼光相撞,那是战意汹涌的目光!幽求高大伟岸
的身躯、狂傲无限的眼神,让她猛然意识到这白发怪人绝对不是一个平凡之人!世间再难寻
找有如此可怕战意之人!而能成为他对手的戴无谓,岂非也应是不平凡的?
红衣女子目光一闪,忽然轻笑道:“恕小女子眼拙,竟识不出尊驾是何方高人!”
幽求的嘴角犹带血迹,但他是一个永远也不愿在别人面前示弱之人,他强抑内伤,尽力
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晰明了:“你可能识不得我,却应该听说过数十年前扫荡洛阳剑会的
人!”
红衣女子闻言一怔,随即眼中寒意渐炽,她声冷齿寒地道:“此言当真?莫非你是虚张
声势?”
幽求狂笑一声:“我幽求何需假他人之名?”
红衣女子神色更显凝重,隐隐有股愤恨之色:“那么,你是否还记得在洛阳剑会所杀害
的人?”
幽求淡淡地道:“那一次死于我剑下的超过百人,我如何记得清楚?”
此言一出,众人皆已色变!一日之间,杀人逾百,该是何等残忍无道啊!
正 文 第七章 绝世战意
第七章绝世战意两股截然相反的气劲悄然席卷而出,一正一反!此乃“素女大法”中的第三式:销魂荡
魄!
幽求正待乘势而进,忽觉自己身躯如同置身于漩涡之中,一正一反两股力道使他身不由
己地向一侧飘然斜跌出去!
旷古剑客幽求怎能任人摆布?虽是内患混乱不堪,却仍强提内力,右脚尖蓦然下压,顿
时木质地板如同被巨力划过,纷纷断裂!而幽求的身躯已在曲伸之间,如同一支利箭,反射
而出!“啪‘地一声,秦月夜闪电般在幽求的身上击了一掌。
但,随即倒跌出去的却是秦月夜,她的身躯如断线风筝,狠狠地撞倒了一处屏风,方止
住去势。她的腹部骇然插着一根木条!木条有三寸宽,鲜血汩汩流出,一时难以看清插入有
多深,伤有多重!
幽求被秦月夜击了一掌后,亦狂喷了一口热血!本就苍白的脸色此时更为可怕!
原来,幽求在以脚尖划开地板时,急中生智,悄然挑起一根木条!他以腿御剑的武功已
是出神入化,秦月夜尚未反应过来,已然中招。
幽求缓缓抹去嘴角的血迹,声音略显嘶哑地道:“小木,此人剑法甚为独……特,似欲
将刚柔融……融为一体,只是修为有限,未能成功。嘿嘿,试问世间,又有几人能真正地集
至刚至柔于一身?能将二者之一发挥到颠峰之境,已足以……咳咳……足以傲视天下!”
幽求不顾自己伤势甚重,对小木临场施教,众人的注意力顿时齐齐被小木吸引了过去!
众人心中皆忖:“此子多半是幽求的弟子,然而看他此时神情,竟毫无担忧之色,似乎对其
师伤势漠不关心,倒也奇怪。”转念一想,幽求视他人性命如草芥,有其师必有其徒,此子
多半是残酷无情到了极点!倒是幽求对此竟也不介意,仍不顾伤势对他加以引导,他们师徒
二人可谓真是人间奇物?!
当秦月夜的目光落在小木身上时,心中“咯登”一下,暗自惊诧:“此子好生面熟,难
道我曾与他见过面?”一时之间,却没有想到眼前淡漠的小孩会是范书的儿子。秦月夜与范
书夫妇二人皆相识,此时看见他们的儿子,自然有相熟之感。
秦月夜的小师妹见师姐受了重伤,忙拔剑护于秦月夜身前!秦月夜一咬银牙,猛地拔出
腹中木条,立时鲜血狂喷!她出手如电,封住了伤口周遭几处穴道,鲜血这才止住。饶是如
此,她的脸色亦已苍白如纸!
徐达、韩贞对视一眼,心领神会,齐齐向幽求悍然扑出!身在空中,已“呛啷”一声,
拔出兵器!一刀一刺,挟破空之尖啸声,向幽求暴卷而去,白宁蒙之死让他们积怒难捺,再
也顾不得武林规矩,要趁人之危了。
幽求一声冷笑,傲然而立,直到刀刺即将及身,方蓦然而动!由极静至极动,仅是电闪
石火的一瞬间!就在这一闪即逝的一瞬间,徐达、韩贞已各中一腿,颓然倒飞!落地之时,
徐达、韩贞只觉体内如同翻江倒海,奇痛无比!二人牙关紧咬,方未喷血!若是幽求未曾受
伤,这一腿足以让他们死上数次。
一个照面即败下阵来,徐达二人顿时有些踌躇,这倒不是因为惧怕死亡,而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