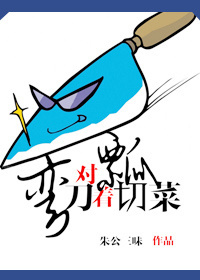吉诺弯刀-第5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
当我再次经过墓地时,发现那里的篱笆墙已经被一帮修铁路的工人拆除了,大片的罗盘葵已被割草机砍掉。
当地人告诉我,政府正在修一条复线铁路干线,经过冬湖小镇。一条是货运列车专线,一条是旅游客运专线。前者负责把这个地区的丰饶出产运往外地,后者负责把外地蝗虫般的游客运入这里的大自然。
我看了挂在镇政府平房里的建设规划图,悲哀地预期:未来几年之内,想必剩下的罗盘葵也将会被无情地翻卷到割草机的料斗里,然后挣扎着被腰斩、粉碎、死掉。
这也就意味着墓园旁边的大草原,终于进入了毁灭期。
大草原的时代将会永远终结。
事实上,罗盘葵们的命运,也是本地土生植物群集体葬礼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世界植物群葬礼的一个缩影。
生活在机械化时代的人们不会注意到大量的植物群落正在无望地死去。
他们只会为经济发展而感到骄傲。我想说的是:愚蠢的骄傲。
当地农人告诉我说,一般情况下,某地的农场越是富足,周围的植物群就越是匮乏。
有的农场主甚至会使用喷火器和化学喷雾器来清除杂草,把草原改造为新的农田,也减少杂草对庄稼的营养争夺,减少病虫害传染的可能性。
但事实上,多年的跟踪研究却发现,对杂草铲除越彻底的农庄,庄稼的产量就越是不尽如人意,而病虫害的干扰也就越是不胜其烦。
但人们已经走上了这条与大自然为敌的道路,人心失教,积重难返。
大自然日渐枯萎在我们追求盲目发展的癫狂脚步下。
可怜的罗盘葵,守护了小镇死者们的亡灵这么多年,最后却没有得到人们的回报,自己也灭绝在了“历史的车轮”下。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的一幕悲剧。
(二)
逸晨先生告诉我,罗盘葵看似脆弱,其实生命力非常顽强坚韧,它只能被铲除,无法进行移植。
当地人说,它们的根系广布整个墓地。如果你想完整地挖一株罗盘葵离开土壤,那你很可能会发现,你需要挖开所有的墓葬。
它们的生命力也很旺盛。野兔啃咬,各种昆虫吞噬,人工伤害,都无法让它们从这片土地绝迹,死去的只是枝条和花朵,作为花的整体体系,它一直都在大地下坚强地存在着。
“活人虽然看上去比较厉害,但归根到底,活人是无法战胜死人的。”当地人这么说。
死亡不可战胜。这就是人们的普遍观点。尤其是唯物主义的普遍观点。
为了验证不可移植说,我邀请逸晨先生一起去墓地,实地挖掘一株罗盘葵做个试验。逸晨先生欣然应允。
我们带了一把登山小铲子,来到墓地的一个角落,在那里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棵罗盘葵的根系向下挖掘。
随着泥土坑越挖越深,我惊讶地发现,罗盘葵的根系在地下的战略布局,真是规模庞大到不可思议。从它的主根,至少分出了数百个根系,随之又分支出数千个枝丫,这样分而又分,一株罗盘葵在地下的网络纵横交织,复杂得如同西游记里的盘丝洞一般,若要把它所有的根系全部挖出,可能真的要如当地所说的,需要把整个墓园都翻个底朝天。这一株罗盘葵的根系,又与别的植株的根系彼此连结交错,互相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要挖出其中的一株,就必然会要连带拖出其他许多的植株,它们之间,完全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
我亲眼看到,这株罗盘葵的主根系,笔直地穿透了地下的一块岩石,从岩石的另一端钻了出来,又粉碎了岩石下的另一块长石,让它裂为无数碎块。这就意味着,这株植物的根系,也与大地深处的各种物质连结成了一个整体,如果要挖出它,必定要搅动整个地下的世界。
因此,挖出一株罗盘葵,的确是个浩瀚无边、牵连无限的巨大工程,除了切断它的根系,把它弄死之后拿出泥土之外,实在是没有办法让它完整地活着离开这片土地。
经过亲眼目击,我完全信服了当地人的说法,也完全相信了逸晨的劝告:罗盘葵看似脆弱,其实非常强大,它只能被消灭,无法进行移植。
我在挖出的泥土坑边坐了下来。想不到一株小小的植物,都是这样背景深厚,不可动摇。
逸晨先生也在我的旁边,和我并肩坐了下来。
他说:“你看,挖出一株这么小的植物的根系,都是这么浩大的工程,更何况要根除内心的一个心结呢。”
我看着逸晨。
他说:“殊非易事啊。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我们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消除对于往事的心结,也就像要清除这罗盘葵的根系一样,复杂而艰难吧。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现在意识到,逸晨先生也许不是随意地对我说起罗盘葵的移植。他也许就是想要引导我来看看这盘根错节的地下世界,这也就是我们纠结紊乱的内心世界吧。
我心里涌起深深的感谢。
(三)
大自然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在一切事物上,都在对我们施以教化与启迪。
但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灵性,有没有这样的慧眼,可以看到它无字的教化,可以聆听到它无言的教诲。
第九百五十六章 春夜挽歌
(一)
气温进一步回暖,屋顶上的冰坡不断退后,整夜屋檐下都响着冰棱融化的滴答水声。就连晚上也可以出门散步了。
森林里的各种动物也活跃了起来。
日落以后,林间小路上烟雾弥漫,每隔一小段路就有一对花尾榛鸡飞起来。整片树林都在暮色中叽叽咕咕地说话。
初春季节里的花尾榛鸡,充满了渴望交流的激情。它们特别喜欢听长笛吹奏的声音。
我们常常以此逗它们取乐。
每每沈先生在营地里吹起银色闪亮的长笛时,花尾榛鸡们便会从雪地冰层上摇摇摆摆地跑来,停在我们营地的大门前和土墙上,歪着头倾听一会儿,发出各种低吟和评论,与笛声遥相应和。
有时,它们跑得如此之近,几乎伸手便可捉到!
真是很感动它们这么信任我们。
夜晚的天空,浓云飘散,再现繁星灿烂。
夜晚的森林,严寒消散后,则变得杀机四伏。猫头鹰每天都在林子的深处,唱着四三拍子的咏叹调,哀叹生命的无常易逝。
逸晨先生听到这凄婉的咏叹,便会感慨说:“身为禽兽,难得善终啊。”
伴随春意的到来,传统的狩猎季节又要开始了。
镇子上的游客人数正在逐渐增多。
冬季的萧条和安宁,日渐随风远去。
春天空气里萌动着的勃勃生机,也吸引着我放下案头的写作,更多地投入户外活动。
沈先生老是觉得我整个严冬猫在小屋里埋头写作的时间太多。他反复地提醒我说:“薇罗里卡,你是来营地度假的,不要总是像还待在写字间那样玩命地工作。”
他说得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些埋头写作的日子,看上去太不像是度假生活了。
然而,写作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却并非“工作”二字所能含摄。
它是我毕生的夙愿。是我献祭自己的一桩圣事。
(二)
我喜欢在祥和的月圆之夜,和逸晨先生走出度假木屋去镇子周边散步。
我们随意地闲聊着,凝视着皎洁的月色,还有被月光洗涤过的雪地。
逸晨很感慨冬去春来的种种变迁中蕴含的时间飞逝。
他告诉我,古书上说:一块地你种上六年,第七个年头让它休闲,如此一轮七年,轮过七回,就到了你的五十岁了,那一年,就叫做禧年。
他说:“不知不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都已经过去了。儿子都快长成小伙子了。而我,也很快就要到自己的禧年了。”
是啊,就连我,也已经活过了你去世时的年岁。
我现在的岁数,比你还要大了。
我们站在镇子里的一处高坡上眺望远方。
夜色中的城郊,纵目望去有三重亮光:上面是蓝莹莹的星斗,地平线上是大城市里居民区较大的昏黄灯光,近处是冬湖上渔人的几近红色的盆火。
湖水快要融冰了。
逸晨先生说,这几天,他正在读杰克。伦敦的荒野小说,也在重读鲁滨逊漂流记,重温人类与荒野和谐共存的那些时光,心中颇多感慨。
他说:“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变得与大自然誓不两立,一心否认自身就是大自然的子女和大自然的一个微小部分,一心想要做大自然的主人,把大自然踩在脚下,任意掠夺与蹂躏。”
逸晨说:“你看,那边城市的灯火,越来越密集和灿烂了。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留给我们的原始荒野,已经越来越罕有了。”
他说:“就比如,最初的美国是在形色各异的原始荒野上被开拓出来的,但如今这些原始荒野大多已经消失。”
我说:“是啊。从前,雄鹿的角曾经普遍地装饰过帝王们宏伟的城堡,现如今,在各大树林里,已经越来越难看到雄健美丽的鹿角了。”
我心里浮现出我们在博桑喂的那只小鹿,它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
逸晨说:“如今,再也没有谁能看到两汉时期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和无数千年树龄的参天大树了,也没有人能再看到成吉思汗时代长着高草的大草原。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那时草原的花海是如何抚过骑兵们的马镫了。那时候的草原植物曾多达上百种,许多都秀美艳丽,还有的着实美艳绝伦,现在我们都无缘得见了,更不用说我们的子孙。像冬湖镇这样在大自然怀抱中宁静度日的小镇,也正在快速地毁灭之中吧。”
我说:“人们并没有理解荒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城市随意地吞噬着荒野,工业化和现代化用很快的速度毁灭着一切。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创造一个荒野。我们只能毁灭和破坏,不能创造和建设。”
逸晨说:“荒野消失之时,也就是人性泯灭之日了。”
(三)
我和逸晨先生,都很认同这样的观点:仰望大雁南飞,要比看电视和手机屏幕更重要。欣赏一朵白头翁花的开落,至少与拥有言论自由,同样弥足珍贵。
然而,持有我们这种观点的,已经是少数派了。
我们和我们这样的观点,都将被历史发展的所谓滚滚车轮,毫不容情地碾压而过。
就像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人类所谓经济成就的殉葬品。
我怀着悲凉的心情,做着这样并不乐观的预期。
我怀念古代的世界和从前的纯真岁月。
我不喜欢如今世界的高楼大厦和狼奔豕突,还有现代文明与科技发展造成的星球表面的满目疮痍。
但我只能通过写作,表达内心的缅怀。
只能通过写作,再次回到那个消逝的年代里。
(四)
《太平》是深情的挽歌。
它远远不仅是我们爱情的挽歌,也是那个森林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