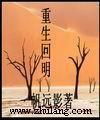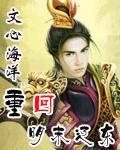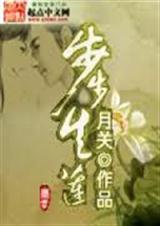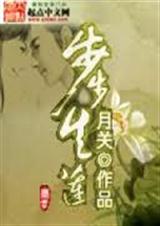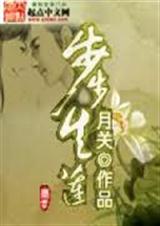回明-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见到在后世中经常见到的食物,原本不该那么吃惊的,但是朱允炆在不少小说中都看到说花生是十六世纪才传入中国的。而且他身为皇室中人,平日也未曾听说过有此物事,但听到朱元璋说是什么“长生果”,心里就有些计较,走上前去,捻了一颗放在嘴里,慢慢的咀嚼着。
好像是在回味,但是心里却有了说服朱元璋的说法。;
第六十七章 蛰伏(三)
又捻了一颗,朱允炆品尝着那久违的味道,被朱元璋传进御书房的花生,并不是如同后世油炸、醋泡、水煮制成,而好似把晒干的带壳花生用炭火慢慢烤熟,在烤制的过程中添加不同的香料,冷却后在除去外壳和红衣后,很细心的将每个花生仁都分开来,显得尤为白皙,怪不得开始没有认出来。
“皇祖父,这长生果味道真的不错,不知道山东进贡的多吗?孙儿想带回去一些,给母亲尝一下。”不知道深浅,朱允炆小心的试探。
虽然是这样说,朱元璋还是十分欣慰的看了他一眼,因为这才是他心目中那个乖巧孝顺的孙儿。但却是摇摇头,却把眼睛看往端花生上来的那个太监,心神领会,那太监磕了一个头,随即退出门外,急的往御膳房而去。
“这长生果,孙儿倒是在一本书上见过,却一直没有口福……。”看见老朱那么痛快,朱允炆也只好没话找话的说着,也不管说的对或者不对。
“此物又称为花生,或者是金果。最是滋养补益,长期食用有助于延年益寿,所以才叫长生果。且长生果富含油脂,一石可以出油六十斤左右……。”绞尽脑汁的在心里换算着自己那可怜的知识,朱允炆只是想引起朱元璋的重视,至于换算的对不对,他不是农业大学的学生,所以也只能靠猜测,反正在后世听说花生出油率在百分之五十,而古代的一石等于大约一百二十斤左右。
果然,话没有说完,朱元璋“咦”了一声,注意力已经集中到皇太孙的话题上了。别看身为皇帝,却对于民事比较关心,他知道就算是皇宫中品质最好的胡麻油,也不过是出油每石三十多斤的那个样子,而这长生果竟然是胡麻的一倍,怎么能不让他有些关注呢?
但仔细一想,又有些失望,道:“能让地方当做贡品的,产量必是极少稀罕之物,这长生果虽然是宝,但也无用。”
“不过孙儿却从书中得知,长生果是可以人工栽培的,而且产量极高,且不择土地,只要侍弄的适合,可谓是大明新增之一宝。”
“哦”朱元璋饶有兴趣的看着孙儿,说道:“允炆不是一向喜好诗书,什么时候对农事也有所涉猎了?”
“孙儿不敢,只是在苏州时,得到皇祖父遣往的张宗浚的人提醒,知道百姓辛苦,所以一直记于心中。不敢有忘……。”
“其实,孙儿方才看到长生果,想起了一些关于种植桑枣、棉花的心得,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说看!”虽然让朱允炆说,但是从语气上能听出,朱元璋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因为这个孙儿虽然不能说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吧,但从小生长在皇宫大内,没有体验过民间疾苦,单凭从书本上看来的那些东西,能有多少用。
“孙儿听说,洪武三年,因大同粮储要运至边关,由于路程遥远,被服役的民壮消耗竟然达到近三成。所以有人建议利用商人,於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如此以来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足……。”
朱元璋点了点头,捻须回忆着当初的情况,当时为了北征,他答应了这个要求,召集商人运输粮食而给予盐引,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为充足边储皆循序此例。不过按照道路远近的不同,或者视情况的轻重缓急,分别从五石至一石有所不同。但是不知道和今日工部所奏之事有何关系。
有些疑惑,但是并没有问,任由朱允炆说下去。
“孙儿刚才得见长生果,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朝廷不按照此旧例,将各地种植不同作物呢?然后再引导商人相互而走。因为孙儿在苏州得知,百姓种植,都有习惯成自然的现象,什么庄稼多产增收,什么庄稼省时省力,他们就种什么,多年的习惯,皇祖父想转变,恐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我大明既实行军屯、民屯。然而却是粮食满仓廪却罕见棉桑,要是强制棉桑却会造成粮食的减产,难过灾荒之年。且农作物还有夺地之嫌,诸如,北方之小麦和油菜籽,同一季节,百姓当然挑选产量高者种之。那样的话,百姓粮食充足,却是罕见油腥,还是不能达到各地自足,”
听到这儿,朱元璋不免真的有些失望,孙儿能提出这般疑问,已经是不错了,可还是想着那些商贾的利益,不过也不想就此打消孙儿的积极性,只能耐着性子听下去。
“当然,要是各地物产齐全,诸事皆宜,又反而无所依赖,不利于朝廷控制。所以孙儿想,为什么不让辽东、西北等地种植于江南不同的作物,然后由官府引导相互交换,这样以来,一则有利于朝廷税收,二来,各地相互牵制,便于我大明江山稳固。”
“为何?”朱元璋明显有些意动,但仍是冷静的听朱允炆分析。
“孙儿偶然得知,在西北边陲,天山的南疆、北疆。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日照时间较长。而木棉是一种好热喜光的作物,那里长时间的日照,充足的积温以及长无霜期给木棉的生长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种植木棉一定十分高产。”
“而辽东,各种矿产丰厚,且有棒打狍子瓢舀鱼,人参、貂皮、鹿茸角成为三宝,极为适合扬鞭天下,那里的部落以放牧为生……。”
“江南号称鱼米之乡,有话说“湖广熟、天下足”,正是我大明的粮仓……。”
……。
“孙儿认为,不如利用各地的优势,形成相互依赖之势。那样由朝廷居中调度,诸地各自为政,便于朝廷控制。”
“诸如新降之蒙古诸部、朵颜三卫、辽东女直等等,各部落不事农耕,长于放牧。朝廷以粮食换取他们的牛羊,他们就会不事生产。对朝廷的依赖性越强。如果将来他们一旦有了异心,朝廷只要切断相互贸易,在我们大肆的收购其牛羊后,恐怕无粮断炊之下。纵有造反之心,也要担心后继之粮……。”
朱允炆说的**裸,但是朱元璋却也听的有味,渐渐两眼放出光来。
~~~~~~~~~~~~~~~~~~~~~~~~~~~~~~~~~
ps:大家一定在鄙视虫子每章的字数,可是在没有推荐的情况下,虫子只想多在页面上露脸一会,哪怕十分钟,也会被多一个人看到,虫子只想多一个人支持,请大家原谅。;
第六十八章 蛰伏(四)
作为大明储君的皇太孙,手里却亲自抱了个杏黄色的袋子回到东宫,让一路上遇见的宦官、宫女个个暗暗称奇,几个想要讨好皇太孙的内侍过来帮忙,却被踢在了一边跪着。反倒是吓的索索而抖。
袋子内装的正是山东布政司进贡而来的花生,朱允炆没有想到,这个在他后世随处可见的日常小吃,在明朝倒是成了宝贝,整个南京紫禁城也只有这么一小袋而已。
回到东宫,朱允炆仍在鄙视那个叫秦天极的山东布政使,就算是十分难得,也不用把花生夸的好似人参一样吧,说什么长生果采摘于乳山之巅,濒临碧海,吸收了蓬莱仙气……,听前来汇报的太监将山东进贡时说的话又复述了一遍,面无表情的他其实早就笑的肠子打结了。
但绝不会笨的去揭破这些谎话,那个秦天极越是将花生说的珍贵,那么以后万一培养成功了,自己才能显得功劳够大,万一种不成,呵呵,那也有个推辞是不,因为种植这门学问在朱允炆心里,仅仅限于挖坑将种子放进去浇水那么简单。
朱元璋已经将钟山附近的一处皇庄指定给他,让在那里试验,皇庄之内不缺乏有经验的老农,自己只要是将事情吩咐下去就可以了。
今天最大的收获当然不是花生了,有些得意的朱允炆将那袋子放在身旁的案几上,然后令宦官前去召铁铉前来。
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借机将铁铉抛了出去,山东布政使由于进献贡品,加上任期已满,被朱元璋调回京师任礼部右侍郎。那个位置空了出来,朱允炆趁机推荐铁铉,说是要派得力之人去山东勘察地势。以便于寻找适合花生种植的地点。
显然,老朱的心情被其孙儿调理的不错,连犹豫也没有犹豫就准了,不过朱元璋也不是无的放矢。居然对铁铉近一年在东宫的表现显得比较清楚,也很满意朱允炆的推荐。
老朱的心情之所以不错,还是源于朱允炆那种在当时比较新奇的言论。利用贸易关系,达到控制和被控制的功效,这个在后世中已经成为潜规则的方法,在此时的大明显得还是那么的新颖。
从这点,老朱甚至可以分析出了一些经济战的雏形,当然,是针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只要利用其对粮食的需求,达到瓦解其部落联盟的目的,只要不操之过急,就可以将其各个击破,各部居无定所,只要利用其对粮食的依赖,再利用商人如同蝗虫般的收购其牛羊,使其根本没有库存,那么很难再联合起来和大明做对,如同温火闷饭,不觉饭熟。
以北方苦寒之地所产出牛羊,远远不能满足大明几千万百姓所需,而仅仅凭借江南余粮,就可轻易满足那些部落所消耗。如果按照皇太孙所提,再以大明之奢侈品引诱,那些游牧部落拼命的养殖,也不足于他们消耗,长久下去,这些部落只能渐渐南移,融入到大明的疆土中去,北方将再无战事……。
对于朱允炆的说法,虽然涉及行商兴盛,但是还是要有官府主导,朝廷主持,那样的话,朱元璋对于商贾纵然有些厌恶,但要是由自己来做庄家,还有什么抵制的呢。
此策可行,虽然有很多地方仍未听懂,但是凭借老朱拿敏锐的政治嗅觉,仍是让皇太孙写一份详细的策论来仔细参详。
这一切都归功于朱允炆参与修订《大明律》后的了解。由此可以推测的很多内容。
大明定的各项制度,大都是借鉴了唐制,宋制,也借鉴了元朝的种种不利,其实都源于秦,秦迁九鼎,分郡县,基本上就订下了这样的框架。历经汉唐,不过是修修补补,儒家根据帝王喜好的增增减减。从来没有大的变化。
朱元璋从来未曾满意过,要不,也不会将《大明律》几次修改近三十年仍未定论,不管是基于唐制、宋制……。都有前车可鉴,作为开国君主,谁不想创下万世基业,但所借鉴的全部都是亡国的制度,这一点让皇帝心中最有芥蒂。
怎么才能找到稳固万世基业的柱石,这应该是徘徊在朱元璋脑海中几十年的问题,为此,他大举分封藩王,是沿用周制,因为不管怎么说,周朝也延续了八百年,又吸取了唐代藩镇的教训,藩王只封给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话,可以使国祚更加稳固。
在朝廷的统治中,仍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万世基业将依靠在那里?朱元璋不知道,但是突然听到这样新奇的言论,虽然和儒家的治国之道有些悖逆,但是他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