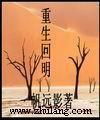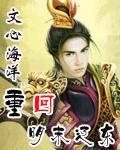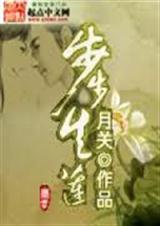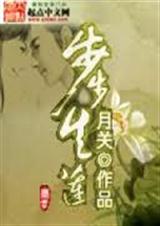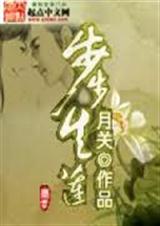回明-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元璋面无表情的听完了孙儿所讲,心里不由暗自叹息孙儿的妇人之仁,哪有谋反案还要公开审理的呢?那不是自曝家丑吗?反贼还可以请人辩护,还要锦衣卫找出具体证据让反贼辩驳。谋反乃是逆天大罪,落到谁头上都是抄家灭族。谁会承认?陪审团也不就是三堂会审?但是陪审团认为没有罪,大理寺不得强行通过有罪的决议,那还审什么?朕的官员每天都有国家大事要忙碌,天天陪审?那他们倒是愿意,可是朕的俸禄不是白了吗?
摇着头,正想把其中利害慢慢的说出来,顺便驳回孙儿的要求。但是转眼看到允炆那充满期望的眼神。一向强硬的心忽然又软了下来。允炆长的可真像标儿啊,都是挺直的鼻梁,如剑的双眉,似水的眼睛,还有厚厚的嘴唇、白皙的皮肤,朱元璋仿佛又看见小时的朱标。
标儿这么大的时候,朕还在南征北伐,一年难得见几回,每当遇见,标儿就会为自己捶打酸痛的腰身,会默默为自己整理好地图和文书。会无声的站在自己的身后,然后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
朱元璋的眼神有些迷离起来,好像又看见是朱标站在自己的面前,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却变成:“一个臣子,要饶就饶了,那还用那么麻烦,允炆,既然你有意要维护叶昇,那朕就给你这个人情,你去传旨吧,也让他们叶家知道是谁救了他们,以后必会对你忠心不二。”
要是换成别人,就算是以前的太子在侧,要是和朱允炆一般的说法,那必定是一顿臭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朱元璋对于这个孙儿有着特别的好感,也许是“隔代亲”的缘故,也许是太子刚刚病逝,朱元璋念及骨肉亲情。
而叶昇,功劳在大明开国元勋中可能连末席也坐不上。因为是当初张士诚部降将的缘故,所以在官场上也没有什么人脉。不属于任何派系,也不属于任何门阀。所以朱元璋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播下种子,想收获个西瓜,但是却得到一粒葡萄,令他有些感到安慰的是,集权也有集权的好处,在朱允炆亲自传旨下,叶昇一案没有经过再次审理就落下帷幕。叶昇保爵去职,暂时留于京师。未得皇上御旨,不得擅离。
一向手下从不留情的皇上,竟然为了太孙而赦免了叶昇,这给太子早逝。许多正在观望的大臣们一个信号,也为许多清流名臣坚持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坚定了信心,东宫门前,一下子热闹起来。
经过多重推荐,两个士子直接找上门来,景清,陕西真宁人,戴德彝,奉化人。两个人皆是洪武二十三年落第的士子。在京师国子监中求学等待下次的秋闱。
二人年轻气盛,都认为叶昇获救之事,乃是朝廷仁政的预兆,听到东宫招纳伴读之人,便慕名而来,请求侍奉于东宫书案。
作为已经知道二人是谁的朱允炆已经将其二人要到身边,作为侍读之人,将他们打上太孙殿下的烙痕,对于他们的欣赏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
因为,后世中建文帝失踪后,这两个都是殉节之臣,简直可以说是建文帝的死士,现在朱允炆初回大明,怎么不求贤若渴呢。;
第五章 正式册封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借助叶昇案朱允炆所积累的人望。朱元璋正式下诏,皇太孙朱允炆为大明储君,以黄子澄、齐泰、为东宫侍读。景清和戴德彝为伴读。重建东宫制,诏命皇太孙断刑狱之事,锦衣卫南镇抚司听命于皇太孙。
锦衣卫主要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管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司法机构。
朱元璋让皇太孙主理锦衣卫南镇抚司的用意十分暧昧,但又似乎十分明显,作为皇家爪牙的锦衣卫始终要掌握大明皇帝的手中,那么让锦衣卫下一步听从皇太孙的旨意就势在必得,而北镇抚司掌握皇帝钦定的案件,现在的皇帝还有利用的价值,所以暂时不能交与皇太孙,而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军纪。如果是别人主理也没有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清水差事。但若是皇太孙亲自主理,那么意义就不一般了。等于说锦衣卫内部的事务他皆可插手,看着谁不顺眼就可以以军纪、法纪来约束对方,是让人都有些心惊胆颤的。
其中最为不安的不是别人,就是身为锦衣卫指挥使的蒋瓛。本来在锦衣卫中一手遮天的他,突然被放个凤子龙孙在身边,还真的不好受,特别这个凤子龙孙还是以后的大明皇帝。怎么能不让他如坐针毡呢?
皇上天马行空的安排实在让他难以揣测,但是蒋瓛却被皇太孙雷厉风行的作风吓了一跳。为了方便北镇抚司专心诏狱之事,很多事务现在名誉上都归南镇抚司监管。除了缇骑和探听局之外,别的基本都是南镇抚司在主理着,乍一看皇太孙只是主理南镇抚司,但是锦衣卫却是大半在朱允炆的掌握之中。
也不知道皇太孙是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还是不知道官场规则。接到圣旨,皇太孙却是连他也不通知,就召集南镇抚司所有官员开了一个会,其中还叫上了主管南镇抚司的同知和佥事,就偏偏没有他这个锦衣卫的第一号人物,等他赶去请罪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朱允炆封官许愿完毕,众人皆大欢喜。当然,不熟悉情况的他只是口头上的承诺,却是令众人热血沸腾,怎么说皇太孙也是未来的皇帝,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有太祖皇帝在位的一天,恐怕他们很难过蒋瓛等人,但是如果刻意讨好未来的皇帝,未尝也不是一种投资。
何况皇太孙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众人皆保留了原来的官职,只是军匠局的头目多了一个副手,叫戴德彝。
看到往日属下扫向自己的眼神,已经和以前的敬畏惧怕不同,蒋瓛心里也十分的郁闷。可是对方是皇太孙,他又能怎么办,心里暗恨着这些见风使舵的家伙,衡量着以后该怎么整治他们。嘴里却是接二连三的向朱允炆请罪。
知道蒋瓛的人品和下场,但是现在初来乍到还不能盛气凌人,于是朱允炆忙谦和的说:“这些奴婢,忘了提醒我凡事要支会蒋指挥使的。还望指挥使恕罪一二。”
而蒋瓛只能像是个受气的小媳妇,一味的说道:“不敢,一切单凭皇太孙殿下处置。”一边心里暗自不爽。
朱允炆却是没有蒋瓛想的那么复杂的心思,接到诏书后,之所以迫不及待的去接管南镇抚司,那是因为他想了解一下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力量。
可能是故意的逢迎,也可能是出于对蒋瓛的不满,一些有心的下属,在朱允炆不明白,而他们又没有接到通知指挥使的命令下,刻意的忽略了通知蒋瓛,趁机也摆了这个日渐骄横的指挥使一道。
李瑞栋就是其中最为最高兴的一个,看着昔日威风凛凛的指挥使怏怏而去,他对于自己今后的前程又增添了几分信心。看到太孙殿下对于锦衣卫的兴趣很大,于是不耐其烦的介绍着南镇抚司的详细情况。
锦衣卫全名为“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前身为太祖所创头戴凤翅盔的锦衣卫大汉将军设之“御用拱卫司”。
洪武元年时改制之“仪鸾司”,洪武二年时改制成“大内亲军都督府”。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二十五年来,锦衣卫经过多次磨合,建制终于稳定下来,其中主要职能部门分为南、北镇抚司两个部门。
北镇抚司的主要职责就是主管各地藩王及官员秘密监视、肃反肃贪,独立侦讯、逮捕、判决、诏狱以及反间谍事项。
而经过多年整合,其余杂事基本上被南镇抚司承揽下来,最惹人注意的有三个部门,就是军纪司、侍卫司和军匠局。掌管着皇宫大内的禁卫之责,锦衣卫内部的刑罚和军械开等等。之所以没有北镇抚司惹人注意,那就是他的职责所在只是在京城范围之内,基本从不公开露面。所以常人眼中的锦衣卫,只是北镇抚司那令人谈虎色变的缇骑和无孔不入的探听局。
把锦衣卫内部的分工了解清楚之后,允炆不由苦笑起来,朱元璋到底想做什么呢?让自己主理南镇抚司,不过是当一个锦衣卫的后勤部长而已。先,侍卫司掌管大内守护任务,肯定是不会听从自己的指挥。军纪司,说白了也就是一个类似军事法庭的部门,既然锦衣卫是皇帝亲卫,那么什么刑罚只能是皇帝说了算,军纪司只不过是一个抡大棒的执行者而已。
军匠局是他抱有希望最大的地方,想和以后的朱棣对抗,只能靠不断展的科技才能与百战铁骑有一拼之力。但是到了军匠局之后,看着寥寥几人的荒凉模样,军匠局千户李成文那满脸的横肉。才感觉到自己以后面对的是多么大的一个烂摊子。
幸亏自己先安排了一个戴德彝了解情况,否则还真的被这个李成文拿出的几种火器蒙骗过去,听戴德彝说,这几种火器还是十余年前留下的,专门为了应付上官视察,以现在的工艺根本生产不出来。
明迅雷铳的焦玉呢?前世身为这个人,不是说在明朝火器已经开始普及了吗?
看着自己的身边,除了景清和戴德彝,几乎没有可用之人。黄子澄和齐泰因为有官职在身,虽然身为东宫伴读,但只是偶尔来授课教授四书五经。暂时根本不可能为自己所用。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最缺的是什么?
人才!
最最缺的是什么?
还是人才……。;
第六章 燕王归来
朱允炆想起在济南上大学时,和同学参观过的“七忠祠”。里面供奉着铁铉、陈迪、胡子昭、丁志方、高巍、郑华、王省七人,他清楚的记得,这七人是建文帝的死忠分子,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绝对不可能被叛自己的人。
必须要找到他们,当然,可能这些人此时还是藉藉无名,就是自己也只是记得一个“城神”铁铉。其他几人也不是太了解,但是谁又能比他多出六百余年的先知呢?而且这样招揽人才,不容易被猜忌。他清楚的记得,朱元璋到死的那天还没有交出自己的权柄,可以看出这个太祖皇帝对权力的控制**。
燕王朱棣最后没有被朱元璋青睐而传位与他,是不是因为两个人的控制欲都太强了呢?朱允炆这样想。
于是一刻也没有迟疑,在李瑞栋的帮助下,景清得到朱允炆的授意,暗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官员普查。没有几天的功夫,好消息就传了过来,铁铉和丁志方目前正在国子监,而高巍却是已经被人告说同情空印案犯而被贬往辽东,胡子昭随方孝孺在汉中游学。
陈迪、郑华和王省三人则无从查讫。只得吩咐李瑞栋利用在锦衣卫探听局得关系慢慢寻找。可惜朱允炆也只是知道姓名,再也提供不出详细的资料了。
不过他要做的事情也仅限于此,再做出其他举动,估计朱元璋就要怀疑自己的用心了,对于这个开国帝皇,在晚年的所作所为,朱允炆此刻只能往坏处想,而不能往好处想。
看了太多的穿越小说,使朱允炆对于帝王之家不抱有任何亲情妄想。一切要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