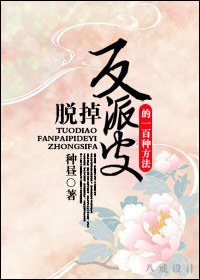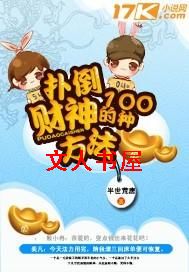换一种方式去爱-清穿-第10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百天。还好,没伤到骨头,只是筋扭了。只是四福晋这下子可一定要好好养着,不然以后很容易经常扭伤的。一会儿让人随我回太医院取几贴膏药,回去用热水将红肿部位暖敷一下,再贴上!”
胤一直站在我身边,让我紧拽他的手,以便疼痛时分散些注意力。此时听得老太医的话,又是担心又是心疼,又有些生气,狠捏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找人和老太医去拿药。回屋后胤忍有所抱怨:“你看你,现在好了!下午那一跤摔得不过瘾,又来一次,伤到了筋骨,真是自己招罪受!到底怎么给弄得?”
我不得不放低姿态,软语相求,一边施展美人计,在眉来眼去,唇舌相依中,让胤忘记了对弄伤我脚的宁真的怒气。
……话说,我周末还上网,老公的脸也很黑……
下篇 沫沫相濡锁重浪 第八十一章
下篇 沫沫相濡锁重浪 第八十一章 无论怎样,日子还是要过的,尤其怎能让旁的人和事来打搅我和胤好不容易得来的幸福生活。在这一点上,我也可以算得是没心没肺吧!只是每回不得已见到胤和宁真,心里难免会冒些些愧疚和无奈出来。
养脚伤实在是一件很无聊的事,走路基本只能用跳的。为了避免成为类僵尸动物,我已经尽量少走动。可整日呆在屋子里,不免觉得无聊得紧。空的时候,还能抓丫环陪着玩会儿牌,可丫环们终究是要做事的。好在还有一份兼职,没事对着天空发呆,想想首饰的设计图案,好从墨那边多赚点钱过来。只是难免老被胤笑话,说我和墨俩人是一对钱迷,一个孔兄,一个方妹,合成铜钱孔方兄。显然,墨的功力比我深厚,在我只能讪笑的时候,墨毫不犹豫地告诉胤,铜的他基本看不上,不是金的也得是银的,才衬得起他的身家。
对于我的脚,胤说我是自招罪受,可却又心疼的紧。墨也来看过我了,不过我一点都不指望这个千年老妖会有同情心,他甚至还无良地嘲笑我,说一个功夫在江湖中也可以算是二流的人,居然让一块小石头和被人摇两下给弄成这副样子,让我羞愧地差不多想找个地洞钻。墨甚至将这个笑话传给了远在江南的琰,琰的答复是:不要嘲笑我师妹了,不是早八百年就和你说过,她就是有百年功力,也就只是摆着好看的。我彻底对这两个损友无语。
“来,和你们福晋说说。最近咱们府里有啥趣事?”某个秋风习习的午后,经过一个多月的修养,已经能够掂着脚走路的我。坐在凉亭里,对着刚刚被我逮到。。。正在传播八卦地几个丫头笑道。
丫环们都只是憋着笑,你推我,我推你不语。还是服侍我的晚儿知道我的脾性,冲着我抿着嘴儿一笑,道:“刚刚负责打扫地小茜说。昨儿个小栋子陪年公子采办东西的时候,那年公子……咯咯,居然对荷包喜欢地紧。”看我不明所以,晚儿补充道:“据说年公子喜欢的是那种精致花俏的荷包……”
嘎嘎,这就是了,看不出来哦!荷包就是用来装零星琐碎东西的小口袋,其实是男女均可用。胤用的,就都是我亲手绣地。但样式上面,总还有些男女用的区分。就好比后世的随身包。男子多喜欢用皮革来做荷包,绣的也多为些诗句,简单的画。耐用不花哨。当然富贵人家的公子也是喜欢用些锦缎来缝制,绣上精美的图案。缀上流苏。但总的来说,还是追求实用功能多些。
女子用的。就不一样了,首先荷包地形状就各式各样,葫芦形,鸡心形等等不一而足,上面绣的东西也复杂得多,要是送给情郎的,什么并蒂莲啦,比翼双燕啦,交颈鸳鸯啦。而且女子多喜欢在里面放上香料,做成香荷包,也就是俗称地香囊,而非荷包的原来用处,用来装东西。而男子一般收到这类荷包,会贴身带着,却不会如寻常荷包一般,坠挂在腰间。
看来这年羹尧当真是公子习性重得很,放在世纪,估计也是个涂脂抹粉地料,此类人一般多有水仙花症即自恋或玻璃倾向。我心里暗自诋毁着年羹尧。
话说,前几日,胤告诉我说,那年羹尧已经通过乡试,上京来,准备参加来年地会试。胤邀请了他在京城的住所备好之前,暂居在我们府内地一个偏院。还派出小栋子协助年羹尧的仆人管家筹备京城住宅的事宜,不想,传了这么个八卦出来。
不过想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年羹尧长得俊俏不说,还挺英武,身上有些贵气,在我看来是纨绔弟子的作风,而且有才干,还是个举人,又得自家贝勒爷赏识,在那些丫环眼中,是个白马王子式的人物。现在有点好奇心也是在所难免,不知道这些丫环回去后,会不会一个个都开始绣荷包,往年羹尧住的竹院送。
嗯,其实她们要真有心,我不介意送年羹尧一两个美女啦。如果他承了我的情,看以后还好意思把他现在还没影的妹妹送过来不?要不咱放下地位,认他做哥哥?清朝有姐妹不可同入宫的规定,虽然被康熙破坏得早没影了,别说姐妹,康熙连姑侄也一并收过。但好歹也是一条规矩,以后我站出来拒绝老年糕的好意,也名正言顺不是?
我这厢和一帮丫环唧唧喳喳,发挥女人天性八卦着。那厢胤却是合着年羹尧,和同为来年会试贡生的张廷玉把酒言欢。虽然这个未来的万能秘书同住京城,而且是胤的老师之一张英的儿子,可是总是错过见面的机会,以致到现在我还没见过他。
十月的时候,胤和十三都随着康熙又一次巡视了永定河。朝中一切太平,只是又有一个李姓的大学士殒落,康熙命人给予了厚葬。
其实若是政治敏感些的人,能嗅出其中的不同寻常。这两年,曾经辅佐康熙巩固皇位的老臣老将先后去世了不少。他们生前多居高位,那么替换他们的人,是些什么人,属于什么势力,比较倾向哪位皇子都成了很奥秘的问题,颇有几分玄机在里头,值得细细琢磨!
朝中的事物并没有多多少,但胤变得有些忙碌,此间陆续赴京的贡生中,定有不少值得拉拢。我唯一能给予的,是对胤的支持。墨那边生意上的,金钱往来的东西我接手过来。琰那边有些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也基本上我在处理。
据说胤他们最近出宫也比较频繁,只是相对于胤只和学子结交,偶尔谈诗论画外,他们的活动有些过于明显,虽然和一些朝中大官如马齐之类的来往,算不上频繁,但一来二去,一两个还可以说私交,走得多了,难免要让人有想法。只是我不明白,以胤的心计和能耐,不该如此急进的。不过,只要于胤无害,我们暂时还是只能做壁上观。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底,通过殿试后,取了三百多人为进士,将近往年录取的两倍,可见随着老一辈的去世,朝廷有多渴望补充新鲜血液。就如意料中一般,年羹尧,张廷玉均中选,可惜状元被一个叫汪绎的家伙夺走。不过巧的是,年,张两人似乎颇顺康熙的眼,同时受封为翰林院的检讨,虽然只是从七品的京职文官,但翰林院本就有“玉堂清望之地”的称号,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绝大多数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可见康熙对这两个年轻人的还是颇为看重的。
……过渡章吗?官官有些心虚地说。
下篇 沫沫相濡锁重浪 第八十二章 随父再巡永定河(一)
下篇 沫沫相濡锁重浪 第八十二章 随父再巡永定河(一) 总的来说,我这个皇四子贝勒福晋的日子过的满惬意的,至少在康熙三十九年夏之前是这样的。秀儿如预期一般,嫁给了胤俄做了庶福晋。看来老十还是挺重情义的,过了这么些年,还惦记着秀儿。绿烟管着府里的所有丫头,晚儿就成了我最贴心的人。
因为胤目前还没有侧室,妾室,自然少了后宫式的争斗。康熙,德妃虽然明示暗示,却也只是无用功。暗示嘛,胤和我一样有默契地装傻,至于明说,一般都有胤在前头推托。
有一次,康熙见到我时,用一种很是奇怪的眼光打量我,然后戏谑般地说了句:“嗯,怪不得!”,虽然以前康熙心情好的时候,和我常笑闹,象个亲近的长辈,但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还是闹了我个满头雾水。后来在我的酷刑下,胤才支支吾吾地向我解释,不由恍然大悟,暗骂康熙为老不尊,整一个老不羞!
原来有一次,胤随康熙一起办事,康熙就唠叨着说胤大婚到现在已经四年,该娶几房侧室也好兴旺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丁。正在专心办事的胤一时不察,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儿臣精力有限,忙不过来!”
其实胤的意思应该是朝中事忙,在家陪我和弘晖盼兮的时间本就很少,哪有心思再娶什么小妾。结果康熙这个风流皇帝听了这话,结合京城里有一段时间流传出四贝勒和福晋恩爱异常,除却公差在外,从未有一日离宿主卧房的传言,很是暧昧地打趣了胤一番。
我很想让胤也去康熙面前谦虚两句。比如:皇阿玛老当益壮,后宫几十位妃子,都能做到雨露均沾。。最快。并保证大多数都有所出,为我大清国添砖加瓦。为儿子多添多兄弟姐妹,儿子自叹不如之类的。不过不说胤肯不肯,康熙要听到这话,估计直接就将胤和我圈禁,而我们也光荣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康熙朝圈禁的第一对夫妇。说到圈禁。难免想到十三后来地遭遇。不过现下,十三似乎依旧有些郁郁。十三对老三胤祉有些微词我是知晓的。敏妃过世后,胤祉先后两次对敏妃出言不敬,又不及百日剃发,虽然他受到康熙的惩罚颇重,但对十三来说,心里总憋着这份屈,尤其敏妃是十三最亲近地人之一,同时又已经过世了。都说死者为大。若有什么怨隙,也该随着烟消云散了,更何况。敏妃生前从不与人结怨,与胤祉更是毫无交集。就更没有仇怨一说。胤祉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忿。难怪康熙一怒之下,连他地郡王爵位也降了。
不过相对于对老三的微词。十三对老大胤就上升到了仇恨的地步,从几次在我们府中私下的言谈之间,我觉着他对老大几乎可以说怀恨在心了。我仔细琢磨,说不定是敏妃临终前对十三说了什么。要不然,以当时的情形看来,若敏妃真死于胤和太子在后宫势力地争斗中,十三该同时恨老大和太子,而不是只针对其中的胤。
我曾试探地问过胤,是不是胤和敏妃的死有什么关系。胤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几乎以警告的语气对我说:“别胡言乱语,小心引火烧身!”待看到我有些委屈憋气的脸色,胤意识到自己语气的不善,长叹一声。
无赖地省去道歉,胤将我一把捞进他的怀里,顺便还揩了点油,才慢慢解释道:“我当时找了个信得过的太医将敏妃临终用过的茶水,糕点,餐具都验过,但均无异样。而我曾因十三弟地要求,让墨略去了敏妃的名字,将她的病症讲述给静缘大师听。大师对敏妃地死也感奇怪,断不出什么病。可大师是出家人,没有切实的根据,有些话不能乱说,而且说是没有面诊,也无法说出所以,只说有可能是几症并发地缘故。况且敏妃临终,我也在场,她并没有说什么比较明白地话。只是十三弟一向和他额娘亲厚,或许知道些端倪,但也没有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或者可以值得让皇阿玛允许追查地线索。所以,我才要你小心说话。宫里的敏妃能死得不知不觉,我们府里的防卫又哪及得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