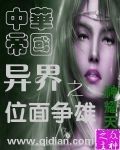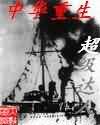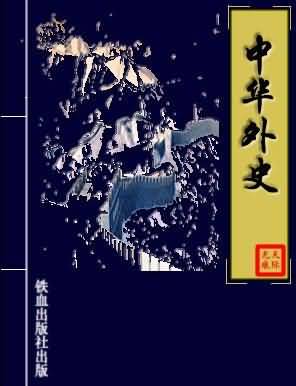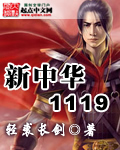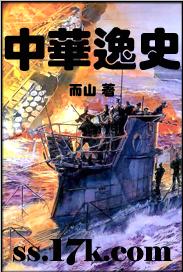中华异史-第2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王坤脸色有些发白,他辩解道:“你,你怎么能这样说咱家?咱家可是对万岁忠心耿耿!”
丁魁楚见两人吹胡子瞪眼,生怕他们吵将起来,便忙说道:“二位不可争吵!莫忘了,这是在朝堂之上,是在天子面前,切莫失了臣子规矩!”他向堵胤锡说道:“堵将军不必太过担心,那鞑子如今也是有心无力,况且朝廷派去议和的大臣已经传回话来,说他们已经与那鞑子的摄政王多尔衮见面了,那多尔衮已然答应议和,大不了多给他们点儿好处,相信他们是不会轻易南下的了。至于那个张献忠嘛,流寇一个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将军出马,一定轻易将他消灭!”
何腾蛟见无法说服皇帝,只好暂时改变策略,他向皇帝奏道:“臣以为,那楚国公林清华一向对大明有功无过,先是数次击败鞑子兵马,后又率兵南下勤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良将,臣以为朝廷若想夺其兵权,那么是否可以留其一命,任其为文官,也可继续为朝廷效力?”
皇帝望了何腾蛟一眼,说道:“莫非何爱卿还记着林清华派人相救之恩?嘿嘿,爱卿可真是个有恩不忘的人啊!”
王坤见皇帝似乎还想说出别的话来,他赶紧拉了拉皇帝的龙袍,向皇帝使了个眼色,同时又摇了摇头。
皇帝虽有些恼王坤多事,不过他也知道不可太过逼迫,遂语气一变,说道:“既然何爱卿替他求情,那么朕也不能驳了爱卿的面子啊!这样吧,等他将手中的兵权交出,那么朕就免他一死,而且还任其为……任其为……”皇帝对于朝廷的官职仍然很是陌生,一时倒也想不出什么好官职,只好将目光投向丁魁楚。
丁魁楚知趣的说道:“皇上,臣以为楚国公确实有功与大明,所以朝廷也不能亏待了他,既然他对于火器十分精通,不如就将其任为工部尚书,并加太保衔,位列‘三公’,以示朝廷不忘其功。”
皇帝不知道这个官儿有多大,他转头望向身边的王坤,见王坤略微点头,遂转过头去,说道:“那就这样吧,就按照爱卿所言,希望林清华能够体会得朕的一片苦心。”他望着何腾蛟,问道:“何爱卿无异议吧?”
何腾蛟明知那所谓的‘三公’如今已经是完全的虚衔,根本就不是什么实权官职,不过,他毕竟认为这已经算不错了,至少能让林清华保住性命。说实在的,他并不看好林清华能够逃出这个陷阱,而且他也认为朝廷的实力已经渐渐恢复,以林清华一个人的实力,恐怕真的难以与之对抗,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实权,保住性命。因而何腾蛟立刻表白道:“臣无异议。”
看到何腾蛟已经不再坚持,皇帝很高兴,他说道:“既然如此,那么今晚之议就到此为止吧。何爱卿与堵爱卿二位立刻返回禁军大营,严厉督促兵丁严守城门,不许任何人离开南京城!”
何腾蛟与堵胤锡当即转身退出大殿,而那丁魁楚与王坤却仍然留在了殿内。
待何腾蛟与堵胤锡二人离开,小太监们又将殿门紧紧关上。
皇帝舒了口气,他盯着站在面前的丁魁楚,问道:“怎么样?朕让你问的话你都问了吗?”
丁魁楚道:“回皇上,皇上命臣向黔国公问的话臣已经问了,不过黔国公却不肯将全部计划说出,他只是说自有妙计,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免得走漏风声。”
“什么?难道朕也会走漏风声吗?”皇帝有些恼怒了。
“皇上万勿生气,黔国公就是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这样想的,他是怕为臣这样的人走漏了风声。”丁魁楚赶紧替沐天波辩解道。
“怎么?丁大人居然替沐天波辩解?”王坤皮笑肉不笑的说道,“莫非你是假戏真做了?”
“臣,臣不敢!”听到王坤这样说,丁魁楚“扑通”一声跪倒了,“臣对皇上的忠心苍天可鉴!臣绝对与沐天波没有任何的私下交往,臣所做的一切均是皇上嘱咐,臣愿一死以表清白!”
听着丁魁楚的脑袋碰击地面的声音,皇帝与王坤对望一眼,随后他望着丁魁楚,和蔼的说道:“爱卿快快起来,朕又没有怪你!”待丁魁楚从地上站起来后,皇帝接着说道:“爱卿的话字字发自真心,这一点朕是知道的,朕绝对信任爱卿。爱卿不必理会别人的话,爱卿继续说下去吧。”
听到皇帝这样说,丁魁楚顿时满脸的感激之色,他说道:“皇上对臣的信任让臣无以为报,唯有肝脑涂地方能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他顿了顿,接着说道:“黔国公说了,他对付林清华的计策还是需要那童清风来办,只要童清风去,就一定能将那林清华诓进城来,一旦他进了城,那么就不怕他不就范!不过,黔国公还有一下策,万一那林清华不上钩的话,那么就没别的办法了,就只有硬拼了,好在镇虏军与洋夷交战甚久,损失较大,而且火药等军需之物极缺,所以只要黔国公的兵马与禁军兵马齐出,就能一举将其荡平,以解朝廷心腹之患!故而朝廷一定要将火药留下,不可送往镇虏军中。”
皇帝觉得此计不错,他点头道:“不错,居然有上下两策,看来这沐天波果然老奸巨滑。”他转头看了看王坤,接着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丁魁楚,忽然语气一变,说道:“丁爱卿,你可要把握好啊,你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你是朕的人,你所做的都是朕的授意,你可千万不能真的变成沐天波一党了!”
听到皇帝语气严厉,丁魁楚一惊,浑身直冒冷汗,他又“扑通”一声跪下,连连叩首,说道:“臣只为皇上效忠,臣绝没有二心!臣绝不做那沐天波的党羽!”
这回皇帝并没有急着让那丁魁楚站起,他转过头去,稍微提高了一点声音,问王坤:“王坤,朕问你,你刚才说何腾蛟将军在黄得功、李成栋的军中看见了沐天波部将王扬祖,这事是真的吗?”
王坤立刻大声回道:“千真万确,老奴愿以性命担保,他确实看见了王扬祖,而且看起来那王扬祖似乎是奉令前往收编黄得功与李成栋的部下,不过好在朝廷已先一步下手,才没让他们得逞。”说完这些话,王坤意味深长的看了眼跪着的丁魁楚,言有所指的说道:“可惜呀,恐怕有人真被那沐天波的花言巧语给欺骗了,以为那沐天波真的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
丁魁楚当然明白王坤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一言不发的连连磕头,将那汉白玉的地面磕得“嘭嘭”直响,身上的官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皇帝见目的已经达到,语气又变得和蔼,他说道:“丁爱卿,你起来吧。朕知道你是忠心耿耿的,要不然,你也不会听朕的话,去和那沐天波称兄道弟、虚与委蛇了。”
丁魁楚战战兢兢的站了起来,他结结巴巴的说道:“臣……臣万不敢欺骗皇上,以前臣对沐天波所说的话都是皇上授意的,臣也一直是与那沐天波假意敷衍,绝没有与他狼狈为奸的意思,皇上赐臣的那块免死铁券臣一直带着,要是皇上想收回,那臣马上就交回。”
皇帝笑了笑,说道:“那铁券是稳住左梦庚与沐天波的东西,虽然那左梦庚先死几天,但那沐天波却还仗着太祖赐下的铁券嚣张,让朕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这块铁券你继续拿着好了,给朕继续稳住那沐天波,要是以后真的顺利的办成了事,那么朕就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用明诏赐你一块免死铁券!”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原创!
第四章 夺鼎 第六节 水寨
太湖,古称“震泽”,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其水域面积仅次于鄱阳湖和洞庭湖,号称“三万六千顷;周回八百里”,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湖泊。
位于江南水乡的太湖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首先大规模开发这里的就是春秋时期的吴国与越国,到了三国时期,东吴进一步开发了太湖流域,使得这里的经济逐渐赶上了中原地区,之后又经过了数百年的经营,到了唐朝时,这里就成为了朝廷重要的粮响来源地,以至于“安史之乱”时,朝廷不得不从这里调运大量粮响,以支援朝廷平叛的军事行动。到了南宋时期,由于中原战乱连年,残破不堪,而且南宋朝廷也定都于南方,所以,此时太湖流域的经济开始全面超越北方,以太湖为中心,形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这里成为整个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到了元朝,在全国商品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太湖流域的经济进一步大发展,这里是朝廷禄米的重要来源地,正是为了将这里的大米运往北方,元朝才将隋朝的运河加以修整,并开凿了新的运河,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才贯通大都黎族较先进的棉纺织工艺传到这里,使得这里的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起来,著名的“乌泥泾被”也就闻名全国,使得整个松江地区成为了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太湖流域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体现,地区经济也就更上一层楼,为随后的朱元璋由南而北建立明朝打下良好的经济根基。
不过,到了明朝末年,在全国普遍灾荒的背景下,太湖流域也遭受了多次灾害,虽然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毕竟让百姓们的生活更加困苦了一些,一些百姓走投无路下,便纷纷进入了那烟波浩淼的太湖之中,当起了打家劫舍的水寇,虽然官府多次进湖围剿,但毕竟活不下去的人太多,而且湖上水道众多,湖中岛屿也不少,再加上官军腐败无能,因而水寇剿不胜剿,太湖也变得危险起来。
在太湖众多的水寇之中,最强大的一支是由一名落第的秀才率领的,那秀才叫什么名字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人们只知道他的外号——五尺孔夫子。
这个外号是有来历的,据说他姓孔,身高还不到五尺,甚是矮小。本来考官看见他姓孔,而且文章也做的不错,原是打算将他录取的,但当知道他身高才五尺时,就立刻拿下了他的考卷,还做诗一首,以讽刺他的委琐形象。“五尺孔夫子”大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儒衣儒冠,发誓从此不读诗书,随后变卖了全部家产,进湖投了水寇,并给自己起了这么个有些大不敬的诨号。
本来那股水寇与其他的太湖水寇一样,都是一群活不下去的百姓组成的,良莠不齐,而且组织混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自从这个“五尺孔夫子”入伙之后,情况就渐渐发生了改变,由于“五尺孔夫子”读过书,通礼晓情,又能从一些兵书上拿出些兵法之类的主意,所以这股水寇渐渐壮大起来,逐渐兼并了其他的一些水寇,最终成为了这太湖中最大的一股水寇,他们不仅在太湖众多水寇中称霸,甚至还数次单独击败前来进剿的官军,名声大噪。
后来那水寇的头领在前往苏州会相好的姐儿时被官军拿住,随后在南京被剐了三千刀,于是这“五尺孔夫子”就被推举为新的头领。他深知自己实力有限,不可能与官军长期对抗,于是便逐渐用银子开路,最后终于成功的贿赂一名朝中的大官,在得到“五尺孔夫子”不再进扰湖边商家地主的保证后,一顶“苏州府副断事”的七品官帽就飞到了“五尺孔夫子”的脑袋上。
这“五尺孔夫子”倒也没有将这官帽放在眼里,他只在那衙门里待了不到两天便向上官告了假,又回到了这太湖之中,并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