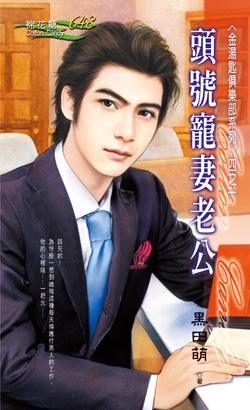蝎子号-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或许会失去生命。”她说。
“如果有一天我失去利用价值,他们一样会要我的命。”我说,“我没有选择,如果在小大学里教一辈子的书,到老来我一样要死的,蝎子号,世上没有长存不灭的东西,套句你说过的话,在时间无边无涯的荒漠里,三十万个小时与三千小时是没有分别的。”
“那是三天之前,”蝎子号说,“在过去的三十六小时内,我学了很多,活着还是很好的。”她看着窗外。
我失笑,“来,我们走。”
我们驾车到实验室,缪斯看见我们,显得“雀跃”。我做了茶,与蝎子号一起坐在它前面。
缪斯问:“你们成为朋友?”
我看蝎子号一眼,不响。
蝎子说:“缪斯,请你将阿姆斯特丹的‘火箭’计划资料打出来。”
缪斯答:“是。”
荧光屏上出现一连串的资料,蝎子凝神观看,缪斯的资料出名详尽,光是介绍将阿姆斯特丹,就从世界大地图开始。
蝎子号看完之后,问缪斯:“‘火箭’的蓝图就在将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梵高路的皇室大厦?”
我说:“这是所相当著名的大厦,属于一间钻石切割公司,大厦的地下就是装饰用钻石商场。”
蝎子号说:“缪斯,我要继续看下去。”
缪斯打出影片,“这是皇室大厦七楼。”
我们看到一所现代设备的办公室,一切都很正常,职员忙碌地工作,电话铃响着。
“蓝图藏在这里。”缪斯说,“总经理室。”
影片中镜头经过豪华布置的总经理室,停留在一幅荷兰大画家梵艾克的“春猎图”油画前。
我叹口气,“保险箱为何一定要藏在油画后面?”
缪斯笑,“你错了,摄影师不过想指出,这幅梵艾克是真迹,时价三百八十余万美元。”
蝎子问:“夹万呢?”
“夹万在这张巨型写字台左边下角,非常袖珍小巧,三十公分高二十公分宽,不会比一格大得多。”
蝎子点点头,她问:“肯定是在里面。”
缪斯:“应该是在里面。”
蝎子:“‘火箭’到底是什么?”
缪斯:“我不知道。”
“取得蓝图,我如何辨别真伪?”蝎子问。
“C7会核对。”缪斯说。
我说:“也许因为这样,才想到以机械人代替我。”
缪斯说:“J3,蝎子号不是普通的机械人,你不必过度自卑。”
我说:“缪斯,我一小时前向C7辞职,C7应允,我想知道,这个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
缪斯说:“我从来没见过C7,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老伴,J3,我不是预言家,我不能帮助你,我的资料中并没有这样的前例。”
我沮丧地低下头。
蝎子说:“别担心,J3,明夜我启程到将阿姆斯特丹,不消二十分钟我就可以打开那个夹万,C7总要与我联络,到时我会问他想怎么样。”
我瞠目,“你问他?”
“为什么不?我们的身份低微,也总有发言的资格,我认为这个人不应令你的生活不愉快。”
“蝎子,”我被感动了,“你这么讲义气,我很高兴,可是人心险恶,事情哪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缪斯说:“蝎子号毫无机心,J3,你不能让她独自去取‘火箭’,她可能遭到破坏。”
“别担心,辞职管辞职,我会陪蝎子上将阿姆斯特丹。”
缪斯说:“那我放心了。”
蝎子号笑,“你‘放心’了?你的心在哪里?缪斯,我们两个都没有心。”
“蝎子号,”缪斯说:“这不是正确的,有思想就有心。”
蝎子叹口气,“缪斯,有时我也很困惑,世上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
缪斯如一个智慧的长者:“蝎子,别太贪心。”
我说:“我们去看博士吧。”
缪斯说:“J3,你当心,蝎子可以不眠不休,你当心倒下来。”
我呵呵地笑,“你吃醋了,缪斯,你瞒不过我。”
“再见,缪斯。”蝎子说。
“再见,你们两个。”缪斯说。
蝎子问我:“博士的屋子,仿佛只有铁门一把锁?”
“防宵小也足够了,要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开直升机进来,难道以高射炮对付他们?”我说,“博士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
我与她并肩出铁门,锁好。
天空上一轮明月,我仰起头看,然后说:“探望完博士,我要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与你到将阿姆斯特丹去。”
蝎子笑一笑。
博士在病床上睡得很稳。
护士说:“别吵醒他。”
“他怎么了?”我问,“可有进展?”
“没什么事了,但是需要好好修养,不能过劳,不能受刺激,否则难说。”护士报道着。
我笑道:“我这就‘放心’了,”我抚抚胸口,看着蝎子,“我是有心的。”
护士以为我们打情骂俏,退出病房。蝎子瞪我一眼。
我们还是把博士吵醒了,他睁开眼睛,问:“是J与蝎子?”他坐起来,张开手臂。
我走上去,“博士。”我说,“精神好点没有?”
“J,你不生我的气了?”
“呵,不,博士,昨天我的态度太坏,我是来道歉的。”
“J,”他说,“我视你如亲人一般。”他的眼睛潮湿了。
“博士。”我握着他的手,侧着头,不敢让他看见我的眼泪。
蝎子号又开始用她那种方言与博士交谈,发音虽然简单,但是悦耳非常。
我忍不住问:“你们在说什么?又在埋怨我?”
“不,”博士笑,“蝎子在表示不满,她说她没有眼泪。”
我奇道:“你要眼泪干什么?”
蝎子号忽然转过头,非常生气。
我说:“眼泪主要的功能是润滑与杀菌,你身上又没有纤维质,况且制造泪腺多么复杂……………”
博士摆摆手,表示我不要说下去。
蝎子闷闷不乐地说:“我到外边去等你们。”
等她走出病房,博士悄悄跟我说:“你有没有觉得蝎子有点怪?”
“早就觉得。”我笑。
“不不,我是指最近。”
“最近?”我益发觉得好笑,“她才‘活了’二十天,我只认识她三天,我不明白‘最近’是什么意思。”
“J,你知道她的二十四小时等于我们的一年。”
“这我不知道,原来‘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十年’。”我笑。
博士喃喃地说:“但我替她安置‘脑’,不是叫她思考这种问题。”
“她现在已不受你的控制了?”我问。
“我都有点害怕,”博士说,“她太像一个人。”
“我早就发觉,”我摊摊手,“她现在要求有眼泪。”
“好好照顾她,J。”博士拉住我的手。
“我会的。”我答应他,“我喜欢她。”
“J,那么我放心了。”他高兴地说。
“博士,我已有数日没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你。”
“好的,J。”博士依依不舍,“再见。”
我到会客室找到蝎子。
“好吧,老友,我们可以回家了。”我拍拍她的肩膀。
我吩咐蝎子号做一连串的工作:订机票,收拾行李,订旅馆。
她觉得麻烦,对她来说,在公园坐一夜便可以解决住宿问题,她能够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作,她能说十种主要语言,除了‘思想;太复杂,跟人类太相似外,她可以说是个十全十美的机械人。
“你有无告诉博士关于辞职的事?”她问。
“没有。”我说,“他在病中,我不想他烦恼。”
“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
“蝎子号,”我想伸手拧她的面颊,可是终于打消原意,“不久你就会知道我们人类虽然弱点多多,但不失是一种可爱的生物。”
蝎子与我抵达阿姆斯特丹,是一个阳光懒懒的日子,欧洲天气比较冷,人们走在街上,口中呵白汽。我与蝎子自机场出来,租了一辆车,驶往酒店。
蝎子像一个孩子,充满好奇,目不转睛的吸收着新事物。
我对她笑说:“等你去到巴黎,就知道了。”
她忽然问:“荷兰人为什么喷白烟?他们又不是抽烟。”
我一怔,然后哈哈大笑,“喷白烟?啊,蝎子号,人的体温是华氏九十八点六度,今天的温度低,自然呵气成雾,你不明白?“
她自然立即明白了,非常羡慕地说:“啊,你们身体的结构真是精妙。”神情中也不免有点黯然。
“达尔文提倡进化论,”我笑道,“我宁愿相信上帝…………谁愿意做猢狲的后代?”
“但你们的思想仍然非常原始。”蝎子说。
我又笑,“好了,别讥笑我们。”
我发觉我对蝎子号的忍耐力好许多。
到达酒店,柜面给我们两间房间的钥匙,我决定退一间房,跟蝎子商量。
我说:“看,两个人住一间房,好照顾,我保证不会对着你脱衣服。”
我填“张三先生夫人”。
蝎子与我上楼,我进浴室洗澡,叫她准备“工具”。
好助手,我想。
待我浴罢出来,她换上新衣服:蛋黄的宽身衬衫,紫色长裤,正在忙碌地准备爆窃夹万的工具,自橡胶炸药至记录号码电子仪器,钻,凿,一应俱备。
我对她先吹一声口哨,然后解释:“这是男人看见漂亮女子的激赏表示。”
她笑一笑。
“还有,我以为有你在,我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工具了。”
“你以为什么?”她白我一眼,“你以为我只要对夹万叫一声‘芝麻开门’,它就会自动开启?”
“啊,”我说,“你看过《一千零一夜》这本书了。”
她问:“皇室大厦那个保险箱,是什么种类的?”
“我不知道,”我说,“去到才算。”
“几时行动?”她问。
“今夜。”我说,“如果有隐行仪器就可以了。”
“我看过一本小说,”蝎子号忽然说,“讲到隐行人一点也不快乐,因为他们不能穿任何衣服。”
我大笑。
蝎子号拿起一把枪,装上灭声器,向窗外瞄准。
“蝎子,”我说,“我情愿任务失败,也不愿开枪。”
她点点头。
“这是什么?”我指着摊在床上的长型盒子。
“这是我的私人武器,”她打开盒子,“轻型迫击炮,有自动追踪仪。”她双托起来给我看。
“这东西可以轰掉整个军队。”我吃惊,“你为什么需要这样强有力的武器?”
“防身。”她说,“当敌人提起刀的时候,我们也要提起刀。”
“这句话真熟,”我微笑,“你阅读的范围真广。”
“嘿。”她冷笑,“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整天读书了。”
“你不见得也整天抬着这管东西走路吧?”我问。
“放在车后行李箱。”她说。
我打个电话叫侍者送食物上来。
“吃吃吃,”蝎子号扬扬手,“整天就是吃,告诉我,这些动物尸体的味道是否真的好吃?”
我喝道:“你少捣蛋!”
她大声笑,我看着她娇艳的笑晏,禁不住叹一声气,多么奇怪的一具电脑机械人,如果她往酒吧中一坐,我保证有一打以上的男人会向搭讪。
食物送上来,我据案大嚼,蝎子摇头叹气。
她说:“J3,你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吃相是最败坏你形象的时候。”
我抹抹嘴取牙签,“一切都是为了吃,人不能饿肚子,衣食足方能荣辱。”
她凝视我。
我说:“蝎子,你不应该想太多,你的资料储藏器太活跃,输出资料的时候混合太多你自己的思想,这是不良现象。”
蝎子号说:“过一阵总有一具混合型电脑会出这种毛病,”她用手撑着一边头,“人何尝不是一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