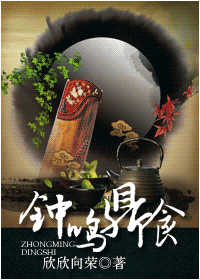鼎食之家-第27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妙容对于这些食物,除了那熏肉外,其它的两样都能接受。主要是陆洞人吃的熏肉并不是谢妙容常见的猪和羊,相反猪羊是比较少见的。他们猎杀的动物比较多的是猴子,此地的山间林地里猴子是常见的动物,陆洞人也比较喜欢吃猴子肉。对于杀猴子,吃猴子肉,谢妙容会联想到猴子长得跟人差不多,心里会毛毛的。她刚才回来时候,可是亲眼见到陆家的孩子们从挂在墙上的一具形似人的熏好的猴子上割下了几块肉……
吃完饭,天色就黑尽了,谢妙容跟阿豆洗了洗脚,就也回屋去躺着了。
说起来,今日经历的事情还是挺多的,谢妙容闭上眼,眼前就会出现萧弘的脸,以及他一闪而逝的惊异的眼神。
她又开始琢磨起来萧弘这眼神的意思……
时间流逝,很快就到中夜,她心里有事,辗转反侧,无法如入睡,在她身边不远处躺着的阿豆已经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谢妙容索性坐起来,看向窗外的皎月。隔壁的阿石这时候应该已经悄悄溜出去跟周坦会合,一起去探石楼,去找萧弘了吧?阿石不愧是有身手的人,他悄悄溜出去,就睡在他隔壁的谢妙容居然没有听到一点儿声音。
谢妙容抱着膝盖,将下巴搁在膝盖上,一边等待,一边想一会儿萧弘要是被带来了,他会跟自己说什么?他会不会要自己不用管他,离开这里回到建康去……
门外忽然传来轻轻的叩门声,谢妙容一开始还以为自己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出现了幻听。她想,难不成阿石和周坦已经得手了,他们已经带了萧弘回来?但是看看窗外那一弯月亮的高度,此时应该刚过了子时不出半个时辰,阿石和周坦才行动了不久,应该不会那么快得手?要是不是阿石和周坦,那又会是谁呢?
谢妙容有些惊疑不定,但她还是很快站了起来,赤着脚慢慢走到门口,隔着门板悄声问:“谁?”
“卿卿……”
这个词入耳,谢妙容已经惊喜不已,这世上,还会有谁这么叫她,除了她的丈夫萧弘,别无二人。
他怎么就能肯定来开门的一定是自己呢?或者他也和自己一样,心有灵犀?
听得出来,他的声音里面有激动,还有急切。
谢妙容抽掉木门闩,把门轻轻拉开。门外一人闪身而进,扑面而来的是谢妙容熟悉的气息。不等她有所动作,她已经被他抱住了,随即他用背将身后的木门阖上。他的动作迅速而又很轻,几乎没发出什么大的声响。
“十五娘。”萧弘在谢妙容耳边激动不已地唤她,“今日我瞧见了你,真是……真是太吃惊了……”
谢妙容没有忘记两人还靠在门边呢,她有太多的话要和他说。
她抱着他,往后退,一直退到屋子的最里面,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她仰面看他,眼里蓄满了泪水,哽咽道:“三郎,知道你活着,能再见到你真好。”
回答她的是萧弘一个缠绵的长吻。她被他吻得气都回不过来。
她感觉到了他身体的变化,而一股热流也在她小腹之下盘踞,她发觉自己从未如此渴望他。
不过,现在貌似不是一个合适的做那种事情的时机。两个人都强迫自己把那种冲动压下去。
长吻结束,萧弘的唇舌一离开谢妙容的,她立即就问他:“三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去做了陆溪鱼的侍卫,我听说,凡是做了陆溪鱼侍卫的都是她的男宠……”
后面的话谢妙容没有说完,萧弘却是听出来了谢妙容话里那浓得化不开的酸味儿。
他闷声笑了笑,说:“你想得太多了,我之所以装傻成为陆溪鱼的侍卫,但是可没有让她得手,让自己作为她的男宠。你知道,男人不想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女人也没办法。”
“看来,她还是诱惑你了对不对?”
“是的,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我被农洞寨主的儿子救了后,因为那些伤都是些外伤,不要紧,所以好得很快。”
“我听你们队伍里一个逃回建康去的兵士牧七说,他亲眼见到你中了三四箭,那样也不重吗?”
“那些箭都射在我肩膀,手臂和腿上,没有射到胸背那些要紧的部位,我落水,是因为那些箭上有让人麻痹的毒|药,我落入水里,尽力让自己仰面随水漂流,将头抬高,这样尽管四肢麻痹,但还是不会落到水里被淹死。我在水里尽力强撑着,等到被冲到农洞的那河岸边时,我就晕了过去,后面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既然你伤好了,那你为什么不走?”
“……”萧弘沉默了半响,才开口道:“我没办法走,我被农洞寨主的儿子下了蛊,他将我给了陆溪鱼交换了四个漂亮的女奴后,也将那解蛊的蛊虫给了陆溪鱼。而且我还想查一查那刺杀圣上以及害死了我那么多兄弟的人,所以,我就留了下来。”
☆、第212章 21。2
谢妙容完全没有把萧弘的后半句话听进去,只是非常紧张地问他:“你被下蛊了?这可怎么办?”
不等萧弘回答,她已经抢先想到:“是不是要从陆溪鱼手上弄到那解蛊的蛊虫才能解蛊?”
萧弘回答:“是,只不过那东西被她以血饲养,跟她可以产生感应,非常不容易偷到。”
谢妙容继续紧张地问:“……若是你从这里逃开,会有什么结果,还有,能有别的法子解了你的蛊吗?”
“要是从这里逃开,陆溪鱼可以催动那只母蛊,在我体内的子蛊就会噬咬我五脏……”
“噬咬你的五脏?”
谢妙容想到一只虫子在体内心肺上咬来咬去,头皮就发麻,而且她知道这种痛苦恐怕常人难以忍受。蛊这种东西她穿前穿后都听说过,不过以前一直都把这个当成莫须有的传说,直到这会儿她都还不太敢相信真有这种东西存在。但是从萧弘比较严肃的表情她可以看出来这不可能是开玩笑。
萧弘顿了顿又说:“别的法子,除非是同样会养这种蛊,并且手段比陆溪鱼高明的黄洞的洞主,以及他的子孙可以解蛊。”
“黄洞的洞主?洞主的子孙?为什么会是他们?”
“因为龙溪十八洞自古以来养蛊和下蛊的权利,只能是洞主还有洞主的子孙可以享有。黄洞作为龙溪十八洞的总寨,黄洞的洞主拥有比其他的洞主更高明的养蛊,下蛊,解蛊之术,这也代表了他们的权力等级不同。”
“所以,你要是不能让陆溪鱼给你解蛊,就必须去找黄洞的洞主,或者他的子孙?”
“差不多是这样。”
“可是黄洞的洞主,或者洞主的子孙咱们也并不认识,再说了他们想必对汉人也存有戒心,所以要找他们帮你解蛊又谈何容易?”
“所以,我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日,除了查那刺客以外,还想找到机会解蛊。”
谢妙容现在是了解了为何萧弘要留在陆溪鱼身边做侍卫了,只是这样一来,萧弘就面临着被陆溪鱼觊觎**的危险,而且身上被下了蛊,就有可能永远也没办法离开陆溪鱼,就算强行离开了,等待他的将会是受尽痛苦而死的结局,这让谢妙容无法接受,相信那也是让萧弘比较为难的地方。
“十五娘,你不该来,这龙溪十八洞可是个危险的所在。听我的话,明日。你就和阿石他们回去吧。”萧弘握着她的肩膀看着她恳切道。
“我们回去你怎么办?你还不知道吧,我阿父派了周坦和阿石来帮我,萧家的一家人都等着你回去,好一起搬去徐州呢。另外,圣上被刺身亡了,现今坐在紫宸殿龙椅上的是以前的桂阳王。”
“什么?圣上被刺身亡了?”萧弘一听立即惊道。
也难怪他吃惊,当日刺客刺杀小皇帝曹桂后,萧弘就带着禁军精锐一路追着刺客出了城,后面宫里的事情他当然不知道。
谢妙容:“就在圣上被刺的当夜,他伤重不治……后来,鄱阳王凭着刺客遗落的一柄铸有睿王府徽号的短剑说睿王是谋刺圣上的人,睿王说要捉住刺客指认自己他才认,王司徒站在睿王一边,说那短剑不能作数,并且睿王还说圣上崩后那个受益最大的人才是幕|后的凶手,这相当于说圣上崩后,最有可能即位的鄱阳王才是派遣刺客刺杀圣上的人。我阿父站在鄱阳王这边,他认为睿王推测幕|后凶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两边都不相让,可是国不可一日无君,拖了三日,最后到底是妥协了,两边各让一步,让桂阳王登上了皇位……”
“这真是糊涂!帝位怎么能够如此轻率地就给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王爷。”萧弘不忿道。
“所以,我认为桂阳王坐不稳皇位,要不了多久这皇位还会易手。我阿父现如今被鄱阳王拉上了贼船,是难以脱身啊。”
“你是说鄱阳往才是幕后的凶手,正是他策划了刺杀圣上,又嫁祸睿王。结果却发现睿王在朝堂上根基深厚,他单凭借一把铸有睿王府徽号的短剑,根本扳不倒睿王。不得已,他只能后退一步,暂且同意让桂阳王登上皇位,接下来,他再想其他的办法继续觊觎帝位?”
“对,这些事情都是在太皇太后薨了之后发生的,先前太皇太后在的时候,鄱阳王和皇后对太皇太后颇为忌讳,所以不敢动手。但是等到太皇太后不在了,他们就忍不住了。其实要我说,这种事情也是迟早要发生的,鄱阳王不管是立嫡立长,都该是他。太皇太后当初不知是怎么想得。她要是早废了被桓羿扶起来的南平王,立鄱阳王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情了。其实,要依我的意思,那刺客你也不用继续查了,只要想办法从陆溪鱼手上弄到那解蛊的蛊虫,就赶紧返回建康吧。我就怕耽搁久了,朝局有变,会有大的变乱在建康城发生,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就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离开建康去徐州了。我也劝过我阿父,他要急流勇退,带着谢家人搬去会稽,他可能也在考虑。至于如何帮你解蛊,我倒是想让周坦和阿石帮忙,把那陆溪鱼给绑了,威逼她交出来解蛊的蛊虫,得了蛊虫给你解了蛊我们就离开龙溪,回建康去,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你说对不对?”
听了谢妙容的话,萧弘对于要捉拿刺客向朝廷交差没了什么兴趣,毕竟现在皇帝都换了,派出刺客刺杀先前的小皇帝的还是鄱阳王。他要是抓住了刺客为先前的小皇帝报仇,那就是得罪了鄱阳王,等于是间接跟睿王结盟了。对于这两人,萧弘都无投效之意。
所以,留在这里的意义除了想杀那害死他手下那么多兄弟的刺客外,剩下的就是得到解蛊的蛊虫了。尽管萧弘对于那害死了自己手下那么多兄弟的刺客非常痛恨,很想抓住他为兄弟们报仇,可是按照谢妙容所说,不能在这里呆久了,毕竟建康家里的事情非常重要。
“好吧,那我就等周坦和阿石回来,一起商量下如何里应外合,绑住陆溪鱼,要挟她交出蛊虫,我们尽快离开陆洞。”萧弘最终答应了谢妙容的提议,接着他问她:“周坦和阿石出去了多久了,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
谢妙容正欲回答,忽地听到外面“咣当”一声锣响起,接着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外面大声叫嚷:“里面的汉人,都给我出来,你们已经被我们围住了!”
静夜里的这一声锣响,一下子就把整个木楼上睡觉的人给惊醒了。
跟谢妙容同一个屋子,睡得打鼾的阿豆抖了一下,一骨碌从簟席上爬起来,慌张地喊:“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