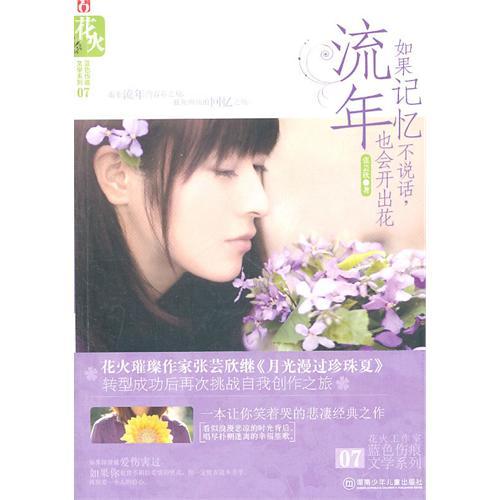石青色记忆-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雅帕菲卡似乎皱了皱眉头。
我们就再没话说了。挂了电话之后,回头看见了梦瑾。我想要过去抱抱她,可是看着她大腹便便地拎了个包站在门口,我有些惴惴。“小梦,你回来了。”我很平静地问她。梦瑾的脸一下子绽开了花,她丢下了旅行袋,朝我大步迈过来,步子颠儿颠儿地,我本能地抬起胳膊,想要接住她。
她一拉着我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说了,说的都是日本某某地下雪了,要过年了,温泉怎样腾腾地冒起泡泡了。我没有插嘴,到了最后索性看着她讪讪地笑起来。
“卡卡姐,”梦瑾用力地抱着我,我觉得她的肚子抵着我的身体,“我会独自把孩子生下来的。”她的脸因为怀孕有点肿胀,毛孔张开了,原本嫩滑的皮肤看上去点点洼洼的。我抬手摸摸她的面,她扑哧一下笑了,看不出半点悲伤,反而有一种抹开的凛然。“叫我爸撵我出来了。”她坐下之后半歪着头,满怀了柔情地抚摸自己的肚子,“他大哭了一场,我也哭了。我很没出息。”
我啥也说不出来了,只好用力地握着她的手,感觉到手心微微发热。
(十六)
这是我出阁之前的夜晚。所有的姐妹都到了我们的出租屋。米罗和卡妙则到新房子去,他们的弟兄们也在那里陪他度过单身的最后一夜。
陆陆续续来了人。我在玄关处点了一大盘香薰蜡烛,点着嘴唇数人数。
伴娘沧绯在煮汤圆。裳雪在给我整理首饰盒,宫儿在清点化妆箱。拉斐尔在数婚纱裙摆上面的蕾丝玫瑰。Tina等会儿会给我上头,正弯了腰看着桌子上的梳子念念有词。梦瑾很疲倦,挨在沙发上打起盹来。小云也因为身体原因没过来。蔓蒂在她娘家,也没有回来。
我看着这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心里已经满足得要死了。
“雪儿!”宫儿忽然大呼小叫起来,“配婚纱的那条钻石项链呢!”
裳雪慢吞吞地从首饰盒底部翻了出来。
“我的妈妈呀!”宫儿拍拍心口,“人家卡妙哥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蓝非钻,你给随便塞到盒子下面去,不像话呀!你老公成天让你暴殄天物的吗?宠坏你了。”
裳雪嬉笑着朝宫儿扔盒子里备用的塑料花。
Tina也终于找好了情绪,让我将头发解了,拿了梳子过来。
门铃响了。
沧绯跑去开门,接着就听到她惊喜万分地叫了一声。我们出来看,见是雅帕菲卡站在门口,手里抱了一个很大的狗熊娃娃。那小熊穿了一件小西装,手里还捧着一束毛绒绒的玫瑰花。他很不好意思地旋了旋脚尖,将小熊放在一旁的沙发上。
“卡卡,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他说。
裳雪嘟嘟嘴:“哪有人送一只给别人结婚的。”宫儿推搡她:“嘘嘘,又不是恭喜你结婚。”
“这个是送给你先生的。”雅帕菲卡从口袋里摸半天,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众人又猜测了一番。
他显然是不习惯成为焦点的感觉,自己就揭盅了:“领带夹,嗯……上面镶了水晶。”
我感谢了他一番。沧绯就端出一碗汤圆,叫她的雅帕哥哥吃了才走。他没有推辞,坐在沙发上,边吃边看着我。“很可惜,我妹一直想来,说要陪着你出嫁的。”
“卡卡,”Tina小声对我说,“过了吉时就不好了,快来上头。”
雅帕菲卡一听,就站起来,往我的房间跨了两步,又犹豫地停了下来。
(十七)
没遇到之前,总觉得仪式是俗气的。可这一刻自己却觉得很神圣。
Tina慢慢地把着梳子,嘴里念念有词:“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我可以感觉梳子顺着头发流了下去,将所有美好的心愿都匀匀地铺满了整个心房。姐妹们鼓起掌来。
我一回头,就看见雅帕菲卡挨在房门口,眼睛里有似笑非笑的颜色。
“雅帕哥哥,你快走吧!到新郎那边去闹吧。”沧绯蹦着将雅帕菲卡推了出去。
狗熊娃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拿了进来,放在床头。它的脸上架了一副又圆又大的黑框眼镜,硕大的脑袋歪着对我直打哈哈。我最喜欢那一捧玫瑰,每一朵都柔柔软软地将芬芳凝固了起来。
“卡卡你是不是把卡妙想象成大狗熊了,哈哈哈哈!”宫儿的声音永远那么有穿透力。
房间里便又热闹了起来。
裳雪刚接了个电话。一走进来就有人逼问她,说最近他们夫妻两个腻乎了,米罗是不是要来刺探情报,把你给策反了。裳雪红着脸摇摇头。再追问,原来是艾欧里亚。房间一下子安静了起来,有人悄悄地望了拉斐尔一眼。
“他对你还有想法?”Tina将裳雪拉了过来。
她窘得直摇头。该是了断的时候,就要断得决然。她没有看拉斐尔,可她忽然生出一种苦口婆心的凛然来。“爱情本来就没分什么对错。他回去了,说永远祝福我们。”
拉斐尔也喃喃地接了口:“走吧,是应该走了。”
卡卡
(一)
这一夜实在是很难入睡。可是Tina硬逼了我躺下,然后将那个狗熊娃娃往被窝里一塞,让我权当个男人搂着。后头有人问:“谁呢谁呢,哪个男人呢?”Tina捂着嘴笑,随便,卡卡你喜欢谁就是谁。
她们把房门带上,还没来得及蹑手蹑脚地出去,外头就有人欢乐起来。我在她们涌动的音乐声和喧闹声中迷迷糊糊做起梦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感觉有人在扯我被子,我就一骨碌爬起来。眼睛还蒙着一层瞌睡,没看清楚眼前一堆的姐姐妹妹们。我被推着出去梳洗妆扮。化妆师很准时地上门,带上两个小徒弟,没喝上一口水就忙开了。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的五官从混沌一团渐渐地有了点轮廓。足足有两个小时,我才逐渐看见了自己的鼻子和眼。
中午十二点,宫儿在阳台大叫:“来了来了!”姐妹们一股脑儿冲到门口去。Tina则不忘记将我推进房间,又低声嘱咐沧绯好生藏好我的鞋子。门便砰一声被关上了。
沧绯那个小妮子不闲着,左翻翻,右拣拣,边折腾边说:“卡卡姐,卡卡姐,这儿不好,那儿不好,他们一下子就会找到的呀!”最后她把鞋子放在了衣柜里头,用卡妙的一套旧西装盖得严严实实。
我们并肩坐下,凝神听着外面欢乐的笑声,心里怦怦直跳。
隐约是裳雪的声音:“卡妙哥,把米罗当成卡卡姐来啵一个!不过不许亲嘴。”接着是一阵起哄。过了一阵,又有谁扯开喉咙唱起歌来,门太厚实了,将外头的快乐压制成书签,扁扁地透过门缝塞进来。
我和沧绯等得有点腻烦了。我将挺直的腰略微放松,弓着背喘了喘气。
房门突然被撞开了,吓得沧绯伸开了胳膊拦在我前面。米罗笑着说:“小妹妹,别徒劳了,哈哈哈哈!”接着他一步一步走进,又在后头挥手,一众兄弟就在房间里找了起来。阿释密达在沧绯的跟前蹲下来,偷偷地亲吻了她的脚踝一下,沧绯红着脸踢了他一脚。只有沙加老师抱着胳膊站在门口,微笑地望着忙里忙外的人们。穆正在梳妆台那块儿翻检着,擦擦头上的汗对着老师说:“您就像个包工头一样看着咱们吧,刚才俯卧撑也不帮着做。”宫儿在后头笑着推了沙加一下。
最后找到鞋子的那个人是加隆。他从衣柜里艰难地直起腰,举着我那只红色的高跟鞋,快乐地像个孩子。我愣了一下,为什么这人群里会有他,我刚才竟然没有看见。
卡妙从他手里接过,慢慢地蹲下身子,帮我穿上,然后仰起头低声跟我说:“永远都不离开我,好不好?”我啥也说不出来,只是用力地点头。拍照和摄影的师傅将长枪短炮都对准了我们。卡妙今天穿的是白色西装,里面的翻领衬衣和黑色腰封将他衬得极优雅。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出非常喜欢的电影的台词:“如果这个世上所有的戒指都拿给我挑,这个,你送给我的,就是我想要的。”
他将我抱起来,抱到外头去,又一直走下楼去。他的胳膊很壮实,稳稳当当地将我托着。
我们在婚车前留影,沧绯又为我撑开了一把红伞,有人撒米,撒彩纸。街上的人也被我们感染了,脸上晕开了喜庆的色彩。
婚车是穆找来的,我坐了进去,卡妙将花捧递给我,然后细心地替我收拾裙摆。沧绯本来也进来了,可一看就又蹦下来,跳到卡妙身边帮着收捡。阿释密达在前座喊她:“快上车快上车,别给人添乱。”沧绯就吐吐舌头,乖乖地服从了。
我们在坐车绕了几条名字很吉祥的路,在吉时准时入新房。
Tina问:“谁挑的吉时?我一直没问。”
我说:“我妈呢。我们回家那边还要摆一次。”
米罗故作深沉地对着卡妙感叹了一声,兄弟,要摆平岳父岳母大人也是个技术活儿,我要好好地教导教导你。卡妙只是微笑,不作声。
进了门,给帮忙搬嫁妆的姐妹们发红包,然后拜了拜祖先,大家就准备要吃午饭了。我提着裙子走下去的时候,卡妙还在后头收拾东西。加隆轻轻地叫我。一回头,才发现其他人早就哄着跑下餐厅去了,就剩下我俩。我不说话了,他也一样。
走到楼梯口,我犹豫着没有迈步。人家说,结婚当日新娘最大,但大不过天,所以必须得用红伞挡着。我就这么抬起头看天,忽然就有一把红色的伞挡了过来,冬日的暖阳透过伞的布罩了下来。加隆微笑着在我后头,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随时为我撑开。
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身材比卡妙还要壮实一些,腰身收下来,感觉更加魁梧俊朗。我想起Tina结婚的时候,他挽着我在酒店里行仪式一般地走了一转,说那是最后一次,他将我当做了永远和他牵手的那个人。
为什么脑子里总是冒出许许多多杂乱的镜头?我们就这么互相走近,又擦身而过,接着成为两条平行线,永远都这么观望着对方,却永不相交。
刚才被喜悦充溢的心脏硬要挤入一丝惆怅,显得有些消化不良了。
“走吧,卡卡,我给你打伞。”加隆挺起胸,庄重地像在教堂里陪我行礼。
我走一阵问他一下。他一改了往日的健谈。
你会回去吗?
不会,我哥把酒吧送我了。
你哥会回去吗?
不知道,他会和嫂子商量。
你为什么说话那么简洁?
我的头脑简单。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吐字清晰,耐心地回答我每一个问题。他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稳定,一直照射在我心里那些说不出缘由的阴霾角落。我有时候会把他当成一个枕头,总在黑夜里铺开柔软的梦。这些,卡妙都不知道,也不能做到。
餐厅就在前头,霓虹灯无辜地眨巴着大眼睛。我们不约而同地站住了。
天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阴暗了,呜咽一阵,就开始飘起小雨了。这红伞太小,撑不住我们的头脑,逐渐就沉沦在这阵忧郁的微雨中。
他拉了拉我的胳膊,抬脚往餐厅前面的一条小巷里跨去。我不由自主地跟着。那巷子歪斜着朝左拐了一下,就是死胡同了。
我们起初还是踱了步子地走。后来就小跑起来。不长的一段,奔得气喘吁吁。一到了巷子的尽头,他便将我拉了过去,靠在墙上,认真地看着。我看不懂他眼里的那一汪,只觉得自